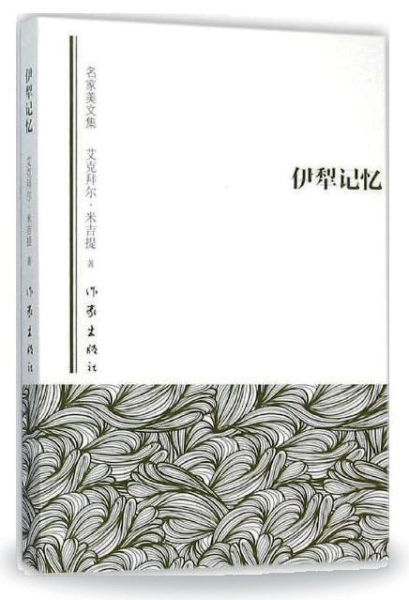
当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把他的最新散文集命名为《伊犁记忆》时,我把它理解为这是作者对伊犁故乡的回望,也是他对曾经生活记忆的梳理。而我这个在伊犁生活过近10年的读者读起来,也算是一种回望,是对过往伊犁风情的回望。
上世纪70年代末,艾克拜尔以短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走上文坛,这篇小说获得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他的文学之路,由此正式开始。而此时,艾克拜尔还是伊犁州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不久之后,他去北京领奖。到了北京才听说已经被文学讲习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录取,成了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一名学员,多年后他又成了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导师。
这些经历,他都写进了《从学员到导师》一文中。我在看这篇文章时难免会想起2013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时接触艾克拜尔老师的情景。那时,我因为在诗歌组,未拜入他的门下,有一天他请他的学生和我们几个新疆籍学员吃饭,老乡见老乡,于是就喝得尽兴了。这是在看这本书时想起的一些往事。恰巧,这也是一本多半写往事的书,从《伊犁记忆》《王蒙老师剪影》《伊犁散记》《童年记忆》《初次遇狼》等文章的题目即可印证。
本书开篇就是《伊犁记忆》。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出了多少在外的伊犁人的心声:伊犁是一种记忆。看过文章就可知晓,这种记忆不仅属于离开伊犁的游子,也属于依旧生活在伊犁的“土著”和初来这片土地生活的人。起码如我,大学毕业后即生活在此,读老伊犁人的文章,也常能生出不少回忆。
在艾克拜尔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生满白杨的城市。那密布城市的白杨树,与云层低语……树下是流淌的小河,淙淙流入庭院,流向那边的果园……”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记忆中,真是再常见不过了。所以,伊犁州的首府伊宁市,也曾被叫作“白杨城”。袁鹰先生曾经游历伊犁,更是写下了散文名篇《城在白杨深处》,由此可见当时的白杨之盛。七八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可能还会看到一点点尾巴。而作为我这样一个外来者,所来不过10年,即便在初到伊犁时,曾经因为职业之便走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也见过一些残存的白杨和果园,近几年来是愈渐难见了。这样的情形,艾克拜尔每次回乡时也都有切身的感受,写进了文章。
在作者的伊犁记忆里,除了白杨,还有满眼的各色花草,“每当夜幕降临,从那家家户户落满芬芳的花园里便会传来百灵鸟不倦的鸣啭。”每家每户庭院、果园里,在花季花开各色,让初来这座小城的人忍不住惊叹,进入了“花城”。这样的记忆对于在伊犁生活得久一些的人来说,真的是怎么也磨灭不掉的,即便离开故乡二三十年后,作者想起这些,还依旧温馨如昨。所以在他看来,“伊犁春色的真正标志,是那漫山遍野怒放的郁金香”,要知道,伊犁本是郁金香的原产地。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被维吾尔人称为“莱丽哈萨克”的郁金香早已经融入了哈萨克人的血液,是哈萨克人最喜欢的花。
一个出门在外的人,走到哪里,看到什么都会把它拿来和故乡的风物进行比较。艾克拜尔也不例外,他在每次在北京郊游,看到山沟里流淌的细小的河流,便会想起故乡天山深处的每一条溪流来。喝着伊犁出产的白酒,端起酒杯也会忍不住说一句:“请开怀畅饮,这是伊犁河的水……”书中绝大部分笔墨都是关于新疆的,《歌者与〈玛纳斯〉》《作为文人的赛福鼎·艾则孜》《天山脚下的哈萨克人》等篇章同样值得留意。
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样一个曾生活在伊犁的读者读本书时,认为全书最好的文章就是写伊犁的那几篇,估计作者不一定会认同,其他读者更不一定认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曾在伊犁生活过。
书中还有一篇《巴金先生的一封回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不长的文章让我意识到,巴金等著名作家作品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译本的相关研究应该还有很多未垦之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相关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