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家鸿 傅兴文的《山顶上的金字塔》是一部干净到极致的爱情小说,讲述的是男主角文恒一痴恋维佳怡却不得圆满,并最终在悲剧中得以成长的故事。作家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文恒一这个男主角,他义无反顾地爱着维佳怡,因之而前行,不管遇到多大的痛苦与挫折,都无法阻挡他对爱的坚持与守望。在多数人识趣地后退之后,他依然坚守,如顽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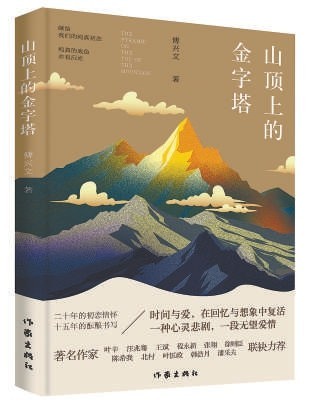 《山顶上的金字塔》傅兴文 著 作家出版社 与此同时,他又因为性格自卑常常退却,不可思议地退守自己的一隅世界,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痛苦、挣扎的个体。他想要得到结果,却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结果。又或者说,所谓的结果,只能是用心去爱、用力去爱的整个过程。过程就是文恒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在他自己看来,悲剧的结果不是由于家境寒微导致,而是自己的性格使然,“我是爱情里的哈姆雷特,而不是奥赛罗,葬送那份爱情的是思前顾后、优柔寡断,而不是嫉妒和冲动。”他很明白苦果是自己酿成的,怨不得贾作甄,怨不得维佳怡。这是爱情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很显然,文恒一身上有很多人初恋时光的投影:面对那份情感,更多的恐怕不是思前顾后,也并非优柔寡断,而是痴心绝对。在满怀痴心的人眼中,她是带着仙气的人,她是山顶上的金字塔,她是遥不可及、不容亵渎的一方存在,她是永恒的乌托邦。如此说来,她不仅仅是一个维佳怡。正如维佳怡对文恒一所评价的,“你活得太不现实了。”在红尘纷扰的人世间,他这份痴心是不现实的。但话说回来,正因为稀罕得如同高山上的雪莲,才显得弥足珍贵。要知道,很多人随着阅历渐深,心灵中痴迷、执着、纯粹的成分会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油滑、粉饰、虚伪、功利。 显而易见,小说中痴心绝对的文恒一有傅兴文本人的影子。他在后记中写道:“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说文恒一就是我。当然,文恒一离我比包法利夫人离福楼拜更近。”小说是虚构的,却带着自传体色彩。时过境迁,当初因痛苦流下的泪水,已然弥足珍贵。清澈、晶莹的泪水,在无数往事沉淀的流金岁月中,闪闪发光。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充满强烈的倾诉愿望,与之相伴相生的是强烈的自省意识。文恒一把自己关在西三环与西四环中间昆玉河边隔断间里的写作,是最刻骨铭心的自省。“虽然写的时候,你会无数次眼含热泪,无数次心绞痛,无数次想放弃,可是,只有把它们如实写下,你才可能将那把利刃彻底拔除,你建造的那座文字之塔也才更有意义。”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一种种心情如慢镜头般回放,笔下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泪交织的混合。虽是无法避免的悲剧,却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安慰自己,我对维佳怡怀有的那种纯粹精神上的恋爱,既是一种缺憾,或许同时也是一笔财富。”写作从生活中来,恋爱的挫折与失败可以转化为写作的素材,不止使用一次,而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无止境的提取。提取即淬炼与锻造,而后是重生。重生是最根深蒂固的成长,外间再猛烈的风雨也无法撼动分毫。由此说来,小说所写的爱情并不是纯然的悲剧,悲剧中盛开的花儿更妖娆、娇艳、容光焕发。 打动读者不是傅兴文写作小说的目的,他提笔书写为的是如实地回到过去,把心中那份潜藏许久的悸动一丝丝拔出,把脑中暗藏多年的激情一缕缕扯出。是的,他所做的只是把初恋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于此,写作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情怀。环境变了,场景变了,姓名变了,初恋季节时的全心全意全情却没有变。 读《山顶上的金字塔》,如有一曲久违却依然熟稔的歌声萦绕耳畔,周遭的嘈杂消弭一空。年少时似曾相识的往事一一涌上脑海,久久无法逝去。那个时候,世界里只有一个她,她就是整个世界。那个时候,她的一个笑容就可以点亮所有的暗夜,她的一句问候就可以融化所有的坚冰。心中有她的日子里,活着就是为了有她,有她就意味着活着。有她并不等于拥有她,有她就是把她放在心中,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人事如何倥偬,她在心中永远年轻、美丽、温柔、善良。而这,已然超越活着,它是生命的存在方式,纯粹而热烈、奔放且潇洒、执着又勇敢。有过一份这样的情感,是生命之树常青的重要缘由。 《山顶上的金字塔》是傅兴文献给80后的初恋进行曲,如一面明澈的镜子,读者不难在其中照见自己身陷痴迷中的某个瞬间或诸多瞬间。在生活颓废麻木时,把这本书拿起来翻一翻,把文恒一和维佳怡或静默或对话的片段回味一番。那种纯粹的爱恋、那种自卑的惶恐,是再也无法回去的曾经。曾经的点点滴滴之中,美好的成分显然更重,也更值得如今的自己细细回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