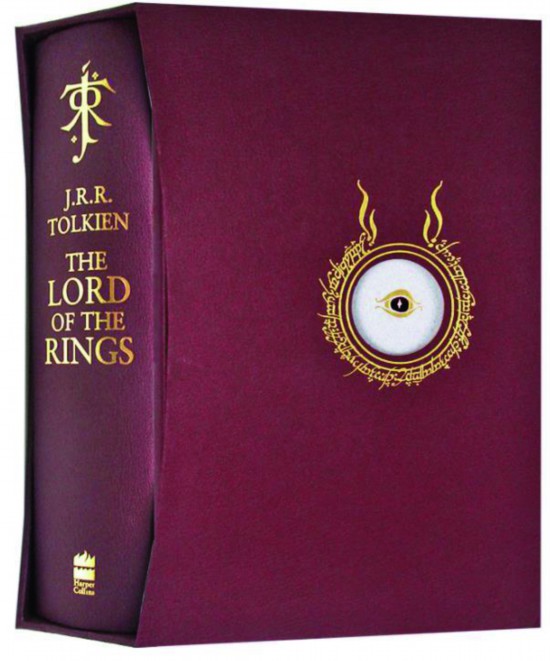   在西方,“幻想文学”是有着悠久传统和丰富内涵的文学样式。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幻想文学的辐射面很广,几乎可以囊括一切幻想类文学作品,包括童话、传奇、奇幻小说、哥特小说、科幻小说等诸多门类。正是如此,幻想文学并非儿童文学的专属文类,成人文学中也有着幻想文学的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末,幻想文学被中国学人从国外引入,并经历了一个吸收和转化的过程,最终被命名为儿童幻想小说。 幻想文学的概念与边界 就在西方幻想文学大量引入和中国出现“大幻想文学”热潮时,吴其南抛出了“幻想文学是个伪概念”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议。吴其南认为,幻想是人的一种潜意识,是创作文学作品的重要心理活动,也是艺术技法之源。在童话、神话乃至所有的非现实文学的门类中,幻想都是必要品。因而,他指出,“将一个本属艺术形象、创造艺术形象方式的问题变成一个创作思维的问题”是错误的。换言之,以一种技法、主题或创作心理来替代一种文学门类是不符合逻辑的。要辨别这一概念的真伪,需要深入该概念内在机理来辨析幻想文学的合法性。从内部机制的角度看,幻想文学在充分调动幻想功用的同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描摹”和“反映”写实的道路。这种边界的设立区隔了幻想文学和写实主义的文学。然而,这还不足以完成概念界定自洽的逻辑。因为即便是写实主义也无法摆脱虚构或幻想的成分。要进一步廓清幻想文学的概念,还有必要深入开掘现实与幻想的关系,洞悉现实与幻想组合的先后、权重等关系。 从词源上看,幻想并非幻想文学的全义,它还内蕴着深刻的哲学与世界观。日本学者城户典子认为,中国幻想文学设定了其内部有一个“幻”的实体,这与西方主流学者所谓“夜的语言”有较大的差异。由此,对作家来说,对自己建构的世界的信赖尤为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幻想是绝对自由的,幻想力的激活仍然依赖于现实基座的反作用力。托尔金的“第二世界”理论也注重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结,而“第二世界”内蕴的真实性源自现实与幻想之间丰富且自洽的逻辑规则。这势必要求作家在运思过程中付出精力来实现两个世界“真实的内在的一致性”。受西方幻想文学思想和作品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界也倾力于在“现实主义”一翼之外,重启“幻想文学”的另一翼。无论是彭懿的“二次元”,还是班马的“幻感”或“迷幻”,都集中在现实与幻想世界的整体性的基点上来创构“中国式”的幻想故事。 幻想小说的文体特质 由此看来,幻想文学不等于“幻想+文学”,也非脱离现实的凭空幻想,而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构筑起融通的桥梁。这种融通性首先体现在文体混杂上。幻想小说不等同于童话,也非一般意义的小说。早在1929年,赵景深就论述过童话与小说的关系,他认为,“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鲁迅也曾将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界定为“中篇童话”。叶圣陶的《稻草人》是典型的童话小说,它与一般的童话或小说有较大的不同,“成人的悲哀”介入为童话的幻想增添了厚重的底色,“两套笔墨”打破了文体单一的惯性,从而获取了从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的角度双向谛视的空间。区隔是为了建构,“童话小说”具备儿童幻想小说的主要元素,不再是单一的“童话”或“小说”了。这种现实与幻想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形式看似存在着文体错位,但实质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幻想小说跨文体的杂糅导源于现实与幻想的张力关系,两者的此消彼长反映了幻想小说内部结构的紧张关系,这也带来了命名的困惑。周锐的《中国兔子德国草》出版后曾被多家杂志分期刊发,不过不同的杂志对其文体的界定却并不相同,有的是“小说”,有的是“报告文学”,有的是“散文”,还有的是“童话”,周锐则戏称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周锐的童话《舞蹈型地震》刊发于《天津文学》时被划到“小说”专栏,对此他这样解释:“他们是成人刊物,不好意思用‘童话’字样。其实大可不必顾虑,既然能容忍小说的‘小’,为什么在乎童话的‘童’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文体归属的困境,其根由在于幻想文学集结了多种文体特征,不能以文体界分来框定幻想文学。安房直子的《谁也看不见的阳台》的中译者安伟邦认为,幻想小说是一种“空想故事”,现实与非现实的交混是其本体特征。朱自强曾以“小说童话”来概括这种幻想小说文体的杂糅性。张之路也认为,幻想文学是一种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文体。应该说,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等文体中都不缺乏幻想的元素,但幻想小说想象力的生发离不开现实的介入与参照作用。简言之,正因为有了现实的立基作用才会有幻想生发的广阔空间。由此看来,对于幻想文学而言,如何处理现实与幻想的关系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根本问题。 现实与幻想的复杂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幻想力根植于对现实的超越或突破。巴什拉从“空间诗学”的角度来阐明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他谈到“当现实令人不满的时候,梦想开始工作。在被挖掘的土地里,幻想无拘无束”。巴什拉的幻想观本源于对现实的超越——“不满”,这种现实与幻想的绝对“二分”容易简化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将幻想置于现实的对立面,这势必会撑破了两者的张力结构。事实上,幻想文学并不是作为反叛“现实”或“现实精神”而出场的。幻想文学同样可以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只不过其在构筑想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绕过了庸俗的、灰色的、模式化的现实主义框架。幻想文学之所以高擎“解放幻想力”旗帜,则本源于幻想力受缚的前提。具体来说,机械的“教训主义”“教育主义”是抑制幻想力生发的主要障碍。因而,将“幻想还给幻想文学”是势在必行的突围之途。 除了命名的混杂外,中国幻想小说发展的困境还体现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两难上,实质上是内外两种思想资源的融通问题。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幻想资源,但受制于儒家“温柔敦厚”及“静穆”思想的影响,这种幻想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那种长期隐匿于民间的幻想传统需要重新开掘、打捞,以此为当前儿童幻想小说创作提供民族性的养料。基于内外资源的不平衡的事实,李东华曾提出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结论:中国幻想小说是“无根”的文学。“无根”意味着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由此带来的是,幻想小说无法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确实,如果只是在儿童小说中添加一些诸如“魔法”“巫师”“吸血鬼”之类的名词,而不能立足于“中国式的童年”来展开想象,那么这种随意的嫁接不仅与中国的儿童有隔膜,实际上也颠覆了外国幻想文学本有的精神意涵。在论及中西幻想文学的差异时,谈凤霞指出,中国幻想小说追寻一种“轻幻想”的底色,气韵“轻逸”,少有西方幻想文学中“繁复”的人性纠葛。事实上,中国幻想小说这种轻逸的姿态的出发点是要绕开严苛的教育主义的负荷,以此来保障想象力、解放想象力。如果能将这种解放了的幻想力夯实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广阔世界,让幻想“贴地飞行”,那么中国幻想小说才会更具生命力。 在讨论幻想小说的“幻想”问题时,曹文轩认为它不是脱离现实的胡思乱想,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思考”和“现实动机”。幻想是有限度的,幻想离弃了现实将难以施展其自由的力量。曹文轩“让幻想回到文学”何尝不是对于无边幻想的一种纠偏?当幻想回归到“文学”的正道,幻想小说才没有溢出整个文学系统。同样,当幻想在现实中飞升,幻想小说才不会成为“无根”的文字游戏。真正优秀的幻想小说应植根童年,以理解童年为基点去开掘“人类的精神文化”。唯有让现实与幻想“双翼舞动”,才能驱动中国的儿童幻想小说真正走向儿童、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