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读 | 张爱玲,在清醒的文字中写尽人世苍凉
作家陈克华曾说:“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她才情斐然,紫罗兰杂志主编在看到她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便惊呼:“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小说!”贾平凹说:“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王安忆也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
张爱玲的佳作,写尽了最绚烂也最苍凉的风花雪月、写透了最真实也最复杂的人性。在阅读她的作品后,我们似乎了解了这位女性为什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自己的文章》: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经常把自己贬为一个卖文为生的匠人,她的这一姿态和立场,实则是对远离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文人故作姿态的清高孤傲形象的否定和改写。对张爱玲来说,对读者趣味和市场因素的迁就,除了文人“为稻粱谋”的实际生存需要,客观上也是对当时革命文学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抵制。当面临文坛对她不革命的批评和指责时,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为自己申辩道:“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理直气壮地以爱情为题材,她看到了爱情宽广的辐射面,看到情爱能深入许多重大问题,触及革命、战争等无法达到的人性和社会的深度和高度。张爱玲笔下虽然写的是情和爱,但隐含的却是人性,是财富,是伦常,是习俗,是战争,是人生的种种封锁围困。在她的文字中,人生软弱阴柔的一面,往往比刚硬更能代表人性的真实。张爱玲通过婚恋主题,把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种种复杂性和可能性在历史变迁中动态地展现了出来。
《沉香屑·第一炉香》:低到尘埃里的花,结不出爱情的果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过这样一句话:“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但是,低到尘埃里的张爱玲,并没能等来胡兰成的爱情。
葛薇龙也是如此。
在姑妈梁太太举办的酒会上,葛薇龙遇上了风流公子乔琪乔,而后便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对方,并且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可偏偏,乔琪乔于葛薇龙而言,是火之于飞蛾——是光亮,更是死亡。为了留住乔琪乔,葛薇龙一次次放低姿态,甚至不惜将自身变成“造钱”的交际花,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沉沦堕落。
她不懂得,低到尘埃里的花,结不出爱情的果。这件事,幸或不幸,自有分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明白:不是委曲求全就能换来圆满,也不是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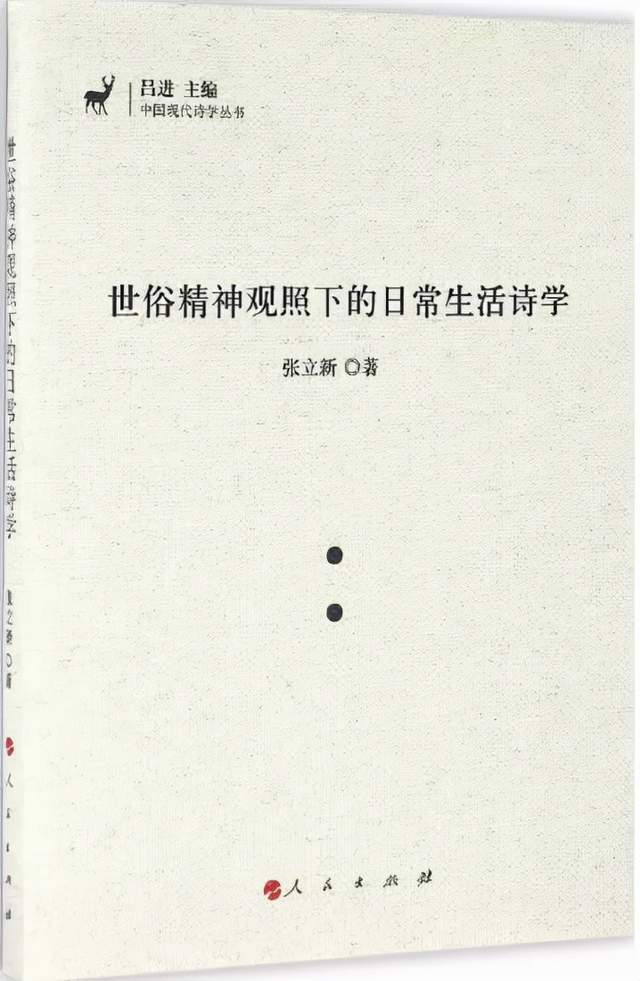
《公寓生活记趣》: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终会在有一方温暖的家里消散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尽管如此,但回家的渴望还是弥漫在张爱玲文学与人生中那无处不在的舞台布景中,一切的戏剧在这里热闹或凄清地上演。“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
那本没有生命情感的机械——一辆衔接一辆的电车,在从公寓房里的张爱玲那一双渴望回家的眼里看来,却像是“排了队的小孩”,“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从“电车回家”这个温情温馨的动人场面,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张爱玲寄居在公寓房里那颗渴望温暖却漂泊无定的孤寂荒凉的心。

《倾城之恋》:当失去一切之后,才能够洗尽铅华,露出平凡的生存本相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东西混杂、传统与现代交战、价值标准混乱的环境中,再加上她个人的家庭背景也是中西合璧的,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也处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境地里,在错乱冲突中选择,进进退退。
《倾城之恋》的女主角——离异归家的六小姐白流苏在一个所谓的“诗礼人家”、一个跟不上时代节拍的旧式家庭,在陈腐冷酷的氛围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娘家遭人嫌弃,最后却等来了她的“良人”范柳原。其实仔细说来,范柳原绝对算不得良人,他游戏人生、处处拈花惹草,哪怕最初喜欢白流苏,也不过因为她面目姣好罢了。
最开始不是单纯的两情相悦,只是相互利用。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这对互相算计的男女在动乱中相依为命、彼此依靠时才明白:原来,人这辈子,财富、地位、名利全都是虚无缥缈的。
刘再复曾评价张爱玲说:“她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拼命争取自由,但总得不到自由。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屏风上的鸟’、被‘钉死的蝴蝶’,想象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纬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纬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当什么都完了、什么都毁灭后,当人类自己又亲手毁灭掉自己的文明后,藏在文明套子里的人才能够打破各自心灵的枷锁,褪掉外在内在的束缚而彼此沟通、袒露真心,才能够洗尽铅华,露出平凡的生存本相。这是什么样的人生逻辑,又是何等沧桑的历史感。从来与历史不沾边的女人,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女人,却成了“倾国倾城”的历史的主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倾城之恋》结尾这巧夺天工的惊人一笔,使这对男女由情爱走向婚姻的“圆满的收场”融入了阐释不尽的审美的、历史的、人生的无穷意蕴。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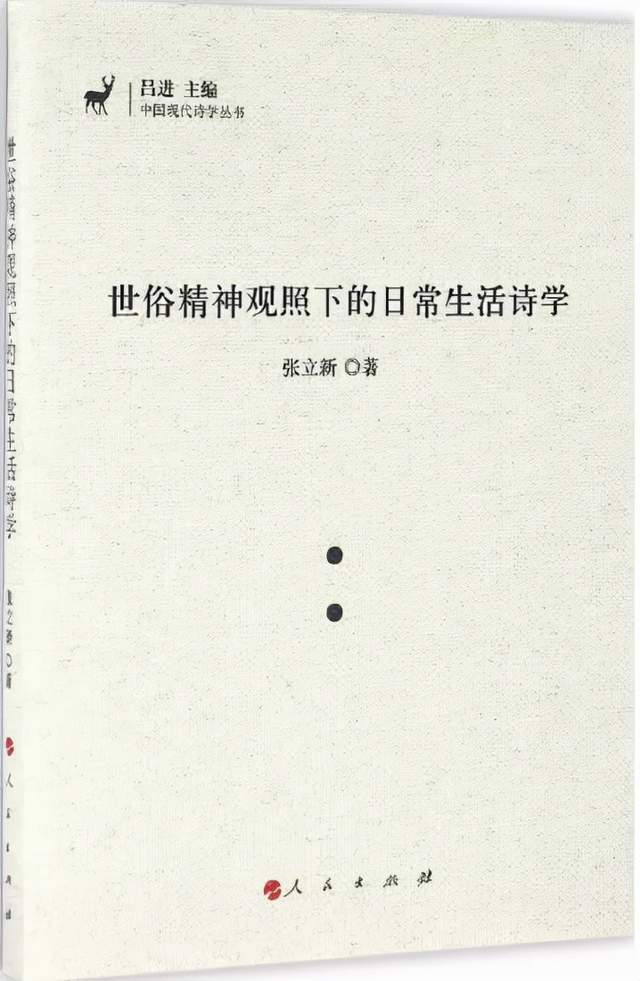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