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卡罗尔·希尔兹 说明:本文对原文有所删减。“艾”,原文为“EW”,即Eleanor Wachtel,以下访谈录中的采访者,亦是卡罗尔·希尔兹多年的朋友,因采访希尔兹而结下友谊。下文简称“艾”。“希”,原文为“CS”,即卡罗尔·希尔兹,下文简称“希”。  卡罗尔·希尔兹 “艺术是制造” 亨伯作家学院 多伦多,1998年10月 艾:据我的理解,您喜欢书写表面之下的裂缝,通过这些裂缝揭示我们生活中令人恐惧的脆弱,也洞察其中的黑暗。不过,我们更经常读到的是,您所书写的这些裂缝是某种超验时刻,它们以一种神奇方式切入、穿透我们日常生活体验,您称之为“不经意间的顿悟”(random illumination)。您能否谈谈这些顿悟是如何出现并影响您的生活的? 希:我总是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超验时刻——这个观念可能有点伤感。我曾经写过一个吓人的故事。新英格兰地区某家庭主妇在一天晚上洗碗碟时,无意间发现手腕上的肥皂泡沫汇聚在一起,上面吸收的光线形成许多小彩虹。一瞬间,仿佛她的一生汇聚在了一起,她理解了宇宙的意义。于是,她把丈夫叫到厨房,与她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她丈夫却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和心理医生。这就是这些稀有的超验时刻可能带来的麻烦:它们很难形诸文字,就算形诸文字也会被视为疯言疯语。我想,这正是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超验时刻的主要原因,更不用说共享这份体验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带来了超验,通常是生活中的各种因素神奇地共同作用而促成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学着去品味这些超验时刻,这样的话,在那些不那么超验的时刻,我们可以主动召唤它们。 艾:当我阅读琳内·沙龙·施瓦茨【琳·沙·施瓦茨(1939— ),美国作家,尤以小说闻名。】的《读书毁了我》这本有趣的书时,或阅读其他任何书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心头,这就是:为什么要读小说?除了喜欢精彩的故事、替代性体验他人的不同人生或进入他人生活的内核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希: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近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你写小说的时候,有时难免会对这项事业丧失信心,然后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要读小说?在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中,人们自我沉浸于所谓“幻觉”的权利是受到质疑的。我总想起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句话:“现实”是语言中唯一需要总是用引号的一个词。所以,关于幻觉与现实的观念是很有趣的。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读小说并不是逃避,相反,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必要扩展。在我看来,很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即便我们中的那些幸运儿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工作,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地方,经历有限的体验。通过阅读小说,即使我们只是身居一隅,也可以开启无数的旅程,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如我的小说《小小的仪式》中的人物朱迪丝·吉尔所说:“我的人生对我来说远远不够。” 艾:在上周的《环球邮报》上,您写了一篇关于莫德·蒙哥马利【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1942),加拿大作家,著有包括《绿山墙的安妮》《安妮的恋曲》等安妮系列小说。】的《日志》的评论,在文章的结尾,您谈到“艺术的超验与治愈可能性”,能请您聊聊写作对您本人意味着什么吗? 希:我经常思考关于艺术的问题,比如:谁创造了艺术?谁来定义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创造艺术又意味着什么?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具备将头脑中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诉诸笔端的能力,我才得以避免情感崩溃。现在我还具备这种能力,这至少让我感到自己还能做点什么。电影导演让·雷诺阿曾这样描述艺术:艺术是制造。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也与我的思考不谋而合。艺术不是看着什么并学习如何赏析它;艺术就是制造。我自己拥有的这种制造的能力,给予我的生活一个中心;否则,我完全不可能找到人生的中心。所以,说写作是“治愈”,是因为这是我的心灵可以前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庇护所。当然,它并不总能完美地发挥作用。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行了好运,第二天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倒霉;你也难免碰到特别糟糕的日子,比如你写的任何东西都与你头脑中的完美之书不匹配,但一点一点地靠近这本完美之书所带来的愉悦,可说是千金难买,很少有其他东西能够令我如此愉悦。 艾:对于我们这些不能写书,即不能“制造”的人来说,应该如何面对情感崩溃呢? 希: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完全掌握艺术与手艺之间的伟大对话。坦诚地说,我认为烹饪一顿美餐,或者把草坪收拾得漂漂亮亮,都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活动。甚至在餐桌上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既愉悦他人,也愉悦自己。这也是在“制造”。 “被惊诧扼住咽喉” 国际作家节 多伦多,1999年10月 艾:您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故事《盛装共赴嘉年华》审视了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演绎着生活中不同的角色。小说描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推婴儿车,买花,拿着一个芒果,但这些小事让他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在寻找什么? 希:我们每天在出门前,都要穿着打扮一番。每天早上,我们必须起床,必须再造自己,为此,我们需要服饰来帮忙。故事的灵感来自我的一个女儿,她在约克大学上学,学生生活过得很辛苦。偶尔有人邀请她共进晚餐,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时,她会一大早去买一束鲜花,一整天不论走到哪儿都把鲜花捧在手里,直到晚上把鲜花送出去。人们看到她,会说:“瞧啊,这个姑娘捧着花呢,肯定有人在哪儿等着她。她将要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个欢宴!”此外,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妇女上班时喜欢带着午餐,但她的午餐是放在一个旧的手提琴匣子里。现在呢,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人们走在大街上,都是边走边拿着手机在通话,这也是这十年的笑话之一。大家的这种行为多多少少都有点矫揉造作,这些人边拿着手机聊天边走路,似乎在说:“你瞧,我并不孤独,我与他人是有联系的。你只能说我现在是孤单一人,但我不孤独。”这篇小说说的就是不同的人穿着不同的服饰或带着不同的物什,而他们是花了一点时间考虑这些事情的,这正是人们用来对抗这个世界的方法,天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卫,哪怕仅仅是涂上几笔睫毛膏。 艾:那究竟是为了什么而防卫呢? 希:自卫,以免遭受误会、蔑视和嘲笑,以免被别人认为很愚蠢,无法融入集体。每天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而心生巨大的恐惧,我们需要很好地抑制住这些恐惧。 艾:当您说我们每天都需要“再造”自己,我知道这句话的表面意思,但这句话究竟指什么呢?我们当然需要穿衣服,并且为怎么穿着打扮而费尽心思。 希:我想,在每个人的个性中,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要展现出来的,在我眼中,每个人都很脆弱。每一天或每一个小时,我们都有那么一两分钟丧失了对这个核心的感知。我们对一天的安排失去了信心——这尤其会发生在一天中的早上,也就是当我们刚刚起床,还寻思着昨晚的梦境,努力清醒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是谁,学着再造自己,给自己一点点勇气。 艾:这让我想到了您最近的小说《拉里的家宴》中的主人公拉里,他老觉得自己是个骗子,随时会被人们揭开面具,真实身份会被识破。当他拿起一件西装上衣,发现这件比他身上穿的更好时,他会没有勇气穿,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衣服,这衣服与他不匹配。您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希:是的,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当然,最好的例子就是周四的晚上,当国际作家节向我致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骗子。当然,女性对这些感受会更加敏感一些,她们觉得他人目光如炬,会看穿自己。但是,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总会有些偶发事情容易引发这种感觉。 艾: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是《盛装共赴嘉年华》,而最后一篇是《脱衣》,讲述一个组织裸体营的男人的故事。是什么让您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 希:我想也许这会是很好的故事构架方法,而且我一直很想写关于裸体营的故事。 艾: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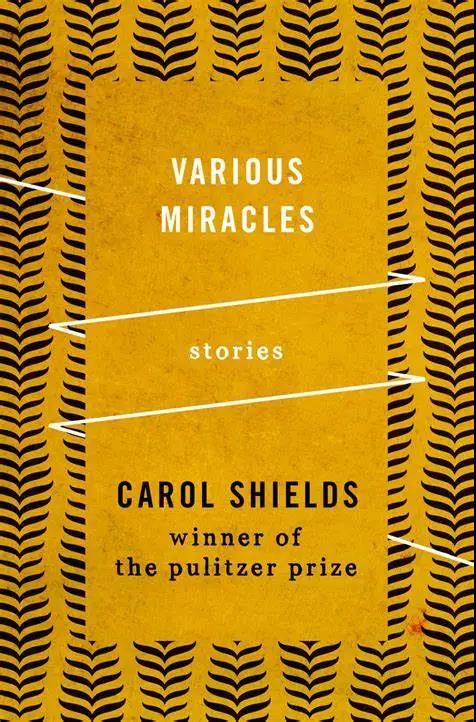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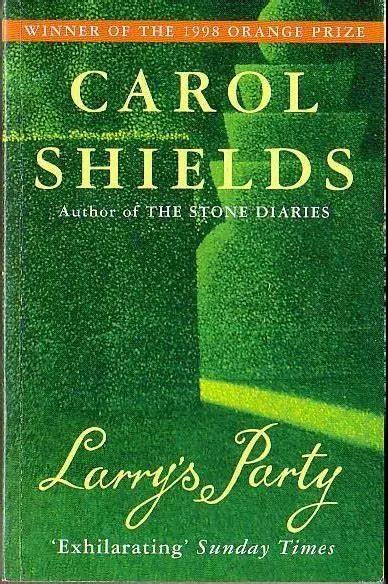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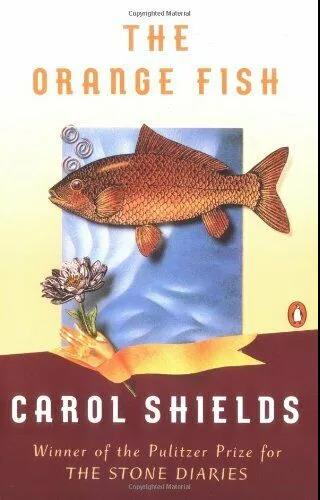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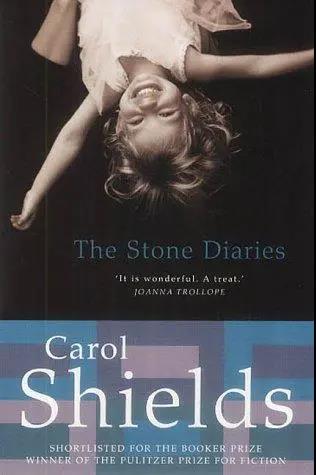 希尔兹部分作品 希: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和女儿莎拉在海滩散步。我们先路过一个普通海滩,人们都穿着泳装,过一会儿我们经过另一片完全不一样的海滩,也就是裸体者海滩。莎拉觉得,这些裸体者躺卧的时候,她还能接受,可是当他们光着身子打排球跳来跃去的时候,就有点过分了。当然,我得承认——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我们后来也加入到了他们之中,这就像一个仪式,因为你突然感觉到你身上的衣服是多余的。我记得当时我竟很奇怪地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你发现每个人的躯体都差不多——不过是有些人更壮一些,有些人更高一些,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该凹陷的地方凹陷,该凸起的地方凸起。你会有种返璞归真之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服饰赋予每个人一些独特性。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的父母是裸体主义者,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是个可爱的词——每每父母把她拉去参加裸体活动时,她都感到异常尴尬。当你看到你的父母、其他成年人还有孩子一起裸体的时候,你难免会惊诧。我只是想对此作些思考,也就有了这篇小说。 艾: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作家琼·布莱迪,她的父母都是裸体主义者。她后来爱上了母亲的一位朋友,她说这男人对她的主要吸引力是他穿衣服。 在您写的故事中,那个组织裸体营的男人的妻子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衣服。事实上,她家的房子里到处堆着各种衣服、毯子和帘子。您是在安排一个衬托性的形象。但是,我想问的是,您讨论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什么? 希:在故事中,男人问妻子能否在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的某一个月不穿衣服,与他一起参加裸体营,她出于对丈夫的爱,照做了,但她一直心存怨愤,因为丈夫让她做的这件事令她尴尬,有违她的性格。可是她还是照做了。我这里要谈论的正是任何婚姻中都涉及的讨价还价式的交换,而小说描写的正是这种交换。 艾:在小说《脱衣》的结尾,叙述者终于意识到,“自然中的万物在它们的种子阶段都是弯曲的,有很多节杆的,所以不可能长出完全直溜之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希:我想,我要表达的是,要选择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你需要一下子放弃很多东西。我们本来的生活方式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复杂,并非你简单地说一句“来吧,我们脱去衣服,过一会儿不一样的生活”就能万事大吉。这涉及我们的自我认知。裸体不但违背了我们应当具有的端庄品质,还与我们以往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中他人的认知相抵触。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迈出这些步子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认知会受影响,并且很可能会心理失衡。 艾:听您谈论自我认知、我们是谁这样的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您所有的作品中经常涉及的问题: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谁。为什么您对这些问题如此着迷呢? 希:我想这些问题令每一个人都着迷。人们常说:“与自我的情感保持联系、与自我保持联系。”我常想,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中说到的“自我”指的是昨天或前天的自己吗?在我看来,“自我”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自我”一直在变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碰撞中,“自我”在此一刻与彼一刻并不一样。我并不确定是否存在所谓的“具有稳定性的自我”。这就如同思考诸如“加拿大是什么”“加拿大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你也知道,在过去,人们都热衷于定义自己的国家,最后人们都放弃了。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身份,或者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找寻身份。我想这同样适用于对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我们无法预测,在面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之时,我们会如何应对:是耸耸肩,坦然接受重大变故,还是直接崩溃倒下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预测我们对未来的反应。 艾:最近您说过,您感到自己寄居于“一个新的自我,一个仍然被惊诧扼住喉咙的陌生人”。 希: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刚刚得知患病的意外情况的那一刻,我完全被震惊了,几乎无法呼吸。慢慢地,我试着学会接受——人们都说与癌症共生,总有办法与癌症和平共处。我想,你千万不要去读那些所谓的统计数据。我需要找些东西来分分心,这也是我在早期所做的。我尝试看些电视节目,以前我从不看的,但看电视的结果就是我再也不想看电视了。我转而开始读小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读小说是一种逃避。我从不认为读小说是逃避生活,恰恰相反,这扩充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当然,还有你的好心相助,我最后走进了阅读的计划中。 艾:您曾经写过某种类型的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特别是女性艺术家,他们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谁,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您自己而言,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那样,您是在许久以后才发现自己能成为艺术家的,您能说说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吗? 希:我想这首先得归功于我对语言的热爱吧。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种热爱:对我来说,语言比实物重要得多。我现在写作时仍能感觉到,我对语言、声音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纳博科夫所说的小说的主题(aboutness)的兴趣。风格与素材,二者密不可分,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字是如何在头脑中酝酿出来并形诸笔端,你是如何赋予其声音或令其手舞足蹈,或者你是如何使其比在之前的版本更加意蕴悠长。我喜欢在修改中让自己的文字比初稿更加精彩。 艾:最近您曾说过,小说归根到底都涉及到找寻我们真正的家园,要么是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家园的感知能力,要么是一开始我们就被安置在了错误的地方。那么,请问这种找寻是一种永无止尽的找寻,像奥德修斯的回家之旅那样,还是说最终人们都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家园? 希:我并不认为人们总是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家园。但我越来越相信,小说——在此我不想使用“严肃”小说(literary novels)一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一定份量的所有小说,都涉及这种找寻。当我说“家园”时,我指的是这样一种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作为,我们感到安逸舒适,当然我们还能够在这个地方自由地发挥创造力,与他人和谐共处,这才是我们的真正家园。“找寻”意味着渴望归属感,人们在有生之年并不总是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家园,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找寻。约翰·契弗曾说过,他想象自己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心静如水,当然手中还拿着一本书。但是,他从未抵达这想象中的场景。 作者简介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加拿大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就学于美国,因嫁给加拿大人入籍加国,成了加拿大作家,并对加拿大文学身份的国族性与历史性的建构贡献良多。希尔兹22岁即做母亲,育有一子四女,带大儿女后方投身教学与写作,因此迟至41岁才发表小说处女作。但她的作品数量颇丰,种类也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传记、评论都写,而且写得都不错,获奖不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斯通日记》(1993,又译《斯通家史》),此书曾获1995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和加拿大总督奖。 希氏作品就内容而言最显著的特点是家庭性(domesticity),即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历,如爱情、婚姻、母女关系中的微妙与困境,以此揭示人生随处可见的大小悲剧,但又时常携带一抹明亮乐观的底色。 李博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