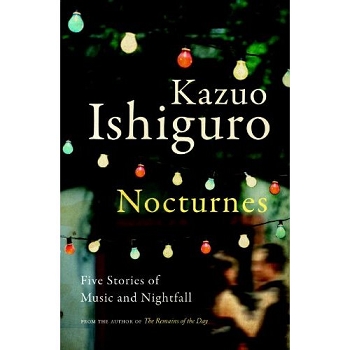 《夜曲集》 [英]石黑一雄著 Alfred. A. Knopf出版社 2009年9月北美第一版 《纽约书评》2009年10月22日那期有一篇介绍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新作《夜曲集》(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的文章:《时雨时晴》(Come Rain,Come Shine),篇名套了书中的一个小说名,又化自一首同名歌曲,石黑一雄偏爱的版本,也许正是我边写此文边听的瑞·查尔斯(Ray Charles)那悠悠散散、柔肠百转的唱腔。 这篇评论,我特意压至昨晚才读,读完后不知该庆幸,还是惆怅。也许庆幸的是,未受其影响,是读完全书再回头的。全篇大约占据书评稿两大页,书中故事逐一拿出来复述、浅析。倘若先读了此文,大概也就不必看书了。不过,惆怅的症结也在于此,反过来想想,这篇评论是不是已经足够,我何必浪费时间再读书?这样的鸡肋矛盾,对待石黑一雄,怕是很稀罕了。读《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和《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我大多数时间一气呵成,根本放不下书的,而这本中篇集,却看得停停走走。 起初看到标题,我很自然想起鲁宾斯坦的肖邦,读书时也特意设为背景音。但凡与音乐有关的题材,我总是有点跃然期待,但也不晓得究竟预备读到什么感触。不过迄今为止,倒是失望居多。前一阵拿到艾里克·艾玛努约·施密特(Eric Emmanuel Schmitt)的《莫扎特陪伴我》(Ma Vie avec Mozart),几页下去,直欲掩卷。一开始就是个为赋新词的多愁少年,父母健在,家庭温和,不知道他做什么要死要活,直至听得一阙费加罗婚礼的咏叹,好似胖歌者隔空对他伸开大腿。自然人人都有表达情绪的譬喻方式,但也许我早已过了青春萌动,听莫扎特是喜欢他的自然与纹理,还不至于联系到肉感救命草。 比照一下,石黑一雄聪明得多,他并未直陈音乐给他的感受,乐理更一笔带过,他选择了浓情怀旧的蓝调、爵士、英美民谣,埃尔加、拉赫玛尼诺夫只是蜻蜓点水充任情绪的导引。他写的并非音乐本身或“之我见”,而是和音乐擦擦边的人们的心境,并且一律收掩于夜幕方垂之际,是以书的副标题所谓“关于音乐”、“黄昏时分”,非常贴切。几乎所有主人公,都处在郁郁不振的边沿,吉他手、萨克斯手、大提琴手,除了最后一个故事用到上帝之眼的视角,其余全部自述,仿佛什么都不在乎传递,梦呓一般回顾灰色生涯里的浊浪。所以上扬的肖邦其实是不大适合的,那种乡关何处,烟锁迷楼的风致,还是婉转爵士比较对搭。 在布克奖得主、甚至我读过的大部分英文作者里,石黑一雄的文笔都算非常特别的一位。我只在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对话里,看过如此浅简的词句,大概不需要托福,都能看个清白。而这么素,评者Claire Messud冠之以banal的文笔,却总蕴蓄了一股涓涓流势,让你情不自禁跟着他走下去。比如这样的话:“我们串了一遍那首歌,它充满了漂泊与别意”(We went through that song, full of traveling and goodbye),我就想不到形容一首歌,会用到traveling和goodbye这两个词,但也恰恰这两个词,仿佛千帆已过尽。又如这段给吉他手的建议:“你一定得告诉他,就是这种音质,你就要这样的音效环境。如此一来,听者听到的歌曲便恰似我们俩今日耳闻,被清风推送,正如我们步下山坡时的乐声……”(You must tell him this is the sound, the aural environment you require. Then the listener will hear your song as we heard it today, caught in the wind as we descend the slope the hill...)在下风当口聆听飘来的吉他声,这么细腻的音效,也亏他写得如此清爽。随处可拾的再如:“第一缕秋风划过的痕迹与不可理喻的咖啡价格,确保了颇为稳定的顾客光顾量”(The first hint of an autumn wind and the ridiculous price of a coffee ensure a pretty steady turnover of customers),平平淡淡,却已有些秋风清秋月明的索然,很容易就带人入境。 很可惜我不懂日文,只看过为数不多几位日本作者的书,中文本大都罕见花俏,文字像清酒一样淡,像还没醒转的柔板。石黑一雄笔下的一个故事里,主人公折返英伦,寄宿姐姐家,那儿也是他的出生地。山乡环绕,客舍迎人,他帮忙看店,感到既亲切又生疏。如果换个场景,换个语言,我会以为是村上或吉本的笔触了。一直只读石黑的书,没挖过八卦,不知道他的文笔是不是还附着一定程度的日系渊源,虽然我打赌,英文造诣很高的人,也未必能写到他这么平静流畅。 这五个故事或有牵扯,比如刚才那位返家浪子,另外一个场景里去救火大学同窗的婚姻。我以为独自发展,或者串在一起,都可能气象转迁,成就一个定局。可是石黑一雄就任它们散在那里,不加点拨,好像随手素描稿,又或者即景日记簿,不知道这算不算从感情浓挚的创作里淡出的一段小憩。当然也并非独立故事本身过分松散,其实每一篇,都还是有点紧张的影子,其中一篇说两个做了整容手术的人面缠绷带,披卫生褂,夜里到处荡,为了去住店会从火鸡肚子里掏一座貌似鳄鱼的奖杯,读者看了都要哭笑不得,一方面还担心会不会巡警突袭。这么荒诞的波折,简直有点类似我比较怕的黑色的阿美丽·诺东(Amelie Nothomb)。我不晓得作者讽刺主人公的同时,是不是还在自娱。 我晕乎乎翻完全书,打开《纽约书评》时,不是不佩服Claire Messud的。老实说,除非一一罗列,我不知道还能如何写那么长的评价。她说的大调小调更迭,重复的韵律主题什么的,我是压根儿没感受到,音乐情绪,除开月下荡漾在大运河上的贡多拉与伤感吉他,统共没有几笔,故此很怀疑是否有这个必要强自解释。写到末梢,她的想法倒是和我不谋而合,亦即石黑一雄的文笔更该在更长、感情层次更丰富的小说中鲜明起来,而非止于这样不疼不痒的音乐白描。当然,因为他是石黑一雄,所以我们又不谋而合地承认,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没读懂这些看似浅显的短章。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