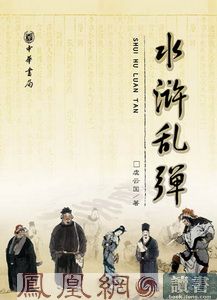 虞云国著/中华书局/2008年12月/24.0/平装 早年读辽教社的《万象》杂志,最喜欢其中虞云国的"浒边谈屑"专栏。"浒边谈屑",顾名思义,即和《水浒》有关的一系列小品随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浒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不下水,不谈论小说本身,借小说的某些细节做由头,生发开去,讲与这一细节相关的社会生活",而"谈屑","谈的都是不成片断的生活风俗,自知这类随笔无足轻重,不过屑末饾饤而已"。 形容自己的文章"无足轻重",是"屑末饾饤",当然是文人学者的自谦之语。实际上,虞云国解读《水浒》,视角非常独特,可谓自成一家。他的水浒系列随笔,不像马幼渔的《水浒论衡》那样,研究《水浒》的版本流传和布局结构,也不像余嘉锡的《水浒三十六人考实》那样,专注《水浒》人物行迹的学术考证,更不像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那样,从社会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民众生存状况。虞云国认为,类似的纯史实考证工作已经基本被前人完成,要解读《水浒》,必须另辟新路。他所说的新路就是,集中考察书中涉及的人情风物,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素养为基础,使小说和史实两者互证。 将这样的互证以小品文的形式灵活表达出来,一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这既避免了学术考证的枯燥冗长,又增加了小品文的可读性和文化含量。他的"浒边谈屑"系列,考察了《水浒》中出现的各式人情和风物,从历代古籍笔记中寻找蛛丝马迹,最后将这些掌故在纵向的历史中贯穿开来。这样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水浒》轶事,在中国尽管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但如果我们不愿仅仅停留于这些表面的情节和人物,有意进一步探究,就会或多或少的陷入某种疑惑。比如"智劫生辰纲"中提到的"太平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比如不少水浒人物的面部都有刺字,那么这在当时对一般人而言,代表着一种怎样的屈辱?再如书中数次提到的流放犯人的"沙门岛",究竟是一个何等险恶的去处?在虞云国的这本书中,以上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作者以小见大的生花妙笔,举重若轻,即使博征旁引繁复细密,读来都非常有趣,让人深深折服。 作者这种解读《水浒》的方式,意义还不仅仅在此。我们知道,百年间和《水浒》有关各式文本,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快餐阅读的风生水起,散居江湖的水浒爱好者们,更乐于用现代人的视角审视这部古典名著。他们的作品,多半冠以"黑话"、"大话"、"闲说"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内容多半集中于对水浒人物性格的分析,揭示故事暗含的"帮会"、"黑幕"、"潜规则"等等灰暗主题。这样掺入太多现代元素的快餐水浒或许在初读时会博得一笑,但仔细考量,大多结论先行,内容为观点服务的痕迹明显。这样的解读有意义与否暂且不论,重要的是,如果《水浒》、《三国》这样流传几百年、被尊为 "四大名著"的古代顶级文学,含有的仅仅是这些人性幽暗和诈术权谋,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非常悲哀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虞云国先生的这种轻松的解读方式,超越文本,捕捉字里行间蕴含的文化。通过他的解读和互证,我们发现《水浒》的作者对他所身处的时代,有着惊人的细密观察。我们也会发现,《水浒》中的每一风物都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和精妙。我们得以在他的帮助下,从文化层面切入《水浒》和宋元时代,清楚的窥到当时社会风貌和人间万象。 在读《万象》的那些年,每篇"浒边谈屑"我都反复阅读,咀嚼不已。掩卷遐想,眼前经常浮现出一个清明上河图式的场景,汴梁城内御街宽阔,樊楼高耸,商铺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一湾湖水围绕着山寨,村落间酒望子斜飘,古道上一台山轿和推太平车的贩枣商人擦肩而过…… 当时一直盼望着这些随笔能够结集出版。果然,2008年岁末,中华书局推出了"浒边谈屑"的结集。尽管出版社为迎合市场,将书名改为更直白的《水浒乱弹》,但就其内容而言,和那些真正"乱谈水浒"的江湖读物相比,高明十倍还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