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书单推荐人 王川 爱书人,近年来因为读书戴上了眼镜。
我读书的岁月用一句话说,就是“很漫长了”,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犹豫。在考大学之前,我不能随意而放肆地读我想读的书,在我可以随意而放肆地读我想读的书的时候,生活的一切扑面而来,使我放下书本去应付那些席卷而来的“生之困境”。现在,仿佛一切安定下来了,人也老了,“读书无用”的思想很容易侵害自己的内心了。好在我还有几分定力,像一头老牛,在书本的干草堆里咀嚼着生活和生命的滋味。我现在做的主要工作是,把我多年的藏书好好清理一下,我的意思是,打扫一下垃圾,挑出不多的几粒豆子,在细嚼慢咽中闭上眼睛,做自己想做的美梦。
阿尔多·李奥帕德说过:“免于恐惧的生活,必然是贫瘠的生活。”贫瘠,指的是物质而非精神。精神的丰满和滋润可以带来支撑生命的最佳营养,而这个浅显的道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了被人取笑的东西,那么,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呢?除了资源被开掘殆尽的世界,留下最多的肯定就是最为贫瘠的心灵了,他们活着,快乐地活着,却不知道危机的临近,更不可能获得生命究竟的秘密与幸福,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奥尔罕·帕慕克曾经描绘过土耳其的社会,说他们国家没有图书馆,更没有读书的人,谁要是读书,就被认为生活不正常,而读书者,则很怕被人看作是矫情地显摆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我们的情况似乎比土耳其乐观得多,每年大量的图书上市仿佛显示了图书市场的繁荣和读书人的众多,然而,拨开这些耀眼的虚光,看到的是更多的营养缺乏甚至是属于垃圾一类的东西——这是利润催逼下的市场运行,与真正的读书早已相去甚远。
但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用心灵的需求去挑选,谁会否认,一个个生命的究竟会在美好的文字中慢慢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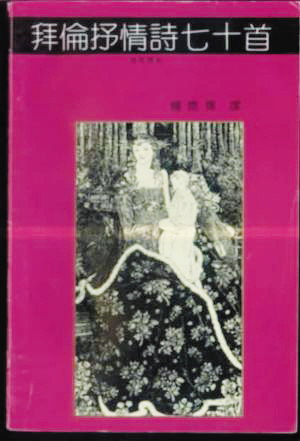
《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杨豫德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年12月
《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至今,我仍然执拗地认为,拜伦的诗是最美的诗,是人间留有的天籁之音。也许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人生最早读到的西方诗人,那一年,我十四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年纪。一位老诗人送给了这本书,使诗歌的灵光第一次开启了我的心扉,照亮了我懵懂又充满渴望的灵魂。那是情感的觉醒,是初恋的滋味,宁静,感伤,带着甜美的忧郁,幻想的芬芳。今天看来,浪漫主义的诗作的确有些直白,但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而言,这些诗句足以让他感到震撼,让他感叹、流泪,记忆到永远。
杨豫德先生的译笔是那么高雅,且拥有着古典的韵律及华美。这样的译文今天已不多见。可惜的是,我最初读到的那个版本早已被我翻看得破旧不堪,于是,多年后又买了一个1991年的译本,作为对失去的美好时光的纪念。

《永别了,苏珊》 (法)亨利·特罗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10月
《永别了,苏珊》
在我看来,这本书写了人的欲望毁灭了良知而被惩罚,最后良知又终于战胜了欲望的故事。一个平庸的人在妻子的怂恿下,为了物质利益而抄袭了妻子的前夫——一位死去的天才作家没有发表的手稿,并因此步入上流社会,受到人们的追捧。但此后他再也写不出被出版社认可的作品,他受到了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的冷遇,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最后不得不顶着压力承认自己的抄袭行为,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但得到的却是更多的误解。他只好永远地离去,与妻子苏珊分手。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天才作家给了他一切,又终于剥夺了他拥有的一切。欲望也许可以使人暂时得到拥有的快乐,但如果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和劳动获得,最后的结果仍将是两手空空,甚至还会被人鄙弃。上帝是公平的,它能看透人间的所有伎俩。他把这种能力非给了人类,那就是良知——它从来不会欺骗。自欺欺人也许只是缓冲了惩罚的时间,却会加重惩罚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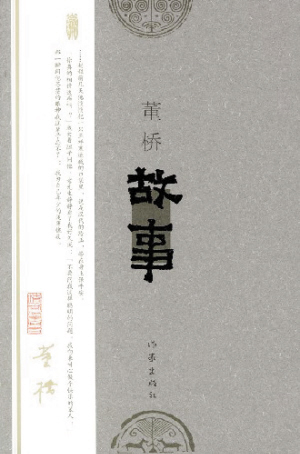
《故事》 董桥著 作家出版社 2007年2月
《故事》
夜晚,窗外的风刮得紧。躲在书房抽烟,竟读了半本的董桥。《故事》的每篇皆短小,但文字的清韵却缭绕不去。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古雅,清新,有趣。这些故事均与书画、古董的收藏有关,虽是旧时的文人雅趣,却多少让人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历史沧桑、运命沉浮。作者的亲历亲闻,以及识见的透彻、笔力的卓越,让文字在亲切中透出一种深邃的华美,甚或怀旧的温馨。让人竟仿佛进入了既陌生又心仪已久的早已逝去的文化氛围中,与故事中的人、物作灵魂的交流。董桥的这本书给我的印象也恰如他对老前辈小楷文言信札的描绘:“言事简淡,情谊沉实。”不过,偶尔也多出些烟桥画柳、乱红轻扬的风致来,并不枯涩。他还说:“人老了,贪恋之念渐渐渺远,缤纷之思渐渐荒芜,偶然写点心事,合该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读得出兴味:浅浅的消息换取浅浅的会心,多了嫌满,嫌浓,嫌多事。”虽不是说自己,但若不是亲身的体味,又如何这般的浅显而透彻。读书和写作,应该是和生命的热度紧密相连的,人的年纪大了,热度降低,却拥有了更高的智慧,更从容的境界,像用笔疏淡却娴熟老辣的水墨画,读它的好,却怎么都说不出。然而,董桥的趣味似乎属于高雅的有闲阶级,文中还隐约飘忽着一丝脂粉气,对于现实的人生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奇人录》 (俄)尼·列斯科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7月
《奇人录》
俄罗斯作家尼·列斯科夫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生前身后却遭受冷遇。也许他笔下那些天才、疯子、奸佞之徒和善良的君子在一个动荡时代里的生存故事并不能被人理解。就像他塑造的人物谢里万,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却长期被邻居误作恶人。列斯科夫虽然寂寞,却得到过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高度评价。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文章的格局比较小。但他笔下的人物独特、有趣。这就是价值所在。他在一篇题为《理发师》的小说中谈到艺术分几等:“一、安宁,二、崇高的沉思,三、直接和上帝交谈的幸福。”他写的是一位“为死人工作的艺术家”对装扮死人的艺术的理解,但这样的艺术法则却可以推而广之。我看到现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他们虽是为活人服务的,却还没有那位专为死人服务的理发师对艺术的理解力强。也许同样是挣钱,“为死人工作的艺术家”永远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和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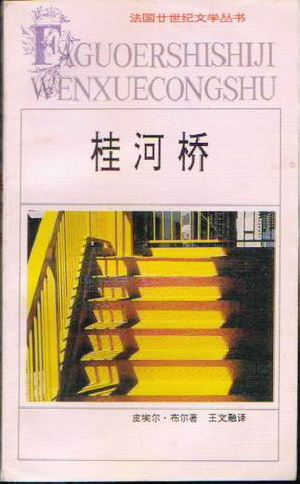
《桂河桥》 (法)皮埃尔·布尔著 王文融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
《桂河桥》
我没有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也许电影会比小说更好看。在一般人眼里,尼克尔森上校是难以理解的,面对战争中的生死对抗,只有敌我双方的你死我活,而不可能有凌驾于其上的浪漫主义的“原则”,比如文明战胜野蛮的原则,人道战胜非人道的原则。但尼克尔森却把这些视同生命,在日本人面前,他为了保持俘虏的尊严宁死不屈;在被强迫修建通往东南亚的桂河大桥时,他开始的抵抗充满智慧,把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但当他把桂河桥视为从精神和智慧上击垮日本人的象征时,他却拼死保护了它,让自己国家的炸桥特种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是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可是尼克尔森这样做恰恰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他心中那至高无上的原则,实现了他人格的尊严,维护了一个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在野蛮、丑陋、粗鄙的侵略者面前的永不丢弃优越感。如果说战争的胜利永远都属于文明的一方,属于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正义的一方,那么尼克尔森的行为从更高的层面上诠释了二战同盟国胜利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桂河桥》也提供给我们一个独特的看待战争和人性关系的视角,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许会存在争议,就像当年我们阅读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一样,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的阅读不会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这也是今天我推荐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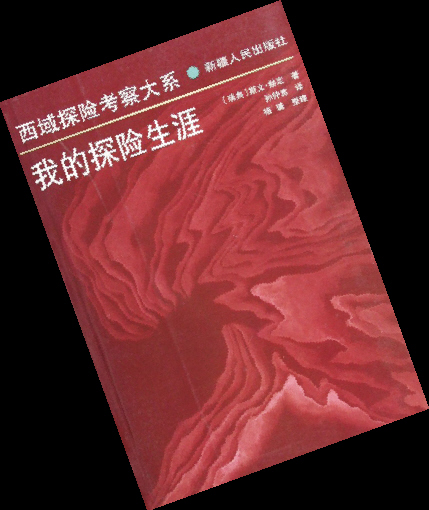
《我的探险生涯》(瑞典)斯文·赫定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
《我的探险生涯》
很长时间,我都在寻找斯文·赫定写的书,书店里已经难得一见了,这套还是在我在一家学术书店里买到的,而且是最后一套。赫定比我大整整100岁,然而人类在这100年当中进入了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赫定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历时几年才能完成的中亚腹地探险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古人的壮举了,有谁还愿意徒步穿越茫茫沙漠,在饥寒交迫中体会生命的顽强,证明人类存在的伟大?那时的交通工具只有骆驼、驴子、杨树剖成的小舟,几千英里的距离,主要是靠人的两条腿行走。然而赫定却把它当成了毕生从事的事业,在孤独和艰苦卓绝中创造了人类探险史上的一个个奇迹。那个时代,还有许多像赫定一样的探险家或掠夺者,但吸引他们的东西也许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遗失的文明和未知的土地难以遏制的了解冲动。我很奇怪的是,今天人们借助科技的支持可以走得更远,甚至已经步入了太空,但是心灵的地盘却大大缩小了,靠一己之力探寻未知世界的冲动不再那么强烈了。也许真的没有必要了,但传奇和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属于我们,我们甚至再也找不到那样剽悍、坚韧的躯体。也许这就是文明的代价。另外一个代价就是,我们也很难再看到那些探险家写下的著作,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曾经那样活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