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于故乡的文学之情 导演: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花城》的读者,也是《花城》的作者,那您与《花城》杂志是如何结缘的呢?同时,在众多文学刊物中,您觉得《花城》具备怎样的特点? 张抗抗:我与《花城》结缘较早,在《花城》刊发第一篇作品是在1981年。我祖籍广东,1980年应《羊城晚报》之邀到广东过春节。父母从杭州到广州,然后我们一起回广东老家,也就是当时的新会县,现在是江门市蓬江区。我在杭州出生,直到三十岁也就是1980年才第一次回到祖籍广东。我母亲是浙江人,我父亲九岁离开广东,也是很多年没有再回去。因此这一趟返乡后,我写了一组散文《新会印象》,这组散文就是在《花城》上刊发的。当时《花城》创刊不久,向全国的青年作者热情约稿,我就把我第一篇写广东的散文给了《花城》,后来的几十年中,我陆续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四五个作品。 《花城》的个性特点在于它的文学性、创新性、实验性、探索性。《花城》创办四十年,风格非常鲜明,属于那种辨识度很高的刊物。它始终倡导文学形式观念的创新和探索,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不拘泥、不守旧,传统与现代兼收并蓄。概括说,我想到用八个字来形容《花城》:花团锦簇、以文筑城。用“百花齐放”的包容性构筑文学之城。  纪录片截图 在我看来,每一个杂志都应该有自己不同的个性。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非常高,几大杂志创刊或复刊以后,普遍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就有“四大名旦”之说。后来这些杂志慢慢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色。差不多从80年代开始,80年代后半叶到9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文学创作的探索创新,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文学杂志也都发表了很多创新作品。但是,《花城》具有唯一性,它的探索步子更大、更集中、更勇敢,而且始终如一。有一些杂志后来逐渐地回到现实主义范畴,但《花城》依然坚持它的探索性,一以贯之,不改初衷,并且摈弃商业性操作,坚守文学的品格。四十年以来一直坚守文学的品格,可以说是一种高贵的坚持。 所以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很自然地就会把自己的作品给到《花城》。很多年轻的、不那么有名的作家,或者因其独特性而被其他刊物拒绝的作品,都在《花城》得到了发芽开花的机遇。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在《花城》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 导演:您用“高贵”这个词儿来形容,非常贴切,且十分有力量。且用“花团锦簇”来形容它的包容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您觉得这种包容性跟广东这个地域的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张抗抗:有非常大的关系。从近代史看,又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西方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通过广东口岸进入,然后北上传播的。康梁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有一个忧国求变的文化传统,是探索和开创的源头。20世纪80年代后,广东又一次成为开风气之先、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前哨,后来又有深圳这样新进的城市崛起。《花城》创办于1979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初期春寒料峭,在冰雪初融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花”,具有耐寒性、挑战性、独立性,不媚俗、不随波。它在不断的成长中,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只要看看近年的杂志就知道,《花城》把这种姿态坚持到当下,而且越来越坚定、丰富。 《赤彤丹朱》:“非红”“非梦”“非黑” 导演:您1994年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非黑》,这部作品的内容、主题和写作意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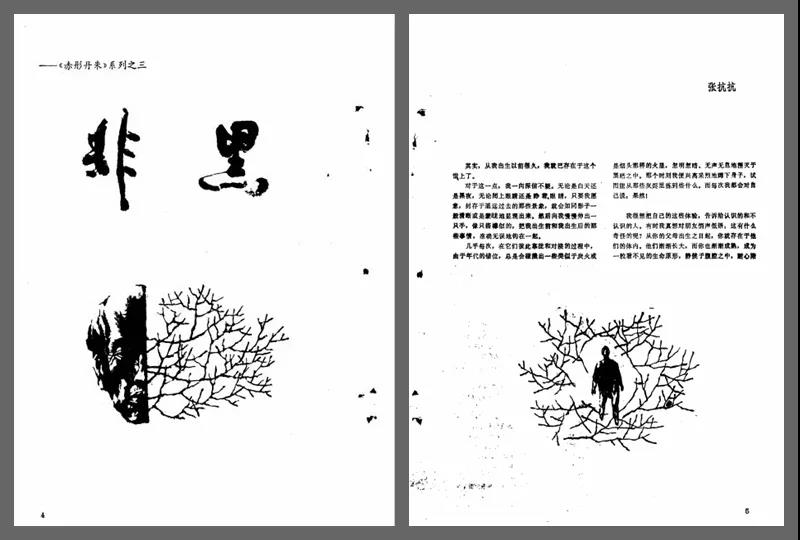 《非黑》内文页 张抗抗:1994年年底,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刚刚完成,我将它拆分成三个部分:“非红”“非梦”“非黑”。其中,《非红》发在了《收获》,《非梦》发在了《钟山》,《非黑》发在了《花城》。 这三个中篇连起来就是长篇《赤彤丹朱》,“赤彤丹朱”四个字都跟颜色有关的,都是红色,它是以我的家庭背景为原型的,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父辈历史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审视。《赤彤丹朱》于1995年正式出版,《花城》刊发的《非黑》就是其中后面的一部分,分量很重的一部分。为什么选这一部分在《花城》上发,这其中主要是因为人物原型取自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广东人,他九岁离开了广东跟随他的父亲来到上海,成为在上海的广东人。我父亲在上海长大,上海虹口区那边聚集了很多广东人,做水果、海产、鱼干这一类的生意。我父亲到了上海以后,在广东人办的学校读书,渐渐爱上文学。后来抗战爆发,他到后方当了新闻记者,经历了很多事情,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但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了不公平对待,经历诸多挫折,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获得平反。这段历史非常有内容深度。为什么取名《非黑》呢,“非黑”就是被黑,但那不是黑,是貌似黑,被黑色遮蔽的红色。在严酷的大时代当中,我们父辈的苦难无色无名,一切都在“非”中被消解了。我把它给到《花城》,也因了书中写到了广东。我的父亲九十六岁了,前段时间他又重读《赤彤丹朱》。记得当年该书出版时,他读后不满意,我不高兴。时隔三十多年,他感叹说写得真好。我反倒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 导演:《非黑》或者说《赤彤丹朱》,您觉得写得最满意的段落是什么,比如说能让您感动到落泪的,一下子把您心里面描述的东西,像画布一样就铺开了。有吗? 张抗抗:这种段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找到小说的整体布局,这是比较难的。一个小说找到一个不同一般的角度,才可以写得与众不同。《赤彤丹朱》是透过我的视角看待父辈,而不是从父辈的视角下平铺直叙。很早以前,我就在我父母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我都是知情的,这是一种贯串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视角,而且视角在不断地移动。《花城》比较喜欢这个小说,也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父亲就是《赤彤丹朱》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与母亲的经历恰恰相反的是,他的命运本该由一条红线从头到尾贯串到底,无论是出生还是对于道路的选择,他都应该始终笼罩在一片红彤彤的光芒之中。然而他却被“黑”了,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导演:此外,您在《花城》还发表了哪些作品,可否讲一讲它的创作背景和你当时的故事。 张抗抗:1992年,我在《花城》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蓝领》。这个中篇小说实际上写于1988年,原题叫作《主人的主人》,这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讲的是“社会主人”意识。我写了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生活,当时的工人希望自己选出自己的厂长,他们要求工会和厂领导对话,最后把厂长罢免了。这个小说写完后就放在那里了。到了1991年,田瑛向我约稿,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编辑,我说你拿去看看吧,我以为当时的杂志可能暂时不会刊发这样的作品,因为这个作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却没想到《花城》发了出来。我很高兴,觉得《花城》虽然是一家纯文学刊物,但很有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到了1998年,我在《花城》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瞬息与永恒的舞蹈》,写我们家养的昙花开花的情形。2006年以后,我一直在写一部大长篇,希望这部小说能再次在《花城》上发表。 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导演:文学刊物跟作家的关系就如同朋友,刊物需要作家的好作品,作家需要刊物的阵地,把作品向广大的读者展示出去。抛开刊物和创作,我们从一个纵横的角度去看,您觉得80年代的文学它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张抗抗:80年代我们称为新时期文学,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时真的是冰河解冻的感觉,那么多好作品奔涌出来。新时期文学出来一代有力量的作家,不但是有一批好的作品,更是一代好的作家,80年代文学的重要作用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80年代的文学带有太强的责任感,责任、道义、负重、使命,它要解决那些生活中用其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撞击和打通,让读者通过阅读来思考与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些人们内心的愿望和期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那个时候商品经济还没有开始,社会自由极其有限,没有更多渠道去释放人们内心的困惑与苦恼。因此当时的读者之所以如此关注文学,正因为文学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释放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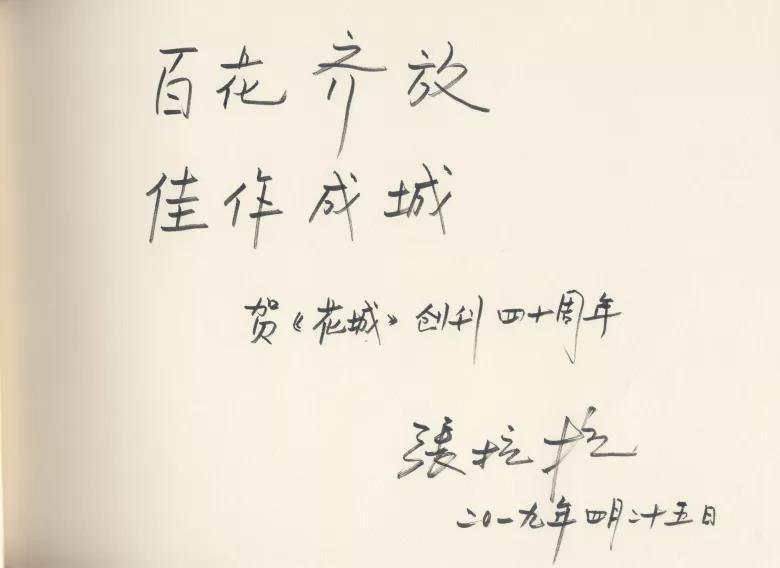 张抗抗题字 导演:不错,这个通道一方面是作家,集中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或是意愿和情感,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在当时文化产品并不发达的时候,通过文学刊物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寄托点,或是自我抒发内心的理想与主张,以及他们见闻的社会现状,从这个层面来看,80年代文学与大众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契合? 张抗抗:当然。那个时候文学的影响力,和大众的内心诉求是高度契合的。好的作品一旦面世,就马上有很多的读者对你的作品作出回应与呼应。80年代艺术文学样式相对较少,电视刚刚走进大众家庭,播放一部电视剧就能引起万人空巷,比如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文学作品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是现在的读者们感受不到的。这并不是说作品的优劣,是那个时候处于一种文化饥渴当中,现如今人们的兴趣点早已分散了。所以,80年代的文学,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文学确实成为大众诉说的一个窗口,另外一方面,文学也承担了太多的义务。到了90年代和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地改变了。我觉得,作家首先是要有良心和良知。良心和良知其实是两个概念,良心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感,良知是文学的本质。身为作家,要清醒要有见解,不要用人云亦云的错误去误导读者。文学作品如果不传递良知,就有可能传递谬知。 导演:那《花城》的良知是怎么样的? 张抗抗:《花城》的良知,我觉得是“尊崇”百花之美。尊崇基于审美,要有一个基本的审美原则。另外一个是,《花城》所负载的使命,是文学和思想并存的一种使命,就是要发现具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我始终坚持文学是要有思想的,就像一个建筑的钢筋柱子,思想就是作品的柱子,没有钢筋的东西是站立不住的,是没有力量的。 但思想性到底是指什么呢?比如从《花城》这本杂志来看,它的特点多源于它的文体创新。当然,有人会批判先锋艺术、先锋文学,或者说现代派文学—现代主义艺术太过于强调或是太讲究文本形式,过于形式化。其实不然。什么是形式?形式并不是外在的形式,形式本身就包含着内容。你采用何种形式,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个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比如我们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里就尝试过表现。人肯定是有潜意识的,现实中不可能有完全崇高、毫无私心杂念的人,那只是因为对人不了解而设计出的空想蓝图。但是如果我们像弗洛伊德那样了解和尊重人的潜意识,那么对人的认识就进了一步,也会产生新的文学意识。我在写《隐形伴侣》时,就有意识地增强这种探索性,探寻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用现实主义的描写与潜在的意识活动两个层面来进行对比。白天处在理性状态当中,呈现出这样一个人,而到了夜间,在梦里面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写作上的尝试与创新,也包含着或体现了作家对于世界和人的认知。作品的思想跟作品的文体是必然不可分割的。所以,《花城》之所以注重艺术的创新与探索,实际上是在校正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文体的形式是有意味的,文体不是为了文体而文体,这个文体是代表它的观念的,代表它对社会对世界认知的观念。 导演: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纸媒和报刊文学期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有些不错的刊物都倒闭了。我看到有文章写道,有些人觉得自己选错了行,不应该搞杂志和文学,然后一头扎到大海里捞钱去了。您怎么理解当代的文学现状呢? 张抗抗:这个很自然很正常。文学不是每一个人都必定要坚持走到底的,也没有要求说作家必须要从头到尾一直写到老,这个不是问题。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自媒体的产生,比如网络文学,让很多普通的或是有文学兴趣的、有表现欲望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每一个人现在每天都可以写作。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作家,专业作家也没有太多的优越感了。当然,优秀的网络作品毕竟是金字塔上的少数,只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能写作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那么,作家何为?这就对作家群体提出更高的要求。 导演:当下的文学应该怎样以更好的作品去面对当下的社会时代,包括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有人说文学是其他艺术的母本,包括影视、戏剧,甚至如今的抖音、快手都是延伸出来的文艺形式,那么您觉得我们文学现在的责任是什么,文学如何更加贴近当下的老百姓? 张抗抗: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其他娱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文学是灵魂的表达,是其他的娱乐形式不能代替的。今天这样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时代,对作家而言,更多的是挑战。对我来讲,我们需要对历史更深层地回顾和解析。我们处于现实与历史的中间点,文学就是一个放射体。通过反思历史吸取教训,同时观瞻未来,这是一个联动的关系。对于作家而言,现实主义作家只着眼于现实当中的某些问题,这远远是不够的。具体的现实背后还应该有厚度、深度和广度的思考,这是立体的,不可拆分的。所以,在优秀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人性的深度嵌于历史的厚度之中,互相印证。 导演:是的,有人性的东西,深刻的人生哲理的东西,总是给人指引光明,您讲得很好,谢谢了。 全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