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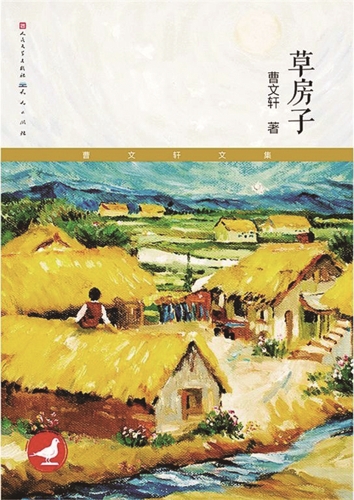  我永远难以忘记40多年前一个夏日的黄昏,白天的酷热已渐渐消退,我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乘凉,父亲为我读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相信几乎全中国的孩子都听过这个童话故事,因为它就印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我也相信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孩子,差不多都会和当时的我一样,难以自控地流下了眼泪。在那个时候,文学在启迪儿童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那时电视在中国还不是太普及,网络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而一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却瞬间跨越千山万水,让“丹麦”和“安徒生”这两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成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小乡村的孩子内心重要的一部分。 当一个孩子开始启程走向生活和世界的腹地时,让那些蕴含同情与爱心的文学作品滋润他们小小的心灵,那无疑是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启蒙。 然而时空流转,当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它就远没有当初那么单纯。毋庸置疑,文学在当下的语境中处于更为复杂的境地。当我们把文学置于“视觉世界”这个前提下来讨论它对儿童所起的作用和功能的时候,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的焦虑、危机,同时也是事实。在这个图像时代,儿童借以了解这个世界的介质是如此地多元化,而且看上去他们也确实越来越被图像所俘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文学在图像的冲击下还能否保住往日一家独大的位置。换句话说,文学在这个视觉世界里还能以不可替代的姿态存在于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这应该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悬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出版人、家长、老师等等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他们担心孩子们在影视、网络、动漫的围剿中放弃了对纯文字作品的阅读,因为在成年人的心目中,影像化带来的是碎片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肤浅的阅读,甚至是童年本身的消逝。我想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20年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运动在中国孩子的阅读生活中持久而深入地推进着。因而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和老师在同仇敌忾地限制孩子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他们像盯防敌人一样盯防孩子们上网玩游戏的时间,同时不遗余力地把纸质书放到他们的手中,甚至《红楼梦》《老人与海》《边城》《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成为高考语文试卷中必考的内容。 我想,这样的一场较量在某种程度上型塑了中国孩子的阅读生态。因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出版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那些几近天文数字的发行量,即便在图像不那么发达而文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不是说中国的孩子们放弃了他们的“读图”情结,也不是说文学在这个视觉世界里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而是二者取得某种意义上的平衡,甚至某种融合。 当我们来看各种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发布的销售数据的时候,会发现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悄悄地占据前列的位置:这是一些纯文字的作品,但又是根据某些网络游戏进行的改编。很多专家认为这些东西根本称不上“文学”,认为文字粗制滥造、毫无营养。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文学”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悄悄做的变身?如果借用体育运动的术语来说,文学过去总是以“单打”行走天下,现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它开始在“单打”之外,积极地与其他艺术介质融合,以“双打”甚至是“集体作战”的形式出现。 这一切也都在迅速地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者的选择。事实上,当我们讨论当下的儿童文学的时候,“文学”两个字也愈来愈呈现出复杂、多元甚至含混的一面。在中国孩子的阅读书单里被热捧的,既有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这样的超级畅销书,也有《安徒生童话》这样的已经经典化的作品;既有国外引进的作品,也有中国本土作家的力作,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曹文轩的《草房子》等等。这些作品轻重不一、风格多样、国别不同、年代迥异,但它们相安无事地待在一个榜单上,在共同地建构着一个孩子心理的、情感的成长。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文学在儿童探索世界中的作用的时候,也许可以用更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因为文学不是一株珍贵但稀少的植物,它是一片森林,它以婆娑茂盛的浓荫护佑着儿童的内心世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那就是在巨大的发行量的背后,我们得问一下哪些书占据了主流,孩子们书桌上摆的究竟是哪一类书?我没有做过严谨的调研,但就感性的判断来说,我觉得是那些流行的、通俗的读物在支撑着庞大的童书消费市场。 朱自强教授说过,新世纪儿童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通俗儿童文学和艺术儿童文学的分化。我并不想去比较两种儿童文学的优劣,我想说的是,在流行的、畅销的、通俗的童书占据如此大的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其对少年儿童的精神情感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类型化的童书创作值得专门认真研讨,更加深入地、心平气和地、不带偏见地理清类型化写作及其特有的审美规律。在创作和评论的双向有效互动中,让这个拥有巨大生长空间的文体能够在消遣娱乐的功能之外,承担更多的使命与责任,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