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晓原 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约百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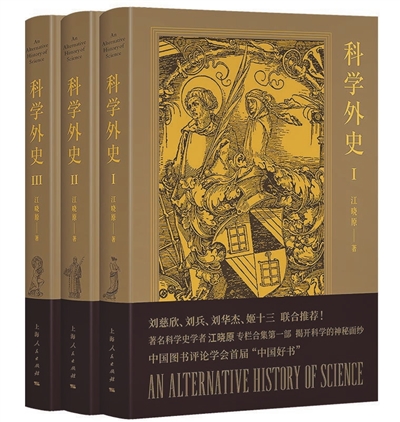 印象 新奇的知识背后 是对科学的严肃思考 一部《流浪地球》展示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也成功地印证了科学史学者江晓原的预言:“中国科幻元年,它只能以一部成功的中国本土科幻大片来开启。”这部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人重新想起2007年江晓原和刘慈欣的一场辩论:“为了延续人类文明,该不该吃人?”决定“不吃”的江晓原选择人性,他的回答昭示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态度,这些观点呈现在其代表作《科学外史》中。 十余年前,江晓原开始为科学杂志《新发现》撰写专栏“科学外史”,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宇宙太空、科技科幻诸多领域,谈及司南传说、星占学家、“超级民科”、影响因子等科坛轶闻。他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的前世今生,又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阐述耳目一新的论点。 129篇有趣而又不失洞见的文章,结集为“科学外史三部曲”,既是人人都可看得懂的通俗科学史,也是好玩易读的科普故事集,更是提倡人文精神、破除唯科学主义的现代科技反思录。 《科学外史》是一部打通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解读奇人妙事、重审科学真意的作品。江晓原的行文初看似乎离经叛道,细察则仍言之成理。比如,《重新评选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篇,心平气和地审视了传统“四大发明之说”的问题,并指出定义“四大发明”的新思路;《〈自然〉杂志与科幻的不解之缘》点明了权威的顶级科学杂志与边缘科幻文化的渊源,打破了众人心中《自然》杂志的“高冷”形象。 刘慈欣评价江晓原时说:“晓原老师潇洒地穿梭于多个学科、多个时空,深入浅出地解读孔子诞辰、费米佯谬等种种谜题。他的《科学外史》在有趣、新奇的知识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对科学和人性的严肃思考。” 现在全国许多高校的科学史通识课程,用的都是江晓原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的《科学史十五讲》,他对待科学史的观点影响深远:“从古希腊算起,科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有着成长、发展的过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刘慈欣是一针“强心剂” 让科幻小说走出了小圈子 记者:现在科幻是热门话题,您如何评价刘慈欣? 江晓原:从刘慈欣《三体》第一部初版的2008年起,我多次评论过刘慈欣,评论的文本形式不仅有报纸杂志上的书评文章,甚至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学术论文。刘慈欣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创作中,具有反潮流地位。刘慈欣是一针“强心剂”,《三体》在国内畅销,走出了科幻的小圈子,刘慈欣是中国科幻作家中第一个可以靠版税生活的人。 记者: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现状如何? 江晓原:虽然有了刘慈欣的雨果奖,有了《三体》这样成功进入英语世界的作品,有了《流浪地球》,但是坦白地说,科幻在中国,至今仍是一个既小众又低端的圈子。科幻被许多知识分子和广大公众看成是“科普”的一部分,就是编一个假想的故事,逗青少年课余看着玩,目的也就是唤起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科普的地位就已经很低了,你又是科普里低幼的那部分,那就更不行了。刘慈欣曾说过,不能让他的同事知道他喜欢科幻,如果知道了,同事会认为他很低幼,很不成熟。他藏得深到他同事跟他说,有一个写科幻的人和你的名字一样,也叫刘慈欣。由此你想,其他人如果要亲近科幻,也有这个问题。当然,这种状况也在改善。 记者:为什么科幻小说在国内一直被看作是通俗文学作品? 江晓原:就文学而言,科幻文学一直是很可怜的,严肃文学对它们不屑一顾。这个局面其实在西方国家也差不多。科幻从来没有成为精英文学。美国有很多科幻杂志,都被认为是很普及甚至低端的东西。国外的科幻大家到中国来,不愿意说自己是科幻小说作家,要说他写的是“哲学小说”,这说明在他心中,科幻也不是很高级的东西。美国小说家菲利普·迪克生前的科幻小说都卖不动,穷困潦倒,第一部根据迪克小说改编的电影是《银翼杀手》,上映时迪克已经死了,电影恶评如潮,但是后来《银翼杀手》被评为“史上十部伟大科幻电影”的第一部。 记者: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对电影的促进有多大? 江晓原:中国数百年前的幻想作品,比如《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这些作品和西方当代科幻并无相通之处。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科幻创作与国际接轨,中国的科幻作家在整体上汇入了国际潮流。我们的科幻小说我觉得并不差,但是科幻电影差太多。我们多年来在科幻这个事情上比较保守,也影响了导演选择科幻作品。从国外已有的改编作品来看,可以说对小说没有特殊的限制。倒是有些作品创作的时候就很为影视改编着想,比如丹·布朗的一系列小说,但电影《达·芬奇密码》肯定没有小说成功。 科学有不确定性 对待“民科”应该宽容 记者:您的本行是天文学,另外还研究科学史、科幻等,您为什么一直反思“科学主义”? 江晓原:我刚大学毕业时,也是个科学主义者。你想学天体物理这种专业的人,肯定是科学主义的,肯定觉得科学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直到我在中科院念科学史以后,对这个领域渐渐有所了解,我的科学主义的立场才动摇了。 记者:您有一篇文章叫《科学的三大误导》,指出科学的误导,第一是认为科学等于正确,第二是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能否解释一下? 江晓原:《科学的三大误导》这篇文章当时《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大出版社出版我编的《科学史十五讲》教材,现在国内好多高校上课用。出版社希望在新版中让我添加几篇文章作为附录,其中就包括这篇。 一个科学主义者是相信这三条的,就像我当年是科学主义者,我也相信。而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一定是对这三条都是持否定态度。我的思想逐步有个演变。我举一个自动驾驶的例子,我认为主要是立法的问题,要确定如果出事谁来负责任。自动驾驶汽车如果撞死人,是找车主还是找造这个车的公司?是界定为谋杀,还是界定为交通事故过失杀人,还是界定为产品技术故障?类似这样的东西,科幻小说和电影里早就反复讨论过。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我认为这很荒谬。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都得消亡干净吗? 记者:您如何看待科学上存在的争议? 江晓原:在科学技术受到推崇和膜拜的时代,很少有科学争议,即使有也会很快消除或止息。但是到了今天,科学争议早已经层出不穷,而且旷日持久,比如转基因食品问题、核电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许多人已经置身于危机中,还糊里糊涂不自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忽略了科学争议中的某些基本原则问题。退一步说,即便真的仅仅是“科学问题”,它们往往也绝不“简单”──因为科学有不确定性。 记者:对于所谓的“民科”,您的态度是什么? 江晓原:我主张宽容,特别是不赞成嘲笑、丑化甚至诋毁。这种态度,本身都是傲慢和偏见的产物。他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提出一些新奇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持宽容态度,要是别人发现这个说法有问题,可以写文章去驳斥。 提出中国古代“新四大发明” 把家变成一个小图书馆 记者:您认为古代有科学吗?或者说古代的科学怎么界定? 江晓原:我认为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定义,喜欢让古代有科学,那就采用宽泛的定义;不喜欢让它有科学,那就采用窄的定义。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同的定义,就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不同的意义。 记者:您曾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意见,认为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和十进制计数才是“四大发明”,这是如何考虑的? 江晓原: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是外国人提的,往前可以追溯到培根,再追溯到艾约瑟,就是说来华的耶稣会士。他们提出的时候,其实也完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但是我提那个新的“四大发明”,是有一定考虑的。一方面这些东西是比较有影响的,有体系的;另一方面它的优先权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丝绸,丝绸是有体系的,从养蚕搞成丝、印染,这一整套等于像一个产业链一样。比如说雕版印刷,有非常明确的文献,它就是中国人最早这样做的。 记者:您有很多藏书,现在还会经常阅读吗? 江晓原:我偏爱看纸质书。我现在其实很少买书,大多是出版社的朋友送的,这在学者中可能比较少见。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就发微信给出版社的老总,说你这个书我喜欢,明天他就会快递到我家里来。更多的是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他们出了这类书,就主动给我快递过来。 记者:您的阅读习惯是如何形成的? 江晓原:我读研究生时,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很多实体书店,我们一群同学把北京的中国书店附近搞成一个地图,每次决定走哪条路,一条路上能经过尽可能多的门店,然后这么一路“扫荡”过去,这是周末进行消遣的重要活动。现在虽然逛书店的乐趣没有了,但我有5万多册藏书。我把家变成了一个小图书馆,我就住在图书馆里,家等于是图书馆附带的生活设施。我现在逛书店的乐趣就改为逛我自己的图书馆,在这里消磨一下午是没问题的,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江晓原谈《科学外史》 所谓外史 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 自从2006年严锋主持《新发现》杂志,我就应邀为该杂志写“科学外史”专栏,每个月一次。《新发现》是法国的科学杂志月刊,是欧洲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以我在巴黎街头所见,报刊亭无不陈列。中文版在样式上保持和法国母版同样的水准,内容全面本土化。 有朋友多次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那么长时间?通常情况下,作者写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够持续10年以上,确实比较罕见。我想这除了我做事比较能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和《新发现》杂志的良好合作──杂志充分尊重和信任我,从不对我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出任何异议,随便我天马行空写什么都行──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编辑几乎从不改动我文章中的任何字句,哪怕是发现误植,也要在电话中核实一下。写了几年之后,杂志又将我专栏的篇幅从两页调整为三页,稿酬当然也有所提高。投桃报李,我对“科学外史”专栏的撰写也越来越用心。“科学外史”逐渐成为我写得很开心的一个专栏。在国内报纸杂志上,这样的专栏也算非常“长寿”了。 “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更是家喻户晓的还有《儒林外史》。以前我写过一本《天学外史》,比较侧重“外史”的学术意义;现在这本《科学外史》,则是上述两种意义并重了。现在回顾起来,当初将专栏取名为“科学外史”,还真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这个名字高度开放,可以容纳几乎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事情、人物、概念,它允许作者在许许多多迥然不同的场景中随意跳转,选择话题,包含了多样性和趣味性。 “科学外史”当然与科学有关,但我并不想进行传统的科普,而是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 我写这个专栏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每次写什么题目都不是预定的,总是到时候临时选题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让喧嚣的红尘生活为专栏的选题提供灵感,还能够让每次的话题在“科学外史”这个广阔的范围中随意跳跃。但是在出书的时候,我打散了这些文章见刊时的先后顺序,按照若干专题重新组合,这样读起来更有条理。 本来我以为《科学外史》只能是小众图书,聊供少数同好把玩而已,所以书做得比较精致,精装,设计风格走典雅路线,觉得出这样的书送送朋友倒挺好。没想到《科学外史》在2013年出版之后大受欢迎,还获得了年度中国好书、第十三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在商业渠道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进入了许多榜单,不久它又入选国家机关干部读书活动推荐的13种书目之一。这完全出乎我意料。按照我和出版社原先商定的计划,就是准备一年后再推出《科学外史Ⅱ》,这已经在《科学外史》的自序中明确预告了。相比而言,《科学外史Ⅱ》的思想性更强,辩论色彩更浓,在某些争议焦点上的立场更鲜明。之后我又选了36篇文章编成《科学外史III》,仍然不受发表顺序约束,而是根据主题将文章分成六组,拥有更多“新知识、新发现、新观点、新趣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