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档案 盘妙彬,1964年生,广西岑溪人,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梧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诗歌写作,2004年参加诗刊社第20 届青春诗会,作品入选《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重要权威诗歌选本,著有诗集《红颜要来》《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盘妙彬卷》《我的心突然慢了一秒》。 作者档案 钟世华,80后,广西合浦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创作二级。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在《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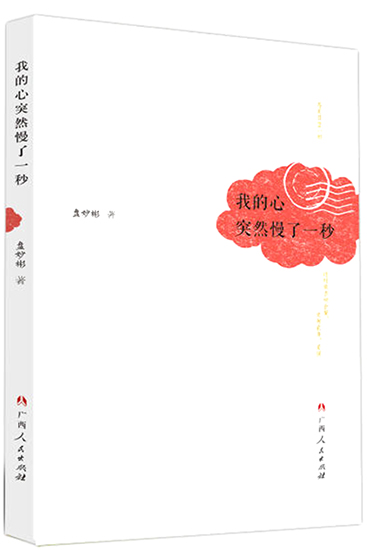 该书为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诗歌类)之一。诗人通过树、山、江、堤、桥、云等景物入诗,生成美的意象,把思想感情依附在景物上,感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作者的语言技巧、叙事方式都显示了其非凡的诗歌创作功力,诗中或浓或淡的情感缓缓沁入心底,婉约自然。 “文字是一种抵达” 钟世华: 中学时你就尝试过创作,你最早发表诗歌是什么时候? 处女作的发表对你今后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盘妙彬: 我不记得最早是什么时候发表诗歌了,谈论处女作于我没什么意义更无影响。 钟世华: 心中有处处有,心在处处在。你的出生地是一个叫榃美冲的小地方,远在天际,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户人家在居。你在2011 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向往天际的故乡》,其实从童年开始你就一直在向往,无论是你选择在梧州工作生活,还是旅游,包括你所到过的地方,向往的小镇。可见这种向往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巴列什曾说过,“童年持续人的一生……”,你的诗歌生涯与这种向往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童年记忆对你日后的创作有无影响? 程光炜教授曾评价说你是一个经验型的诗人。 盘妙彬: 永远是精神世界大于现实生活,而飞翔的翅膀得靠自己创造。童年的这份向往让我长出翅膀,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童年。我想,当我到了80 岁,也一样能长出翅膀的。向往应该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这个物化日益严重的时代,我们要让自己有时间和心情,不时抬头看看白云和远方。至于我是不是一个经验型的诗人,我自己不知道。只要我是这一个“我”就行了,不要丢失了自己。 钟世华:追溯很多作家的创作之路,起点皆源于年少时对文学的向往与热爱,那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盘妙彬:年少时常被别人欺凌,常有幻想不被欺侮的时候,这样的幻想后来叫做向往,这样的孤独后来叫做寂静。我想,年少的我心中是有一个与现实相反的天地的,现在想来这就是财富。中学时喜欢读文学书籍,集体宿舍熄灯后,常用手电筒在被窝里读小说。大学时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文学氛围浓厚,不学文学在那时是不对的,不想成为诗人在那时是不可想象的。 钟世华: 古人云:“仁者近山,智者近水”。1984 年寒假你到了一趟梧州,过江时你脑海忽然闪过回梧州工作的念头,并认为生活工作在这座美丽的小城是很理想的。屈指数一下,你已经这座城市生活了25年,你在20 世纪末或晚曾写过一篇文章《小城心》,那么,请谈谈你对梧州最深切的感受。你每星期都爬一至两次白云山,每晚都在江边散步,在你的诗里,充满了水的湿润和山的沉静。那么你所生活的梧州与你写诗有着怎样的关系? 盘妙彬: 如果读者愿意,请读者再读《小城心》。这确是一篇好文,不会浪费读者时光的。我的灵魂、我的世界观、我的思想全在我的诗文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愿多说我作品以外的话,有时候我一句都不想说。我在小文《文字是一种抵达》曾说: 要我把自己与大自然万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一“翻译”给世人听,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与他人或太多的人有太多的距离和分歧,以为这是自己的缺点,我愿意这样抱残守缺到最后。 我文字的缺点更甚于人本身,它与人本是一致的,后来它越走越远,越来越纯洁,越来越简单,别指望有“第二个”。“心在云端”是我的博客。我扛着梯子向山顶走去,往云端攀登,去向的远方远远大于现实。有人曾认真地问过我: 在山顶就你一个人,梯子用什么支撑? 我答: 风会帮我扶住的。梧州有白云山,有西江,在这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每星期爬一至两次白云山,晚上沿江边步行一小时左右,这渐渐成了我的习惯。山川给我的就是浮云和流水,于此略有所悟时我还不是中年。“无所图,无常,没有成败,就是活着。”明白时不要太老了。 钟世华: 在广西大学读书的时候,文学渐渐渗入你的骨髓。你曾担任过学校“映山红文学社”的社长,参加文学社团对你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盘妙彬: 1986 年7 月我从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直到2011 年8 月我才第一次返母校看看,短短的半个钟头,相隔25 个年头,许多感慨无法说。今日大学校园文学与20 世纪80 年代的校园文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中文系的那座红砖小楼不见了,我真真的要用泪水来怀念那四年的大学时光,那一去不复返的。大学文学社给我的是梦,那青春年少的血液保存了梦的温度,保存了那文学火苗小小的火种而不被世风吹灭。 钟世华: 有人说,诗歌需要有殉道精神,要用一生去写作,要耗尽青春、前程,甚至是生命。在广西,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仍能坚持并能保持良好的创作势头的诗人并不多,你是其中的一个,可谓“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的支撑点是什么? 盘妙彬: 中国诗坛中的不少人,只把写作当作获取某种目的的手段,目的达到了,不写了。我十分敬佩外国的那些大师们,八九十岁了还在写还在出作品并且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些经验访谈之类的咳嗽,这种现象在中国难觅。其实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三几首好的诗歌不难,很多人做到了,难的是一生中优秀作品不断。不少中国诗人写了几首好诗,就开始当先生、做老师了,喜欢出席各种讨论会,喜欢亮相,坐到讲台上、主席台上,开始向台下的人宣扬自己的口水和咳嗽,大谈特谈自己的某年某月和某日,如何如何等等,这种现象中国诗坛比比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更甚。福建的一个诗人曾经这样说,在北京的某些个诗人写了几首不甚了了的诗,因为钱多就组织作品朗诵会、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弄个场子热闹热闹,然后在各论坛上发消息,真的不甚了了。现在太多诗人不甘心寂寞了,想的不是写,而是如何利用现代传媒抢眼球,以为出了名才是重要的。于我自己,以为作品深入读者心中才是最重要的,那单单有个名而名不副实比不了一阵风长久。于我写作是清风和明月,是生命和灵魂需要,一生都离不开的,这其中不存在“道”。当然清风和明月可能是没什么用的,那又有什么要紧呢。 真正的诗歌关怀万物生灵 钟世华: 你在诗歌创作中融入了很多古典诗词的韵味,使诗歌带上了“唐风宋雨”的痕迹,你的诗仿佛一幅幅活生生的山水画。那么,你是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你更多的是从哪一方面汲取营养? 盘妙彬: 先说说诺贝尔文学奖。每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出来,只要是诗人获奖,中国诗坛的许多人都会流口水。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西方的一个奖,评委中有几人对中国文字的造句、韵味懂一点点呢?中国文字乃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字句、词采、音律(我这里非指古典诗词中的押韵) 、韵味被某些人翻译成外语,可能有鸡和鸭的区别,严重一点说可能是蛤蟆和天鹅的差别了。中国古典诗词中字与字之间的美妙搭配、内在关联、形成的词韵之美,许多国人包括时下许多写分行中国字的人都不懂。现在的问题在于,许多外国大师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却是怎么读都不体现大师级的水准呢,这可能又是翻译出了问题,把那些外文中特有的音律、韵味弄丢了。当然,外国大师们作品中的那种活生生的现场感我是领略了,那是西医中手术刀给人血肉直现的那份生命中的真切。而中国古典文学如中医药般给人那种经络畅通的感觉也是妙不可言的,当推陈出新。对于传统和现代,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传承与吸收,一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钟世华: 在你的诗里行走,仿佛每一句都是一阵自然的风。对于诗歌,多年前你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万物的样子就是诗歌的样子》,你的诗歌与其说接近梦想,不如说更接近自然。 盘妙彬: 对,当文字进入与自然万物的对话,那种美妙无法说,也可以说是下笔如有神。文字真正融入自然万物中了,一切写作理论都是多余的。在当下诗坛,我以为那些称为“理论”的文字是多么的苍白,这些文字没有从实践中来更没有回到实践中去。优秀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会自然而然在体现自己的“理趣”,那些评论多是皮毛。 钟世华: 读你的诗,直叫人顿悟( 作家高瞻语) 。“阳光是甜的/发生是一件简单的事,神这样做/在一个慈悲之人的心种黄金”。也如你所言“经过佛,遇上好人,碰到果”,你怎样看待诗与佛学的关系? 你觉得佛学思维方式与诗的思维方式有何异同? 盘妙彬: 真正的诗歌关怀万物生灵。心中有佛我不拜佛。塔作为一种建筑更是一种艺术,塔进入山水让山川更加完美,成为山水的一部分。塔一般筑在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起到锁水口、镇山川、蓄文脉的美学作用。塔总是升腾的,使人高远,产生遐思。我在,我写,我从来不问也不懂什么是佛学思维方式与诗的思维方式这些无趣的东西。 钟世华:《大理在,大理不在》《此地在,此地不在》,类似于这样标题在你的诗里有不少。这种看似一对矛盾体的标题,是不是一种悖论? 盘妙彬: 人对自然万物的感悟千差万别,回答这个问题说简单十分简单,说难比拉牛上树还难。 “不断寻找诗歌的地址” 钟世华: 有观点说你的诗属于乡村诗歌,对于这个观点,你认同吗? 盘妙彬: 别人说我的写作是什么和什么,我很容易忘。我不明白别人的观点,观点于任何写作都是危险的,至少我是这样。我的诗歌是自然万物,它一直在其中。还是我在各种提问中只说的一句话: 万物的样子就是诗歌的样子。 钟世华:回顾上世纪80年代,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盘妙彬:一扇沉重的国门打开,一个新时代到来,一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完全一个崭新天地。 钟世华:朦胧诗的热潮,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 盘妙彬:朦胧诗的出现,是诗歌广阔天地里又多了一条道路,至于如何选择,则是诗人自己的事。对于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艺术,都要吸取其精华,结合自己的心得,走出自己的路。 钟世华: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对你而言是什么? 盘妙彬:说八十年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指的是大环境、大气候。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深圳随便向天空扔一颗石子,掉下都会砸到一个经理的头上的大气候下,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这多么的好。沉寂回到了沉寂,又是多么的好。于我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更多的是以宁静的心灵,不断寻找诗歌的地址,这又多么的好。 “只有在写作中才感到自由” 钟世华: 从1980 年开始至今,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已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参加青春诗会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盘妙彬: “青春诗会”成为一些人的坟墓,到此为止,以为可以在诗歌至高级别的档案里找到自己的名字了。更多的人把“青春诗会”当作加油站,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20 届“青春诗会”在黄山脚下举行,是严格意义上我第一次参加诗歌活动,最感动的是我第一次认识了黄山。 钟世华: 你的一篇文章谈到著名诗人海子,他的情怀或许就是淡淡的,忧伤的,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其实在读你诗的时候,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你的情怀———流水般的梦想,抑或浮云般的“乌托邦”理想,希望中忧伤,忧伤中又憧憬希望———心在云端。正如你自己所说的,诗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家园”。 盘妙彬: 这个观点是我早期提出的,时到今日,再加入“自然主义者”。诗歌是自然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家园。这样说,我是越来越老了。我不明白别人会说我的诗中有“乌托邦”,可能是或者不是“只言身在此山中”。 钟世华: 你曾说“对于诗歌,从前不说,现在也无语,今后也不会发言”,其实对于诗歌你一直在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你认为谈论诗歌是一种危险吗? 盘妙彬: 明白的人自然会明白,不明白的人说得再多也是白说。种树的人从来埋头劳作,吃果子的人才会老问果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钟世华: 你曾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自独立生活以来,旅游便成了你人生的重要内容。在你博客“心在云端”下注的简介也是: “旅行,写作,全是我”。你去云南,被云南迷出了《如梦云南》组诗十几首。请问旅行在你的生活和写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说旅行在你个人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旅行更容易激发诗人语言的激情?或者说带来更多的灵感? 盘妙彬: 艺术就是创新,旅行则带来创新。陌生的地方给人新视觉、新感受、新体验、新思维,乃至新思想。旅行让人保持心灵的新鲜,新鲜的心灵有什么事做不到的呢。 钟世华: 塞弗尔特曾说过说“我为能够感到自由而写作”,我觉得你是“只有在写作中才感到自由”,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盘妙彬: 是的,写作中的我是自由的,心灵有无限的高和远。现实中我则是尽量让自己自由,对许多人情世故不甚了了,事实上我的人生越来越简单,这一点我要高出太多和太多的人了。我不知道塞弗尔特是谁? 但好像我与他相反了,或者说他与我相反了。哈,这有趣。 钟世华: 你如何能将诗人和领导秘书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身份结合为一体? 盘妙彬: 为了不让人产生误解,需要说明的是,我曾经做过几年领导秘书,现在不是。现在只是在办公室从事无聊的文字工作,谋生而已。诗人和领导秘书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身份,从来没有在我身上结合为一体。正确的答案是: 有两个“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