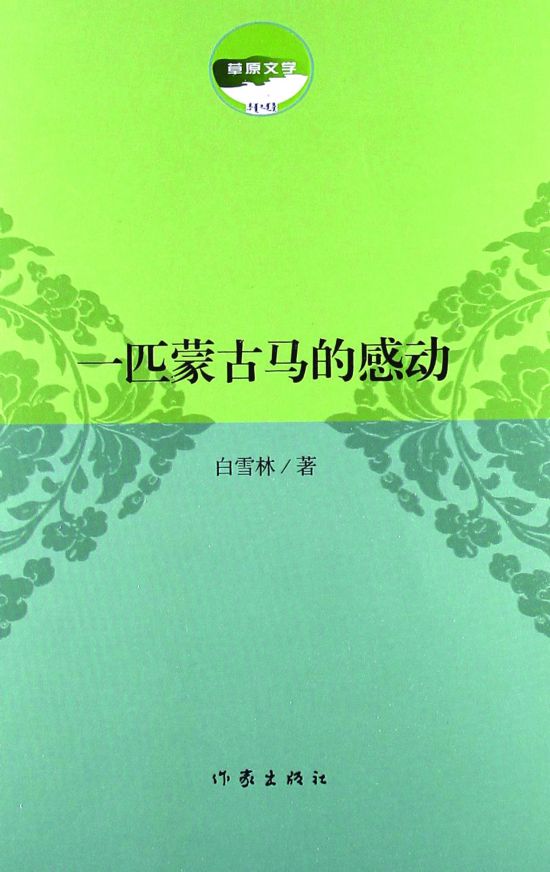 白雪林,我一直敬重的兄长,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作家。他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科尔沁蒙古人的劳动和生活,富有半农半牧地区的蒙古族的浓郁生活气息。古老而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相互交融是其作品的重要母题。他的作品并不是太多,但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如《蓝幽幽的峡谷》《拔草的女人》《成长》《霍林河歌谣》《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等。其中《蓝幽幽的峡谷》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一年,他31岁,刚刚开始发表作品,这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 1985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年底,《北京文学》在京召开笔会,邀请了当时较为活跃的几位作家。记得有山东的矫健、陕西的邹志安、浙江的李杭育、北京的陶正,还有就是内蒙古的白雪林等,由此我结识了他,并成为好朋友。那时候,《北京文学》即将更换新的领导班子,由作家林斤澜出任主编,作家、评论家李陀出任副主编,陈世崇担任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北京文学》上上下下都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新的变化。笔会除了举行编辑与作家的座谈和对话活动,还组织观看了欧美和港台最新的电影录像。美国电影《凶兆》神秘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悬疑化叙事,香港电影《蝶变》独特的主观镜头表达,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与雪林在私底下也讨论过这两部电影,我明确表示了对《凶兆》诡异风格的着迷,雪林则更偏爱《蝶变》的形式感。那时的北京已经有秋意了,我记得我们俩曾在户外有过一张穿着西服的合影。 那次笔会过了几个月,他寄来了他的最新作品,题目叫什么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我在编辑部还是个助理编辑的角色,没有机会成为他小说的责任编辑。这也是我的遗憾,当了30多年文学编辑,竟然没有编过他的一篇稿子。之后他多次来北京参加全国的青创会或作家代表大会,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差不多3年后,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成长》,发表在《民族文学》上。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希望我认真看一下,如有可能也希望我写一篇评论。我认为《成长》是他最诗意化的作品,充满了童年的欢乐、忧伤以及想象。小说叙述上采用了诗歌的通感和抒情性,以童年的视角,将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等孩子的所有感觉,融合贯通绵延在一起,营造了既有童话之美、又有现实之真的意境。 “哈达从松软的草窝窝里爬起,小熊一样从高高的垛顶上向下滑。其实在他脚尖挨到冰冻的地面之前就已经注定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蒙古汉子了。但当时他却什么也没想。多少年以后他在蒙古草原的都城呼和浩特做那段往事的回忆时的的确确是从那一刻开始的。那草垛又高又大,是全村近千只牛、近万只羊冬天的食物。从垛顶上向下滑,飞快呀,欢乐而又能忘掉自我,那飞快的滑行中冲起一股微香的草的味道。那草当地人叫作羊草或碱草,冬天在大垛里捂着,还保存着鲜嫩的绿色,牲口吃起来一片沙沙声。那是草原上最好最肥的牧草啦,还有比吃起那草更令牲口惬意舒适和满足的吗?那时牲口向牧人们瞟来的眼神都充满了感激。”我忍不住摘录了小说的开头部分,虽然这段叙述明显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篇模式的影响——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这种开头模式的仿效几乎成了“时尚”。但是读着《成长》的开头,我不仅没有不快,反而觉得这样的开篇非常准确、自然,并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展开童年回忆的心境和情怀。我的评论后来发表在《民族文艺报》上,可惜刊物我一直没有收到,不久刊物停刊,我的底稿也丢失了。 那一年正好是1989年,之后他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开始写电影、电视剧,据说还做了一段生意。我们失去了联络,为此我对他还有点不高兴。若干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是他发表了《一匹蒙古马的感动》之后,那时候他的心脏已经装了两个支架。他已经不能喝酒了,只能微笑地举着茶杯和我们对饮。不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搂着我的肩膀,有些歉意地看着我说:“你那篇写《成长》的文章是关于我小说最到位的一篇评论。” 在我看来,他是个对文学有着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的作家,并且他还敢于或者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尤其愿意与年轻作家们分享心得。他对年轻作家的帮助是无私的,不分民族,不分远近。看到一篇或者一部好的作品,他不光会提出诚恳的意见,还会主动帮助作者寻求发表或出版的途径。达斡尔族“80后”女作家晶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刺》,就是他推荐给我,由我负责出版,后来还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的新人奖。与他会面聊天很少会扯及八卦或政治类的空谈,他更愿意谈论文学和写作。比如,他会兴高采烈地告诉在座的最近读了什么好书,或者在创作上有什么感悟、遇到什么问题等等,时有真知灼见,给人启发。我从年轻时就经常与国内的很多重要的前辈作家混在一起,我深知听他们聊天比听讲座或者看他们的创作谈更有意义。那是没有经过修饰的话语,没有隐藏,没有伪装,你甚至可以听到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快乐和困惑,以及他们写作的软肋。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对年轻作家极有帮助的学习方式,而知名作家也应该多以这种方式去关怀和帮助年轻的作家们。雪林正是这样的作家。 最后一次见雪林,应该是2016年夏天父亲病重期间,他来看望我父亲,之后一直没有音信,期间我去过呼和浩特多次,但那时他多数时间住在北京附近的燕郊,他女儿的家里。燕郊与北京城区还是有段距离,我也不便多打扰他。后来有一天,作家路远告诉我,他见到雪林了,他的心脏搭桥后,效果不理想,身体非常虚弱。突然有一天,在内蒙古作家竞心的微信里,看到他转发了白雪林的小说《蓝幽幽的峡谷》,我看到一条留言是“雪林老师,走好。”我内心其实有过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发蒙,因为最近这几年身边的亲戚朋友和作家走得有点多,我甚至有些麻木了,但是当我确认他真的离去的那一刻,还是让我感觉突然和无法抑制的悲伤…… 雪林是那一批作家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也是其中最执著的作家之一。2013年7月7日,他在送我的小说集《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的扉页上写道:“文学是我们永恒的期望。”我相信他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写完,那些故事、那些场景,还有人物和对话,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是,他已经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在《一匹蒙古马的感动》的题记中写的一样:“马是草原上的灵物,它们感情最深厚,最热烈,对主人最忠诚,你如果把它感动了,它愿意为你奉献一切,直至生命。我为蒙古马哭泣。”重读这篇小说,我依然为这匹马而感动,我感觉雪林就是这匹叫查黑勒干的马,而文学就是他的主人。文学滋养并丰富了他的人生,他也用生命回报了文学的恩典。 雪林兄,一路走好。内蒙古文学、蒙古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有你重重的一笔,这足以让你欣慰和骄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