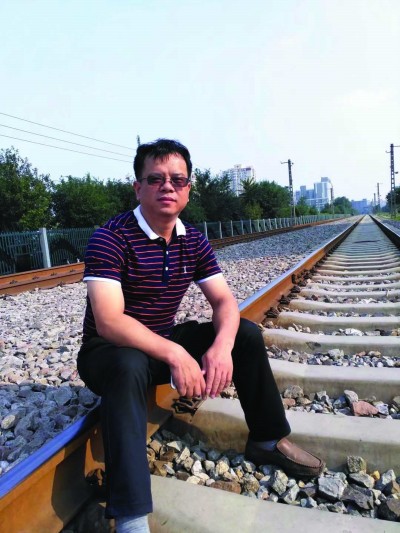 近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王安忆、陈思和、林白等都谈到了方言与写作的关系。广西实力派作家代表朱山坡说,直到现在,他的普通话还说不好,写作时都是方言的思维方式,把方言转换成普通话,这可能也是一种特质,他宁愿一直保持南方特质,不刻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作家。朱山坡曾经在政府机关做文秘工作十五年,为了真正地能够靠近文学,打入自己理想的圣地,他先后两次走出广西,进入南京大学作家班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他说能跟文学安静地待在一起,互相凝视对方,就有收获,就有启发,就能激发他的热情。“在大学里读书,像空中加油一样,毫无疑问,能延长我的飞翔距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他要从“边缘”地带开始迈进“中心”地带呢?很明显这仅仅是他的文学方向,他依然热爱着那个地方,“生在南方,基因就是南方的,血液里、骨髓里流淌的和储存的都是南方的记忆。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坚持在‘南方’写作。” 朱山坡,本名龙琨,1973年生,广西北流市人,在粤桂边的山村长大,从小说粤语,受粤港台文化影响很大。从中学开始写诗,15岁在县刊发表作品,曾在乡、县、市政府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计15年,现为广西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2000年开始与县内朋友一起组织《漆》诗社,写诗、编印民间诗刊、搞诗歌活动、混迹网络诗歌论坛,在《诗刊》《星星》等发表大量诗歌作品。2004年开始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花城》2005年第6期“花城出发”栏目重点推出两篇小说、创作谈和访谈,此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天涯》《山花》《小说界》《作品》《江南》等杂志陆续发表小说近百篇,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和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有部分小说被译介俄、美、英、日本、越南等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中国银行》《灵魂课》《十三个父亲》等。 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上海文学》奖、《朔方》文学奖、《雨花》文学奖、广西自治区政府文艺铜鼓奖等多个奖项。根据小说《美差》《灵魂课》改编的电影分别获得第25届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影片及儿童贡献奖、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 □本期对谈嘉宾 朱山坡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王迅 1 只要跟文学安静地待在一起,互相凝视对方,就有收获,就有启发,就能激发我的热情。在大学里读书,像空中加油,毫无疑问,能延长我的飞翔距离。 王迅:在70后作家中,你是一个比较善于学习的作家。十年前你脱产到南京大家作家班学习,现在你又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与鲁迅文学院联办)。这种学院式的学习训练对你的文学创作有帮助吗? 朱山坡:我在政府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忙于公文写作,很少接触文学。但一旦转身投入文学创作之后,才发现自己如此才疏学浅,对当代文学简直是孤陋寡闻。面对这种状况想通过见缝插针式的恶补也是很难的。因而,我决心脱离工作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地补一下文学课。对我而言,在南京大学两年收获甚大,这也是十年后我下决心去北师大学习的一个原因。只要听课,只要跟文学安静地待在一起,互相凝视对方,就有收获,就有启发,就能激发我的热情。在大学里读书,像空中加油一样,毫无疑问,能延长我的飞翔距离。 王迅:当下大多数作家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有人说,高智商的人几乎都不在文学圈。换句话说,写作不需要高智商,也不需要高学历。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朱山坡:有一定道理的。幸好那些智商极高的人不从事文学创作,而去搞科研发明和金融投资等行业去了,否则作家这一个行当竞争更剧烈,更不好混。但是,作家拥有高智商、高学历也没有坏处呀。伟大的作家不一定有高学历,但肯定是有高智商的。我自认智商中等偏下,勉强适合在文学圈混,有时候还感觉到智商不够用。我一直以为要提高智商,进大学是最好的途径。所以那么大龄了还厚着脸皮坐在大学教室里,听年纪比我小的教授传道解惑、指点迷津。 王迅:在我印象中,高智商的作家是有艺术天赋的那种人,比如张爱玲,这类作家通常是可遇不可求。高学历并不是评判作家水平的标准,但不时“充电”是必须的,你曾两度前往高校学习,能否谈谈最近在北师大学习的情况? 朱山坡:在北师大学习一年间,我自认为还是蛮拼的。我们住在鲁迅文学院八里庄校区,跑到北师大上课。通常是乘地铁,从十里堡站上6号线车,在朝阳门站中转2号线,到积水潭站出来,骑小黄车约十分钟可达北师大。上完课后原路返回,路上单程大约要五十分钟。每周有一天课是早上8:00上的,因而6:50得出门去挤地铁。北京早上7:00左右的地铁拥挤程度超乎想象,有时候要等差不多十趟才挤得上去。开始的时候,面对车厢里拥挤不堪的青年男女,我不好意思挤进去。后来习惯了见缝插针,让别人把自己推塞进去。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晚饭后常常越过十里堡的铁路前往大悦城逛完单向街书店又回来;或沿着铁路一直往西走,从石佛营路返回来。有时候跨过天桥前往红领巾公园,看广场舞和湖面的夕阳。冬天,北师大的乌鸦数量惊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少逛京城,期间和同学去过一次东北,目的是看雪,但说好了的雪一直没有下。以为一年时间很长,其实就是弹指之间。 王迅:北师大这一年,有哪些老师给你们上课? 朱山坡:李敬泽、苏童、格非、李洱、欧阳江河、西川、邱华栋、张清华、张柠等名师给我们上过课,对我还是有启发的。我对大学依然肃然起敬,依然保持一颗热爱学习的心。一年下来,我没有缺多少次课。中午不得休息,有时候上课会打盹,但即使是打盹,我也尽量压缩时间,坚持把头抬起来。单词几乎忘光了的英语,我重拾起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英语课上我十分认真、投入。 王迅:学习期间,可以把工作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文学的氛围中。这是催生好作品的土壤。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应该酝酿了不少作品吧。 朱山坡:是的,我的同学写了很多作品,我也写了一些。写完了长篇《绿珠》,接着写了小说集《蛋镇电影院》。我们常常自嘲,也互相鼓气,叫嚣着要写出“杰作”来。 王迅:看来创作上是大丰收了,祝贺你!现在谈谈创作的具体问题吧。经常有作家和评论家讨论“二手生活”的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经验够丰富吗?你笔下的生活是否也存在“二手”的问题? 朱山坡:并非所有的经典作品素材都来自“一手生活”,“二手生活”也未必写不成伟大的作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读到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源自“二手生活”。当然,亲身经历的事情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我也希望自己像海明威、杜拉斯、马尔克斯等等那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写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够了。他们有足够的素材写一辈子“自传性”的小说。但我显然不是那类型的人。我的人生经验相当简单,跟大多数同龄人相似,波澜不惊,平常无奇,仅靠阅历不足以构建一个像样的文学体系。 王迅:你的小说素材多半来自“二手生活”,那么,这是否涉及到一个转换的问题,如何把别人的“二手生活”变成“文学素材”,转换成个体的文学经验? 朱山坡:我必须借助“二手生活”,借助想象力,把别人的人生经验变成自己的切身感悟。因此,我也常常去观察,去寻找我的小说人物和素材。当然,如何把“二手生活”变成“亲身体会”和“感同身受”,在自己的小说里没有隔膜感,这需要巨大的感受力和写真能力。 2 生在南方,基因就是南方的,血液里骨髓里流淌的和储存的都是南方的记忆。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 王迅:文学史家通常把何立伟的小说命名为“绝句”式的小说,那是因为小说中蕴含着无边的想象空间。我也曾在一篇评论中把你的小说《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称为“诗小说”,这缘于你的诗人气质,请谈谈你对小说美学的追求。 朱山坡:小说是讲究意蕴的。尤其是短篇小说更应该以意蕴取胜。诗歌是最讲究意蕴的。如果能把小说写出诗歌的气质,那是多么令人暗喜的事情啊。我尝试过以诗歌的形式写小说(叙事诗),当然,我也应该尝试用小说的形式写诗歌。在写小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写小说。 王迅:你的某些小说充满了“诗”的意味,留白空间或可阐释空间很大。那么,在下笔之前你是否想到接受的问题?会不会担心读者认为你写的作品不像小说,或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不一样? 朱山坡:我不担心。我一直努力写不一样的小说。我觉得自己的小说还不够另类,诗意还不够。我不奢求很多读者喜欢我的小说。 王迅:现在聊聊影视改编吧。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西、鬼子、凡一平为代表的广西作家频频“触电”,一度成为中国文坛关注的焦点。最近两三年,你的长篇小说《懦夫传》和短篇小说《灵魂课》《陪夜的女人》《惊叫》《美差》《推销员》等同时被影视公司看中,买下改编版权,现在已进入拍摄环节了吧? 朱山坡:《懦夫传》被改编成60集电视剧,已经开机。《灵魂课》改编的电影去年在东京电影节展映了。《美差》改编的电影《八只鸡》刚刚全国公映。我没当过编剧,只是小说被搞影视的公司看上了。因此我算不上“触电”吧。但我对小说变成影视充满着期待,好小说和好影视是相互成就的。小时候我多么喜欢电影,看电影几乎占据了我的童年一半的记忆,以至近来我写了一部以乡镇电影院为背景的小说集《蛋镇电影院》,还原和复活了当年看电影的场景。那时候,我坐在电影院里,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王迅:与你其他作品相比,你觉得这些被改编影视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吗?你认为小说中包含了哪些影视元素?如果有,在创作中是否是有意识地融入一些影视元素? 朱山坡:小说应该有好故事,有好细节,还有令人难忘的人物,当然,还有清晰的画面感。这些元素也正是影视所需要的。好小说天生就具备影视的元素。刻意往小说中加入影视元素是没有必要的,像往水里加几滴油,徒劳无益。莫言说过,你越想把小说写成影视,离影视就越远。所言极是。 王迅:作家们常说,但凡作家都渴望财务自由。财务自由了,对写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你会为了钱去写那种有“看点”的剧本吗? 朱山坡:如果我去写剧本,绝对不仅仅是为了钱。如果不是热爱,我宁愿不写。每个人财务自由的条件是不同的,在南宁,有三两百万可能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了,但在北京可能要两三千万。究竟要写多少剧本才能实现财务自由?如果能通过卖小说影视改编权来实现财务自由,对小说家来说应该是最理想的。我从不奢望通过写作实现财务自由。 王迅:广西作家的小说、诗歌带有明显的“南方特质”,林白和你的小说尤其突出,比如林白的《青苔》《致一九七五》等,还有你的《风暴预警期》及一些中短篇,无论是小说的气韵,还是语言方式,都是特有的,富有浓郁的地域性,为中国文学的南方写作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能否结合作品谈谈你对“南方”这个概念的理解? 朱山坡:生在南方,基因就是南方的,血液里、骨髓里流淌的和储存的都是南方的记忆。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坚持“在‘南方’写作”。我和林白所处的“南方”,又有特别的东西。我们那里跟广东接壤,华侨多,客家人多,受港、台、粤和南洋文化影响很大,又有诸如鬼门关、南越等文化底蕴,还受到巫文化的浸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耳濡目染,我们的底色变得比较繁杂、斑驳,所以我们笔下有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觉得神神道道,或觉得吃惊、将信将疑。 王迅:除了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在叙事语言的本土化上,你的写作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这是文学写作独特性的最直接的体现。 朱山坡:说到语言,更是让我们曾经感到自卑和纠结。复旦大学在上海刚刚举办了“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王安忆、陈思和、林白等都谈到了方言与写作的关系。林白说到小时候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十分羡慕,就为自己的方言口音感到自卑。我也跟她一样。直到现在,我的普通话还说得不好。写作时我们都是方言的思维方式,把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所以有人说广西作家的语言不是那么“规范化、标准化”。可能这也是广西作家的特质吧。我宁愿一直保持南方特质,不刻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作家。 王迅: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广西是欠发达地区,广西作家的写作很难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你觉得在边缘地区写作吃亏吗?比如说,在广西和在北京,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肯定是有差别的,不仅仅视野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有平台、传播和资源等等。北京就是中心,相对来说广西就是边缘。你觉得在中心写作跟在边缘写作区别在哪里?你有过纠结吗? 朱山坡:毫无疑问,中心和边缘是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在资讯比较发达的今天,差别仍然十分明显。我们必须正视,但不必自怨自艾。默默地写,安静地生活,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喜欢的人就住在对面,甚至没有人知道或在乎你是一个作家,这种状态也是好的。我有一帮球友,他们都不知道我是作家。如果大家都称我作家,我有紧张感,难为情。在下班后的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边缘人,很不显眼,即使是在球友中间,因为球艺不精,又不甚活跃,我也是边缘的。如果一个向来安心于边缘的人一旦站在中心,他会自在吗?会不会露怯显丑? 王迅:过去,你虚构了一个“米庄”,现在,你又在打造一个“蛋镇”。我在《风暴预警期》中读到了具有浓郁南方气息又陌生化了的“蛋镇”,从“米庄”到“蛋镇”是一种跨越。能否认为这是你厌倦了乡村,向城镇文学迈进? 朱山坡:农村题材写了那么多年,确实有点厌倦,想换换。我在农村长大,对城镇生活不是很熟悉,写城镇心里没底。写蛋镇前,我做了很多准备,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巷子,每一座房子,每一道桥梁,都在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进进出出的各式人等,心里都给他们画了脸谱。至少在我的纸上,蛋镇是坚固的。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使蛋镇更加丰盈、宽阔。其实,我早已经开始尝试写城市小说,为此我准备了很久。乡村终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城市文学将越来越重要。对城市,我也将乐此不疲。 王迅:迄今为止,你出版了《我的精神,病了》《懦夫传》《风暴预警期》等三部长篇小说,但无论从艺术形式上还是从题材内容看,这三部作品都显得风姿各异,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美学追求,这在70后作家中并不多见。这种不断颠覆自我的尝试是难能可贵的。我想知道的是,每部作品写完,是否达到了下笔之前的审美预期? 朱山坡:写短篇小说很让我有快感,每写完一个,都有制作成了一件小玩意后的喜悦。写长篇小说让我有庄重感,好像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到可以放弃任何身外之物,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去做。我写过的长篇小说,得失自在心头,不甚满意,但也不至于自认为是一坨屎。我会一直在变化,往好里写,往经典写。 3 每个作家、每个作品都有各自的命运。有些作家生前就家喻户晓,有些作家死后才为人所知。关键是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筛选。 王迅:从美学气质上,我曾把70后作家分为四类:一类是徐则臣、田耳、王十月、李俊虎等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人数最多的一类;一类是以乔叶、付秀莹、东君为代表的,具有古典气韵,承续人文传统;一类是鲁敏、朱文颖、滕肖澜等致力于女性书写的作家;再一类就是像你、李浩、路内和阿乙,属于专注于叙事探索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大致粗略的划分,很多重要的70后作家不能囊括其中。你对70后这一代作家的创作现状怎么看? 朱山坡:我拿不准你这样划分对不对。但我想,归类对作家来说都是很困难的,都未必准确。70后作家不断被提起,被评论,好像是,他们像一群溺水者,正在挣扎着、沉浮着,如果不往上提一下就要沉没了,从此消失了。沉没、消失的危险永远是存在的、巨大的,但不仅仅限于70后作家。如果一定要把70后作为一代的,我认为这代作家取得的成绩并不差,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即便拿到国际上去比也不见得逊色。现在纯文学就那样了,国际上的那些70后作家难道比我们强很多吗?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以年龄来划分,现在还活着的、还在写的作家都处于同一个时代。文学史从来都是以时间段(比如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来叙述的。 王迅:读者是千差万别的,初级读者、高级读者以及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解读作品的视角也是各不相同。哪怕是评价一个优秀的作家或一个杰出的作品,也越来越难以做到众口一词。评判的标准受个人的喜恶影响很大。你如何对待别人对你的评价? 朱山坡:有人说你写得好,也有人说你写得不够好,这都很正常。有人说我写得不够好,除了个人喜恶之外,可能是我确实写得不够好。我经常否定自己。但还好,因为我还相信自己能写得更好。 王迅:从2005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你的很多作品,如《陪夜的女人》《鸟失踪》《灵魂课》《爸爸,我们去哪里》《回头客》《推销员》等短篇精制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影响越来越大,你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定位?未来的创作有何规划? 朱山坡:我像是一个在大海里徒手捕鱼的渔夫,折腾了十几年,捉到了一些鱼虾,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突然到了油腻中年,被慵懒之气缠绕着,不太愿意冒险和苦熬了。有时候自掴耳光,催促自己到深水区捕捞一条大鱼,最好是大鲨鱼。非大鲨鱼不能激发我的斗志了。我正往深海寻找大鲨鱼。如果遇到了,就破釜沉舟,放手搏一把;如果不遇,也就算了,原路返回,晒太阳去。 王迅:你觉得你会“火”吗? 朱山坡:不会吧。因为一个作家要“火”,除了写得好外,还要具备其他很多条件的。 王迅:我说的“火”当然指圈子内部的关注度,就当下语境来说,想让一部纯文学作品火起来确是奢望。就文学圈来说,一个作家要“火”起来,需要哪些“条件”? 朱山坡:当然写得好是关键,但还得有契机。比如说改编成影视,让你的作品以影视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要懂得吆喝,有平台、有媒介给你吆喝,有名家帮你吆喝,通过各种传播的方式让你的作品为人所知;还有获奖;也有不少好作品是通过读者和同行口耳相传变得炙手可热的。每个作家、每个作品都有各自的命运。有些作家生前就家喻户晓,有些作家死后才为人所知。关键是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筛选。这是常识了。 王迅:有人说,作家不要写得太多,写得太滥,要珍惜自己的文字。无论是当代还是现代,很多作家都存在重复性写作的问题,你认为在这个年龄段你写得够多吗? 朱山坡:我刚刚还跟弋舟谈论到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我们70后这一拨作家在个体的创作数量上并不见得有优势,也就是说,数量还是偏小。前段时间,我在书店里看到莫言、余华、苏童、王小波等前辈的作品系列,在书架上排成一排,洋洋大观。在我这个年纪时,他们的作品数量就相当可观了。不说质量,我们的数量也比不上他们。他们50后、60后对文学的执着、投入和付出值得我们钦佩。反正,我自愧不如,我服气。当然,追求数量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有些作家重复自己,有的作家越写越差,只是为了刷存在感而写,就没有必要了。有时候读了某个著名作家的新作,真替他可惜:要是他从那时候开始不再写了,那该有多好!很多作家跟运动员是一样的,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体面退役是明智的。我多么羡慕80多岁仍能写出杰作的作家。 王迅:近年来,广西作家与东盟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很多作品都被翻译出去。昨天,我收到一本柬埔寨语版的小说集,其中有你的作品,能否谈谈你的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情况? 朱山坡:除了《懦夫传》越文版在越南出版外,其他都是单篇翻译出去的,有俄文、英语、德文等,数量不多,说明我写得还不够好。 王迅:《懦夫传》译介到越南后有何反响?越南文学界怎么看这部作品? 朱山坡:三年前应邀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跟越南出版机构签订了《懦夫传》越文版出版合同。此书近期内会在越南上市。越南的图书做得很精美,我很喜欢。越南读者也喜欢读中国文学作品。我的一个短篇《鸟失踪》去年翻译到越南,在《先锋报》发表。译者跟我说,他被小说感动哭了,所以才决定翻译给越南读者的。这也是一种鼓舞。 (王迅,著名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