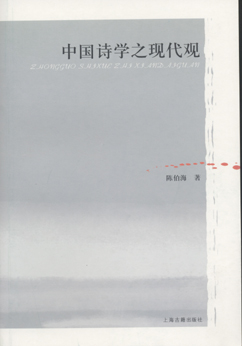 陈伯海先生早先以研究唐诗学著称,曾著《唐诗学引论》,主编《唐诗学史稿》。唐诗学的特征蕴涵在中国诗学的整体系统之中,并在与中国诗学的系统质的兼顾与比较中才得以显现。由唐诗学切入,陈先生进而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中国诗学的整体中去。继2002年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诗学史》问世后,他主持并独立完成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不久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诗学之现代观》重在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和阐发中国古代诗学,以求激活与释放中国诗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在该书中,我们既看到了老一辈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对现代学术谱系,尤其是西方近现代以来各家各派诗学和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尽力关注,又看到了一位对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有素的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和系统周详的思考;既看到了作者对中国诗论若干基本范畴勾疏爬罗的微观考辨,又看到了作者对中国诗学主导精神及其逻辑结构的宏观解析,堪称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横向研究的煌煌大作。 陈伯海先生早先以研究唐诗学著称,曾著《唐诗学引论》,主编《唐诗学史稿》。唐诗学的特征蕴涵在中国诗学的整体系统之中,并在与中国诗学的系统质的兼顾与比较中才得以显现。由唐诗学切入,陈先生进而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中国诗学的整体中去。继2002年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诗学史》问世后,他主持并独立完成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不久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诗学之现代观》重在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和阐发中国古代诗学,以求激活与释放中国诗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在该书中,我们既看到了老一辈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对现代学术谱系,尤其是西方近现代以来各家各派诗学和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尽力关注,又看到了一位对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有素的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和系统周详的思考;既看到了作者对中国诗论若干基本范畴勾疏爬罗的微观考辨,又看到了作者对中国诗学主导精神及其逻辑结构的宏观解析,堪称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横向研究的煌煌大作。积数十年诗学研究之功,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陈先生对“中国诗学”加以“现代观照”之后得出的基本观点有两个值得注意。第一是中国诗学的“生命精神”;第二是中国诗学“意→象→言”的“逻辑结构”。 什么是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呢?在陈先生看来,就是它“从民族文化母胎里吸取得来的生命本位意识”。西方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群己对立。由此形成的诗学本体观是以“自然”为本。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是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群己互渗,由此形成的诗学本体观是“言志”“缘情”、“情志为本”。“‘情志’作为中国诗学的生命根本,内蕴着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人欲与天道诸层矛盾,其理想境界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群己互渗、情理兼容,而仍不免要经常出现以理节情、扬情激志以及‘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种种变奏,‘志’、‘情’离合因而亦成为贯穿整个诗学史的一根主轴。不难看出,这样复杂而多层次的生命内核,确乎为中国诗学所特有。”“情志”从对物生怀到实感的“意象”,再向超越性的“意境”的运动,构成了中国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诗作为语言的艺术,无论是“情志”转化而成的实体的“意象”还是超越的“意境”,最终都落实在“言”上,都通过语言文字这个媒介反映出来。文辞因而构成了诗性生命实体的外在形态。它衍生出多种形态,如“辞采”是情性的自然焕发,“声律”是心气的流注与节律,“体势”构成生命形体的风貌与动势,乃至明清人常讲的“格”与“调”,也无非是诗人品格、气格、情调、风调在作品文字音韵上的具体显现。文辞体式因而成为诗歌作品中“有意味的形式”,共同指向诗歌的生命内涵。再拓展开去看,“情志”作为诗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属于现实的生命活动。它与诗人一己当下的生活遭际及情意体验相关,并不必然地具备感受的普遍性和生命内涵的深度。意象化的过程乃是诗人对自我生命体验进行对象化观照与审美加工的过程。经过意象化活动,诗人由一己当下的情绪感受转向了对生命本真境界即理想境界的探求,于是生命体验实现了自我超越,转变、升华为审美体验。象外世界的想象空间即“意境”的创造是诗人审美体验充分展开的成功标志。这里,实体意象世界的拘限已经打破,原初的一己情怀也有力提升,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乃至宇宙生命发生交感共振,这是诗歌生命活动的最后归宿,也是传统诗学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 通过对“情志”为本的中国诗歌生命精神的系统阐释,中国诗学的逻辑结构得到了清晰揭示。陈先生指出:以“诗言志”为肇端的中国诗学主要是向着如下几方面来拓展其话语系统的:一是围绕着“志”这一诗性生命内核,由“言志”转生出“缘情”,更由“志”、“情”的复合及其内在张力而引发出各种情志与情性关系的论析,从而构成中国诗学的人学本原观。二是着眼于诗性生命的显现,即由“言不尽意”转向“立象尽意”,再由“穷神尽象”提升为“境生象外”,这一“情志→意象→意境”为主轴的诗歌生命流程的追溯,构成了中国诗学的审美体性观。三是落实到诗歌文本的构造,由言说达意功能的认定,进而讲求文采、声律、体式、格调诸条件及其与诗性生命内在关联,由此构成中国诗学的文学形体观。而总括以上三个方面,将诗性生命的本根、生命境象与生命形体组成“意-象-言”的系统,加以诗兴的发动,再穿插气、韵、味、趣诸要素,则民族传统生命诗论的总体构架便大致浮现出来,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逻辑结构了。 本书分设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情志篇”,论述“中国诗学的人学本原观”,揭示中国诗性生命的本根。中编为“境象篇”,剖析“中国诗学的审美体性观”,探讨诗性生命的发动、审美显现、精神境界、人格范型、审美质性和超越性领悟。下编为“言辞体式篇”,阐释“中国诗学的文学形体观”,揭示诗性生命的语言功能、文辞体性、音声节律、形体组合和诗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