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托卡尔丘克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中国问世。近日,腾讯文化对托卡尔丘克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采访者:柏琳
被访者:托卡尔丘克
在今天的波兰文学界,有一位国宝级女作家,地位堪与诺奖得主米沃什、辛波斯卡等文学巨人并肩,而且她本人也成为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她名叫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她评价甚高,认为她是一位“辉煌壮丽的作家”。
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她曾是荣格心理学的“信徒”,有在精神病医院的工作经历。1987年,她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9年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并因此获得波兰权威文学大奖“尼刻奖”。此后,她彻底放弃公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999年,她的长篇《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再获“尼刻奖”。
可以说,心理学背景给予了托卡尔丘克一种独特的创作视角:通过一种叙事魔法,用寓言、神话、梦境等超现实方式,将个体在相同情境下产生的迥异体验,“统领”入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不神秘,它就存在于每个波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沉痛历史和破碎社会现状的缝隙之中。
在这一方面,托卡尔丘克接续了波兰文学的深厚传统。波兰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从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滚烫的长诗起步,数百年来,文学一直和这个国家的动荡历史具有某种同步性。贡布罗维奇、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乃至扎加耶夫斯基,每一代波兰作家,都在寻求用更宽广的视野反映现实。
如果说在托卡尔丘克前一代的作家,比如米沃什,一直致力于揭露、清算战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现实的是非功过,坚持“文以载道”,那么到了托卡尔丘克这一代,尽管也强烈关注波兰民族文化和历史纷争的多样性,但他们的写作姿态有了明显的不同。
这是因为成长背景的不同:在托卡尔丘克这一代,宏大叙事渐渐消隐,“大社会”转向“小社会”,“大写”的人也变成了“小写”的人。托卡尔丘克更乐于和个体亲近,在作品中拼贴神话和寓言,用一种看似变形的方式,还原普通人“小写”的生活。
2017年12月,托卡尔丘克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中国问世。近日,腾讯文化对托卡尔丘克进行了邮件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神话是故事的根基,也是文学的间接灵感”
记者:你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求学期间曾在一个针对青少年的精神病收容所做过义工。对于精神问题的研究,是如何影响你后来的文学写作的?
托卡尔丘克:学心理学时,我还很年轻。这当然是我寻找自我成长道路的一种方式,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不会过分高估这段经历的重要性。即使学的是桥梁工程或农业,我也迟早会开始写作。我对文学的兴趣埋藏得更深。
但心理学的研究确实发展和深化了我对“世界文学”的感知力。后来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时我最重要的发现是:即使经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体验方式。在此之后,“文化”这个概念,会将这些个体的经历捆绑在一种具有统领性质的叙事体系中,这个叙事体系即我们所谓的“真理”或“历史”。我对这个发现非常着迷。

心理学家荣格对年轻时的托卡尔丘克影响甚深
记者:在心理学方面,据说你是荣格的信徒,你为何被荣格吸引?
托卡尔丘克:荣格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今天我不再那么受它们吸引了。
我在华沙学习心理学时,波兰正处于戒严令管制下——那是一个可怕的时期。

1983年12月21日,华沙民众在为圣诞节排队采购物品
荣格的书在我心中播下了秩序的种子,使我相信:集体意识是由某种我们可以信任的、更深层次的、固定的规律所支配的。
而他的心理学讲座内容让我再度确信,存在一些比混乱的日常政治更坚实的东西,那就是神话。它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即使我们不认识它。神话是故事的根基,也是文学的间接灵感。

托卡尔丘克作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记者:神话的确是你写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你讲述了中世纪圣女库梅尔尼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神话韵味。你曾说:“写小说对我而言,就是对人讲神话故事,让人在神话中走向成熟。”那么,神话在你的文学世界发挥了什么作用?
托卡尔丘克: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读寓言和神话。它们使我感到满足和安慰,就像是“叙事的黄油和面包”,是一种必需品。
寓言是讲述世界的最古老和最深刻的形式之一,它是民间自发生长的智慧,关乎一些最根本的事物:死亡,躲避死亡的可能性,对正义的理解,以及社会运行机制。而神话为孩子做好了生活的铺垫,让他们从中学到很多。大多数人的文学冒险之旅,都是从阅读神话和寓言开始的。
从广义上说,讲故事和写小说这两件事,都源于寓言传统。我们通过塑造的角色来直面人的困境和障碍,我们也能由此了解他人的生活。在寓言和神话中,世界总是巨大的,有无限可能——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力量会帮助你,什么会变成危险。在小说中也是如此。神话提供了一种图解式的叙事,为某些场景和事件做好预演,但神话从来不引入心理机制。而文学的伟大,就在于把心理学引入了情境。
“写作时,我喜欢用青蛙的视角,不喜欢鸟瞰”
记者:你是很难被限定在一种文学体裁内的作家。以《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为例,自传体、随笔、史诗,甚至菜谱……它是各种文体的杂交。事实上,在写作中,你经常致力于寻找史诗和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另一个空间”,你如何理解历史叙事和文学之间的界限?
托卡尔丘克:我相信,每一代作家都试图寻找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世界。而随着世界的变化,这种描述的形式也必须改变。一方面,我们沉浸在传统中;另一方面,这种传统越来越狭窄,令人窒息,让人无法真正定位自我。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自我的声音。
在写作中,我总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我的声音、我的故事节奏。即使已经有了故事的话题和角色,我还是会问自己:“谁在说话?我听见了谁的声音?”事实上,谁来讲述故事,取决于语调和语言系统,以及情绪和氛围。我需要耐心和勇气来为笔下的角色定调。
我用这种写作方式写成了《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后来的《飞行》。这些小说由很多碎片构成,如同星座群像中的一颗颗恒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画面,代表一种更广阔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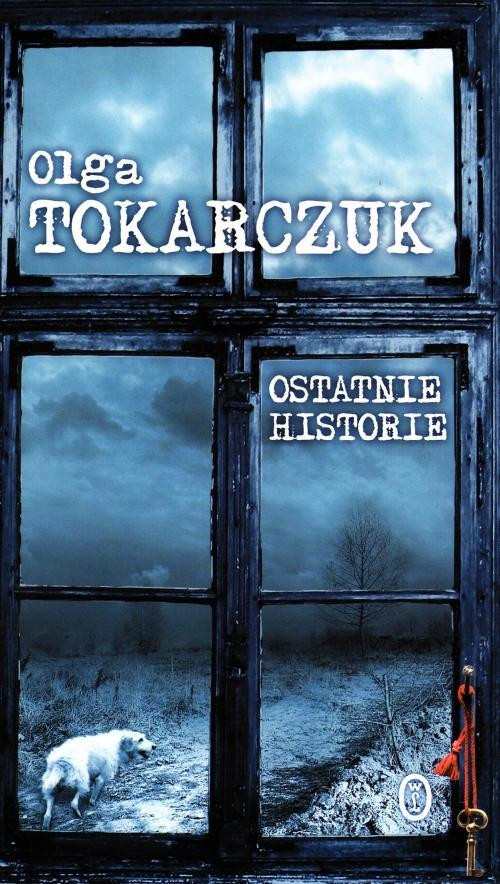
托卡尔丘克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故事》
记者:你也写过很多短篇小说,比如2004年的《最后的故事》(Ostatnie historie),你还曾提议创建一个“短故事节”。短篇这种形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托卡尔丘克:我相信如今的人们更倾向于用简短的方式来思考。这是我们和互联网共存的结果导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比如我们以为在用一个Windows系统,结果跳入大脑的是若干个彼此毫不相关的网页。因此,我们(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混乱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并从个体经历中找出更普遍的意义。
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作家的要求很高——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创造“金句妙语”的能力。我总是告诉自己,长篇小说应该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而短篇则应该让人体验一次微妙不可言喻的启蒙之旅,并给予我们洞察力。
创建“短故事节”的想法,源于一种反抗不公平现状的情绪——读者和出版商对待短篇小说的态度比长篇差太多,短篇小说总是不受欢迎的体裁,人们总是喜欢写些“大部头”,以致于崇高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日渐萎缩。

托卡尔丘克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记者:“寻根”同样是你写作的重要主题,《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探讨了人们在新地区如何扎根的问题,《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探索了个人在历史长河中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为什么“寻根”的主题对你如此重要?
托卡尔丘克:许多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刻重返家庭叙事。家族故事是我们童年记忆中,能分享给陌生人的最私密的部分。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确实受到了我祖母的家庭故事启发,当然,我做了很大改动,加进了我自己的理解。距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把这本小说看作我的青春时代的映射。
记者:在以上两部小说中,你提供了一幅抑郁、古怪的“畸零人画像”,比如醉鬼马雷克和恐惧睡觉的苏姆,这些描写让人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或者福克纳和麦卡勒斯的写作,孤独的畸零人总在寻求爱与平静。你写这些畸零人有什么用意?
托卡尔丘克:把“人”(human)的首字母大写成“H”的宏大历史,总是在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显赫的人类功绩以及重大历史进程,而普通人和他们“小写”的生活总被忽视。后者的生活,我们只能通过文学来了解。
写作时,我喜欢用青蛙的视角,不喜欢鸟瞰。我喜欢从近距离、从底部看到的一切。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者,我很清楚每个人都有点古怪,都有自己独特的敏感点,无论好坏,我们都会把这些特质隐藏起来。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事实上,西方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非常强调这种独特性——由此,就会创造出一批强力而凸显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学人物往往比真实的人更生动,比如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和莫尔索。
“如今波兰人更愿意阅读那些与个体关系更密切的文学作品”

托卡尔丘克
记者:波兰有伟大的文学传统,诞生了密茨凯维奇、贡布罗维奇、辛波斯卡和米沃什这样的“巨人”,作为当代波兰作家,你是否觉得年轻一代作家依然生活在这些“文学巨人”的阴影下?
托卡尔丘克: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没认识过任何一个试图模仿辛波斯卡或米沃什的作家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的情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然而我意识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伟大的文学前辈建立了一种感知的范域,用来测试波兰语所能抵达的边界,而语言才是真正连接我们的东西。
看辛波斯卡和米沃什的写作风格,他们就像来自不同国家的两个人。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停止在“民族”范畴里思考文学了,文学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语言的产物。人类的经验愈发普遍化,文学也变得愈发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译者是跨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使得阅读成为一种纯粹的人类行为。在波兰,我们对来自中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小说都抱有很高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深刻而精妙的交流手段。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文学中的“波兰性”。波兰文学是东欧文学的一部分,在东欧剧变后,波兰文学也有了变化,原来旨在揭露殖民和反抗极权的“清算文学”逐渐淡出,新一代作家似乎把目光从“大社会”转向了“小社会”,不再想背负“现实使命”,对此你怎么看?
托卡尔丘克:是的,文学如今变成了“私人的事”,但这并不是说它变得琐碎,或者回避了生活中重大而普遍的问题。
今天,我们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政治”不再是权力斗争、军备竞赛或者和平条约,它成了个体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他或她吃什么东西,是否觉得自尊受伤,是否实现了自我价值,自我独特性是否被接受,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责任,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对待自然、动物……这些都成了“政治”。如今波兰人更愿意阅读那些与个体关系更密切的文学作品。
记者:波兰有过沉痛的历史。在20世纪,它曾沦为德国和苏联两种极权模式的实验场,留下了历史创伤。这一创伤至今仍在对波兰人的精神状态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作为作家,你觉得自己是否存在某种写作责任?
托卡尔丘克:我不是宿命论者。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强大、清醒且有支持力的社会,波兰就能变成现代化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共同体。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时打击似乎会使一个社会丧失自尊,战败和数次起义(的失败)会导致天才缺席,人们无意识地进行自我贬低。这种缺乏自尊的心态会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其有效工具。要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尊,提高自我估值,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文化建设——在社会中,建立能进行深入、具体交流的对话体系。
一些政客似乎并不喜欢这样做,他们把赌注压在工厂、矿山、进出口贸易上,但正是文化,才能让一个社会变得强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