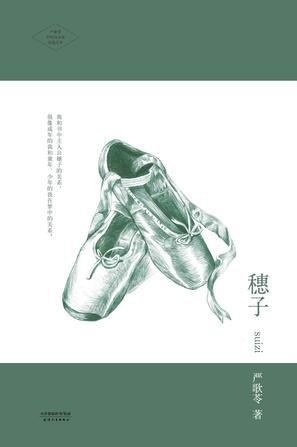 在《灰舞鞋》中,作者对女主角的鞋子给出了慷慨的笔墨篇幅。小穗子刚刚对邵冬骏动心时,“她找着个清静角落,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按场次顺序搁好。演出接近尾声了,轮到最后一双舞鞋。是双灰色的,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小穗子与邵冬骏开始交往时,“一次他和一群男兵逛街,听她在马路对过叫他。她斜背着挎包,辫梢上扎着黑绸带,脚上是崭新的妹妹鞋。”邵冬骏提出分手而小穗子要挽回时,“她穿着布底棉鞋的脚劈里啪啦地踏在雨地上,追上他。她嘴里吐着白色热气,飞快地说起来”。 这些细节足以证明对鞋子的注意并不是过度解读,这种带着隐秘性质的足部描写,总是与青春的激情、模糊的爱恋、暧昧的情愫联系在一起,被电影主创方敏锐地捕捉并放大,出现在电影海报上,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暂且不去探寻它背后的隐喻意义,只是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个人记忆演变成青春象征。《芳华》电影海报上大大的英文单词“YOUTH”,以及文工团员们紧绷的足尖和腿,隐约表明这将又是关乎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故事。这种热情洋溢的荷尔蒙味道和悲天悯人的怀旧情愫,弥漫在“50后”、“60后”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老炮儿》里,也弥漫在“70后”、“80后”的《致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 很明显,在严歌苓小说《芳华》中,叙事者对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错综交织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并未急于让“一个人”成为“一代人”,或者让“一代人”代替“一个人”。书中的何小曼成为战斗英雄后,“我”看了关于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个“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人记忆被集体叙说所覆盖后的困惑感与无力感。严歌苓说:“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而集体叙说则是要在这许多层面中,找到高度凝练的那个惟一的层面,个体只得湮没其中陷入失语境地。 这种清醒和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严歌苓曾说在《芳华》中想要寻求一种写作方式上的创新尝试。叙述者“我”——小穗子既参与记忆之中,又随时准备跳出故事之外。在娓娓讲述后又笔锋一转,“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一句话毫不留情地将读者拽出故事,与讲述者一同冷静旁观。这种安排颇有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味道,演员在台上突然跳出剧情直接面向观众讲话,使观众不会沉浸于剧情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感受。一言蔽之,讲述者或表演者是要让观众读者去思考,而不是去体验。 这种手法在严歌苓其他小说中早就初见端倪,比如《扶桑》《穗子物语》等,只不过《芳华》运用得更加纯熟更加得心应手,或许和小说的独特题材有一定关系。从12岁开始的文工团生涯,可谓严歌苓窗前的白月光、胸前的朱砂痣。严歌苓说,《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她一再强调这个故事的“诚实”、“真实”,但也毫不讳言个人记忆的碎片化和不可信赖,以及叙述中的虚构重组。“小曼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小说中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是。任何历史都是通过叙述被不断接近的,虽然永远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真相——如果真的有所谓“真相”的话。记忆与现实交错呈现,叙事的时间线被故意混淆,这种手法与叙事者无处不在的自我怀疑、自我反思非常契合,在文本的缠绕中,故事剥丝抽茧一步步露出全貌。 事实上,严歌苓在处理其他题材时,一直是一个注重外部体验的作家。写《小姨多鹤》,她住进日本村子去;写《妈阁是座城》,她去了澳门赌场;写《陆犯焉识》,她去青海农场采访。她以一种新闻记者式的严谨与敏锐,探寻秘密,发现人物,收集细节,然后重新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而在处理以《芳华》《穗子物语》等为代表的文工团题材时,面对最为切近真实的生命体验,严歌苓恰如其分地保持了距离,个人记忆的原始形态得以保存。因其自身经历的独特性,隔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隔着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隔着个人经历与历史变迁,严歌苓实现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审视乃至审判。 对个人记忆的深入探索,不仅使严歌苓在处理同类题材时避免掉入“伤痕”“反思”的窠臼,也为她其他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养分。“地母”情结是谈论严歌苓小说时无法绕过的一个主题,她笔下的女性隐忍奉献、温厚和平,顺从所有的苦难,宽恕所有的伤害,如同大地般滋养着别人,比如《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等。文工团题材作品中并没有这个典型形象,但又依稀可以从“好人”刘峰、照顾刘峰的何小曼身上看到隐约的影子。在对早期文工团经历的回顾中,作者必然要思考一些问题,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生命如何面对生命中固有的苦难。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何演变为“地母”形象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诚然,个人记忆一旦开始被回顾、被叙说、被阅读,就无法摆脱集体化的命运。如何与历史、与记忆、与自己和解,对于写作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在路上”的课题。也许虚构与现实、历史与个人、记忆与现实、碎片与整体,永远是两位一体的存在,不可能割裂,也不可能统一。在《芳华》中它们和谐共存,隔空对话,犹豫地试探地触探着过往曾经。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