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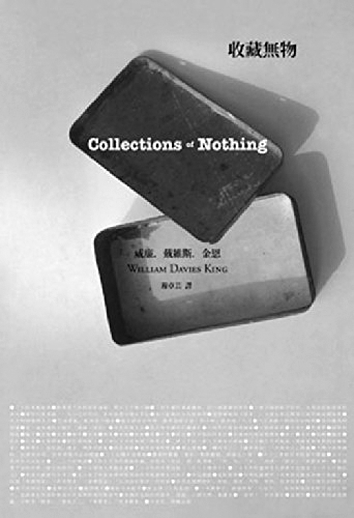 关于收藏这件事,恐怕再难以找到内容和叙事方式上反差如此之大的两本书。弗朗西斯·亨利·泰勒的《艺术收藏的历史》(秦传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它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有趣的细节展现了西方世界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19世纪初期2000多年的艺术收藏的历史。”而威廉·戴维斯·金恩(William Davies King)的《收藏无物》(缪思出版有限公司,远足文化事业,2012年3月)所谈的,是个人的收藏怪癖:他收藏被世人丢弃、被收藏家认为毫无价值的生活垃圾,如食品标签、瓶盖、废金属零件等等,收藏的是“无物”。在叙述方法上,前者通史式的写作框架与后者个人心灵的独白更是全然不同。 我是几乎同时阅读这两本书的,读的时候不断想到:它们其实都是从收藏的角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一本谈人类的文化财富如何积累传承、如何塑造人类文化自身,另一本谈个人的内心世界如何质疑和反思收藏的“有”与“无”、如何从“拥有”中认识生与死的真谛;从根本的价值观上说,它们分别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关于“有”和“无”的价值判断。另外,在收藏作为人类宏大文化记忆的“常态”行为和作为个人最隐秘内心世界而呈现的“病态”行为之间,所存在的价值判断的反差是否从一个隐秘角度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自我反思的盲点?由此,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关于收藏的价值观念的两极论述:辉煌与黯淡、虚幻与真实、集体与个人、物质与心灵……无论如何,这两部书虽然只是偶然被我同时阅读,但是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反差关系,其中有对比、驱魅和反思。 《艺术收藏的历史》原名The Taste of Angels: A History of Art Collecting from Rameses to Napoleon,初版于1948年。该书所叙述的是以艺术收藏为中心的时代、国家、观念、人物的故事,叙述方式很平实、老派,没有时下某些史论著述的花里胡哨。作者泰勒(Francis Henry Taylor,1903-1957)是美国著名的博物馆管理者和艺术品收藏家,曾执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部收藏史是他艺术收藏与管理生涯的学术总结。而《收藏无物》的作者金恩(William Davies King)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戏剧教授,在他成长过程中曾经有家庭的忧郁和压抑体验,在以后的人际关系中也常常伴随着孤独、压抑的氛围。正是这些生命体验使他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更多地面向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尽管他既不缺乏组织戏剧表演的创意和能力,也不缺乏严谨的逻辑学术训练和在学术生产体制中获得学术奖项的经历。他的这部《收藏无物》原名Collections of Nothing,200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以“无物”通向个人心灵的秘密通道。泰勒与金恩,他们完全是在不同的个人体验和写作语境中出发,在同一个“收藏” 的概念下拉开了最大的距离。 不过,即便有如此大的距离,这两部书仍然有着共同的焦点,那就是“物”背后的“人”。泰勒认为艺术收藏是一种本能的现象,是内在个体一种复杂的、抑制不住的表达,不可一概斥之为纯粹的时尚或对名声的渴望;它有点像魔鬼,一些伟大人物也经常被这个魔鬼附体。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穿透遮蔽画布的那层清漆,希望进一步找出藏在图画后面的人”;同时他还认识到,“这些个体彼此之间差别很大,却都是他们各自时代和各自国家的典型代表”(导言,第1-2页)。因此泰勒笔下的收藏家、艺术资助人都充满了复杂的个性与时代的印痕,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美第奇家族、哈布斯堡家族、路易十四、红衣主教黎塞留、蓬巴杜夫人、凯瑟琳大帝、拿破仑等等,无论是用“热情洋溢”还是“贪婪无度”来形容他们对艺术收藏的态度,都可以满足读者对这些关心艺术的人的好奇心——关于他们的品味与雄心。或者更重要的是,认识他们是如何在“占有”中“被占有”的,例如法国红衣主教、曾任路易十四的首相的马萨林在去世前的某一天向他的藏宝告别的情景:他说“我要离开所有这些东西了”,“为了弄到这些东西耗费了我多么巨大的努力。我能够离开它们吗?我能够抛下它们而不感到丝毫惋惜吗?……在我即将去的那个地方,我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泰勒认为这“显示了一个人所占有的东西在怎样的程度上占有了其占有者”(第250页)。 关于“物”背后的“人”,金恩在书中则有更多直抒胸臆的评述:“人类普遍拥有的收藏欲望来自两道伤害,一道源自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最物质的社会,一道源自个人的生命历程。”(第22页);“人太容易误判价值而沦为输家,视大为小,视小为大,但在一个供应太多的世界,两袖清风又好像双重剥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关注别人一举一动的焦虑加深了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价值变成空前困难的问题,收藏是回应问题的一种社会形式,一种控制贪婪社会的方法。”(第23页)收藏来自人受到的社会伤害、来自价值判断的危机,这是深刻的社会学视角。虽然金恩该书更多是通过收藏而讲述个人成长中的心理动机和阴影,但是对社会性背景的深刻洞察构成了剖析收藏与人性的坚实基础。金恩关于收藏的论述可以联系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成了主宰当代生活的最重要权力,成了一切伦理的基础,生活价值的真实性已不复存在;大型技术统治组织极力引起无法克制的欲望,并且在欲望的实现中创建了用以取代旧的不同阶级区分的新的社会等级(参阅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除了对“人”的关注以外,这两部关于收藏的书还有一个共同的、但是容易被忽略的角度,那就是经济学的视角。泰勒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确立(不管多么模糊)艺术品在它赖以创造或获取的那个社会中的相对价值。”因此,他在书中大量论述了各时代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劳务报酬等与艺术家和艺术收藏者的关系,从中我们知道,直到十五世纪中叶,艺术家在经济上才达到了小店主的同等水平,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艺术收藏史如何成了南欧家族世袭财产变卖给北欧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历史。而在金恩的书里,极为微观的经济学视角随处出现,“清贫”与“收藏”的关系使一段卑微、琐碎的人生浮现出一抹温暖的色彩。例如当他在每周六参加拍卖会的时候,都期待着能让自己仅有的一、二美元派上用场(第60页);他曾认真地计算把微型插图从十七本词典上剪下来粘帖到自己的收藏本上所花费的物质成本和劳动成本(第216页)。在金恩看来,收藏绝非仅是富人们的游戏,同时他也精准地揭穿了收藏市场的嗜利性:“收藏经常凸显出资本体系的荒谬,……收藏者总是在等候物质世界陷入疯狂,他们的遐想全都寄托其中。”(第100页) 关于收藏与政治的关系,金恩当然少有直接的论述,因为在他的“无物”之中难有政治性的遗产。在泰勒的收藏史观中,政治则是相当重要的议题。第七章“艺术与法兰西专制主义”指出,黎塞留把“文艺复兴期艺术家和批评家构想出来的那种古典权威嫁接到了绝对君主制的学说之上,为国王对艺术的真正资助提供了一个逻辑基础和法律基础”(第241页)。与此相同的是,当雅各宾革命积累起了势头之后,对艺术品的需求就越来越成为新权威的一个象征(第372页)。 于是,我们不妨重温泰勒关于收藏是一个附体的魔鬼的说法,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伟大的还是渺小的心灵,这都是一个深刻的比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