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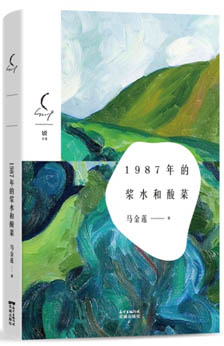
近期,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写作被誉为“当代呼兰河传”的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最新著作《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作品中,马金莲用深情的笔调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岁月,用细腻、质朴的笔触书写生活中那些让人动心的细碎鳞片,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回民家庭的生活往事。
我的文字注定绕不开土地和乡里
记者:请简要说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这本书吧。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是我的第四本小说集,之前我已经出版有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难肠》等。这本书是我近两年创作部分作品的一个选集,收录了七篇作品,其中有四篇的题目和年份有关,因为我一直写乡土,而且总是写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西海固乡村生活,而那样的生活真的不好写,因为别人早就写过无数遍了,为了避免踏着前人的步子重复,挖掘出新意,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我选择了一种相对比较疏离的方式,就是从题目开始便明确告诉读者我笔触将要延伸的地域和时间段,这样我自己写起来也没有压力,可以一心沉浸在过去的生活里,慢慢地用情感浸润故事,慢慢地打磨我需要的情节,挖掘时光缝隙里泛着暗香的那些让人动心的细碎鳞片,只要是投入并沉溺其中的写作,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价值的。其中我最喜欢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我用深情的笔调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和那种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生活方式。清贫、寒酸、苦涩的日子里,何尝没有处处蕴含温情与良善,这样的品质在今天是稀缺的,这也是我怀念的意义所在。我已经在后记里说过,这是我第一次和花城出版社合作,但是很愉快,整个合作的过程流畅,一些来往的细节感人,感谢花城出版社和责编老师。
记者:在评论家的视野里,往往把你划入乡土派,纵观你的作品,感觉你的小说的确属于80后中的乡土派,我想你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对这种生活再熟悉不过,可否请你勾勒一下你生长的环境?父母亲戚是怎样的人?你和你周围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生长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你是否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吃过苦、挨过饿、受过穷?
马金莲:说起八零后的写作,我首先想到了我自己。也许这样的下意识其实带着一种一厢情愿和自我迷恋。在当下的纯文学写作的八零后群体中,我觉得自己的位置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一来是我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一个回族,我的作品里自然会带有一个民族的特殊印记。二来,我生长于西海固并且书写的对象一直是西海固。至于西海固的特殊性,相信不用我多说,不少人是知道的。
至于我是否属于乡土派,我没有想过。我们这里总体来说是宁夏南部山区,地域偏僻,气候干旱,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而且基本都是靠天吃饭的那种农业生产。在我成长记忆里,可以说十年九旱,三年一大旱,两年一小旱,干旱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干旱倒是不正常了。
我出生在西海固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里,这个村庄就是我后来不断书写的扇子湾。二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在扇子湾生活,除了去学校上学,暑假都是帮父母务农,寒假在村庄里陪伴家人过着寂静的日子。村庄交通不便,我小时候我们要去集市上,十多里山路靠步行和毛驴驮载,后来才有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靠的是村庄中间水沟里的一眼清泉。夏季用水量大,大家需要一大早排队去担水,冬季泉口结冰,厚厚一层,蹲着是舀不到水的,我们就给水瓢装上巨长的木柄,这样才能伸进泉眼去。我们的童年是在很散漫的环境里长大的,那时候这里极度不重视教育,女童教育更是薄弱,所以村庄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不念书。我们夏天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拔柴、割草、除草、放羊……小脸蛋被风吹日晒得粗糙而褐红。冬天大家就在一起学习做针线。清真寺里遇到圣纪节的话,我们会成群结伙去寺里跟圣纪。总之,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是一种很自由很散漫的童年,没有学习任务,就在大自然里接受着磨练。
我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正是因为这个有利条件,才为我童年时候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条件。母亲等人都是农民,亲戚也都是农民。我们把农民叫做泥腿子,想想其实挺形象,常年在土里劳作,两腿自然是粘着泥土的,这泥腿子很形象地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一个群体的艰难和苦难。
每一个在西海固山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都要经历一个被生计磨砺的过程。尤其像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母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在家里劳力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女孩子自然得像男孩子一样去挑起劳作的担子。我很早就学会了女孩子必须会的活儿,后来还像男孩一样承担了一些繁重的苦活儿,比如赶着牲口犁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拉架子车,往车上抬粮食口袋,赶着毛驴去磨坊磨面,等等,都是需要比较大的气力的。家里孩子多,土地少,那时候没有挨饿,但是吃得不好,尤其九十年代初西吉连着几年大旱,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我们姐妹都在县城上学,家里开支很大,在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和别的八零后相比,我们西海固山区的孩子,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偏僻落后,还有苦难对生命个体的考验和磨砺。后来我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是中专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在家待业好几年,期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那时候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因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要像每一个成年男女一样从事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相比之下,亲生父母还是比较娇惯我的,有些很繁重的活儿舍不得叫我们干,但是到了婆家,不存在这一说,我割麦子,跟着丈夫、小叔子、弟媳妇,一趟一趟,常常苦得站不起来。跟着婆婆做席面招待客人,守在寒冷的小厨房里一忙碌就是一整天,晚上洗完锅灶解下围裙,一双脚早就冻麻木了。西海固的生活,对我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了下来。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围绕土地和乡里,书写苦难,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还是出于一种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悲悯?或者是需要一笔稿费来帮助家里度日?
马金莲:写作写什么?这个可能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困扰过我,因为我一开始呈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故事……都是熟悉的,就在我们扇子湾,就在我们西海固,就是我童年时代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而这些,都是在我熟悉的乡村发生。所以,我的文字注定绕不开土地和乡里,而西海固乡村生活,总是和苦难难以分割,所以,不管我是自觉还是无意,都不可避免地要书写苦难,因为苦难和生活是紧紧依附、交融在一起,是水和乳,是血和肉,绕不开,逃不掉,只能面对。
18岁,开始文学经历,这时候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成熟到去考虑自己拿起笔写点文字的初衷,和需要承载的意义,我更对文学没有产生过什么宏大的梦想。我只是觉得扇子湾的人都活得太苦了,大家的故事活生生的就在眼前,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把他们在生计里的挣扎和苦难表达出来,如果可以算作初衷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初衷了。那时候稿酬低,而且我一年也就发表两三篇,挣那点稿酬,好像改善不了我的处境。之所以一直坚持,还是因为喜爱吧,没有什么太强的功利目的,就是喜欢,而且这样的坚持,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还能带给我内心的丰富和安宁,所以就没有放弃。
怀着虔诚敬仰的心态书写过往的时光
记者:很多人说你延续了萧红文脉,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马金莲: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做《蹲在洋车上》的小文,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如果要在我们之间寻找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我觉得肯定是我们都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凭着本能抒发和表达的愿望,并且将这一本能表现在作品里了。我们的写作,都完全地出于一片赤诚吧。
记者:你的小说里总会出现很多娃娃,这些娃娃大多忧伤而平静,被伤害而不怨恨,例如《糜子》中法图麦在冰雹击落的糜子地里痛快淋漓地狂奔,你也常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马金莲:的确,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虽然后来为了避免单调和重复,也尝试拓展叙述角度,但纵观我目前一百多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儿童视角占据了一半之多。
我文字里书写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关于从前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另一类是关于80年代之后的。
之前的时光,我是通过老人的口述加上自己的想象去体悟的。最庆幸的是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老人都健在。老人们本身就是一段故事,一段从岁月深处跋涉而出的经历,每一个老人的身上都带着个人的传奇和岁月的沉淀,而那些过往的岁月,含着我所向往的馨香和迷恋的味道。太爷爷当年跟着他的父亲拉着讨饭棍子从遥远的陕西到甘肃的张家川,再到西海固落下脚来,到后来经历了海原大地震。自然的灾难在上演,生存的课题在逼迫,这些目不识丁的人,依靠着什么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了那么纯真纯粹朴素简单的品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上世纪80年代初外奶奶常来我家做客,来了就和我们姊妹睡一个炕,她的故事真是装满了肚子,一讲就是半个晚上。还有奶奶呢,这位饱尝了人间冷暖的妇女,肚子里更是塞满了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经历过的,说起来滔滔不绝,真是叫人佩服她那朴素本真却很迷人的口才。我喜欢听故事,听后就记住了,有时候喜欢在干活的间隙回想、琢磨那些故事里的事情,反复回味打动自己的部分,和一些含着深长意味的人生道理。等我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这些故事自然冒出来,我不得不打量它们,然后尝试着写了下来。《坚硬的月光》《老人与窑》《尕师兄》《柳叶哨》《山歌儿》等都是。这些文字里,自然都是已经逝去的岁月里的事情,但是西海固的落后和淳朴,导致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化很慢,当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扇子湾人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具还是很早时候继承下来的。包括居住的地方,大半是黑乌乌的窑洞,里面盘着土炕,炕上有土墙,铺着竹篾席子。装清油的坛子、换水的粗磁水罐、母亲的雪花膏和银粉……我喜欢这些东西,常常抚摸着它们,我觉得一个瓦罐上闪烁的光泽里浸润着岁月的汗渍和呼吸。我借助着这些古旧的器物,让自己一遍遍回到过去的岁月当中。书写那些过往时光故事的时候,我怀着虔敬敬仰的心态,怕自己写不好。而要书写这些故事,切入点自然是儿童视角,童年的那个听故事的我。
另一类,是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的故事,书写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选择自己童年时候的角度,更好表达一些。
记者:你的小说也擅长讲述死亡,在对死亡的情态进行刻画的同时,你对死亡的概念与意义也有所叩问和表达。你似乎对“死亡”这一题材有着特别的执着?
马金莲:我小学三年级时二奶奶肝硬化去世,五年级时三奶奶肝炎辞世,初一时太爷爷口唤,2001年我唯一的弟弟病故,两年后爷爷无常。这都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大家也在死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还有邻近的村庄。我们回族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了,鼓励大家去送葬,送葬是行善的好事。所以从小到大,我参加过的葬礼其实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不同的哭相,听到了不一样的哭声,感受着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叹,还有领悟。总之很小的时候我, 就知道生命苦短,人生不易。当我面对写作的时候,那些去世的面孔,有时候猝不及防地就会冒出来,在眼前赫然呈现,那么新鲜。不写写这样的死亡,这样的题材,我心里不安。写出来,其实是帮助自己克服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吧,毕竟这一命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不防备不迎合,以我笔写我心
记者:你的作品有许多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追忆。有没有想过,如何让自己的写作得到更年轻读者的共鸣?
马金莲: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写道:我的文字都是关于村庄的。我的灵感的源头,就是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今后的写作还是围绕村庄。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对于写作,我始终怀着一颗真挚纯朴的心,喜也罢,忧也罢,用文字点染出内心的真实部分,也就完成了最初的心愿。对于小说,对于这个世界,我都没有别的奢求,就这样一直一直地写着,用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内心朴素的想法,以朴素的方式面对世界。近来总是禁不住思索自己的写作。十年一梦,惊醒之后,蓦然看清,过去的时光里,我就像一个跌入深谷的盲人,凭着本能摸索着寻找出路。我踏遍了深谷的底部,磨穿了鞋子,脚底结上了厚痂。可是我还是没有摸到出路。有一天,忽感眼前一片光亮,我的视力恢复了。可以看清世上的万物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原地踏步。从来就没有走出过谷底。地面上满布着我留下的脚印。写作,究竟该如何进行。很多人说,摆脱苦难,不要再重复苦难,因为西海固作者的作品,给人一眼就有西海固贫穷的影子,有千篇一律的印痕。尤其我们这样的末流作者,更难以摆脱石舒清郭文斌等人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宁夏作家都是一个路子,鲜有新路。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徘徊中,我始终舍不得丢开手中的笔,舍不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淳朴和善良,舍不得生我养我的西海固。我一直沿着苦难的路前行。何去,何从?一段时间之后,我释然了。不是写苦难有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我的笔触不够深入,远远没有挖掘出苦难背后的东西,仅仅浮于讲故事的层面,情节深处那些人性中闪光的鳞片,或者需要批判反思的病垢,都是需要往更深处开拓挖掘的。《绿化树》也写苦难,《心灵史》同样在写苦难。今天,我们距离大师还有多远?跟在大师后面赶路,不是战战兢兢地去防备,避免踩上前面的脚印,刻意回避重复,而是大着胆子,迈开步子走路,说不定,就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会不经意间超越了简单的重复,深化了自己,露出我们自己该有的面目。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写了《父亲的雪》,《坚硬的月光》,《尕师兄》,《山歌儿》,《夜空》,《鲜花与蛇》,《梨花雪》,《瓦罐里的星斗》,《老人与窑》,《暗伤》,《难肠》,《碎媳妇》《绣鸳鸯》《离娘水》《长河》等一百多万字的中短篇。
近来我专门抽时间回过头打量了自己这些年写出的文字。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时间段,前者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故事,后者是我后来经历的生活。我之所以留恋很久之前的时光,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高龄老人,太爷爷,外奶奶,爷爷,奶奶,这些老人都是从岁月的坎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日月更迭和社会变迁,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个感人的传说。我的外奶奶尤其具有传奇色彩。我的奶奶又是个说古今的能手,我陪伴她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她讲故事的氛围中入睡的。被这样的故事熏陶着,那些远去岁月里的故事和那种馨香的味道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我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想起了它们。而老一辈人身上具备的质朴和纯粹,对生活的热爱,对信仰的坚守,让今天浮躁的我们感到汗颜。所以我敬仰那些已经远逝的人们,之所以写那些时光,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敬意,也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对比和反思。同时我是一个八零后,我也会写今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西海固偏僻农村的八零后。那个叫扇子湾的养育了我的地方,它至今还保持着落后和淳朴。到了扇子湾,你会感觉生活倒退了,一切停滞了,1997年才通电,如今没有移动和联通信号,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东西较少,人们挑着扁担去沟里担水饮用,农历六月在地里干活的人们坚持封斋,过圣纪的日子里大家头戴白帽涌往清真寺里。而我小时候经历的生活还要更纯粹更封闭。我的生命最初的塑造就是在那里完成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自然和那个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我笔下的世界与外面的社会保持了相对的距离。
至于如何让自己的写作得到更年轻读者的共鸣,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写东西不是为了刻意去迎合某一部分群体。拿起笔写,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心,给自己的曾经和现在一个交代,记录我的扇子湾,那一群人,那一种生活,足够了。但是不会再简单重复,以后的笔触肯定会向着深厚广博的方向努力,希望写出具有分量的作品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