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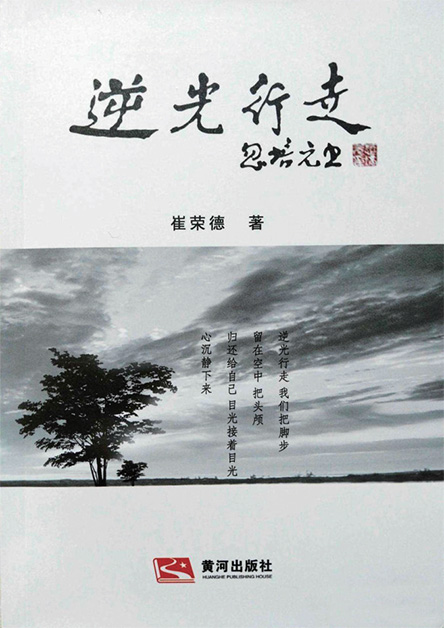
古人说:“诗穷而后工”。为文为诗者,因为“穷”,就发自内心地想表达他的思想和感受,这样的作品,是通过心的淘滤,就比较能够达到真正的“工”。所谓“工”,是真正的质量和水平。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所谓“穷”,穷尽也,不是随意地“玩”,这是一种社会职责,应该认认真真地写,努力地做好,达到苦心孤诣而不是马马虎虎。要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文字,要在自己能力所及处做到极致。苗族诗人崔荣德的生活条件是比较清寒的,但他在诗歌创作上要尽力写好。从他的诗集《低处的树说》来看,虽不能说无可挑剔,但相对而言,他是尽心尽力了,因而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工”。
诗人虽是清贫的,但我从其诗集的总体思想中找不出那种哀哀戚戚、自怨自艾,也迥乎于某些“打工诗人”总以“弱势群体”自命而疏于固化骨质,他是有志气的,如《风吹草低》中所写的,“风吹草低/大地上/全是我们的身影”。“我们”作为普通人,都是根植于大地、最具活力的生命本体。而作为“我们”中的一分子,诗人自己和每一个有志气人的自信,是不应被无视的。诗人无疑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张扬了正气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写了这样的诗句:“去村里走走/不必担心山路是否平坦/只要心里正直/就能走出平坦的大道”。他是一个坚持走正路的诗人。
通读《低处的树说》,我感觉崔荣德的诗歌风格是在柔和中见风骨,既不乏阳刚的内质,但也充满美的柔情,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如《割麦姑娘》:“啊 割麦姑娘/就在你开镰的那一刹那/我也变成一片/金烂烂的麦地/你如何收割”。这样的想象和意象,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浪漫主义色彩,二是爱的本质,三是诗境的创造。
最近又读了他的新著《逆光行走》,我的总体感觉是,他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诗思的旺季,想得较多,写得也不少,总的来说,这是值得称贺的现象。
崔荣德的诗歌创作仍在与时俱进,在原来质扑而有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有所丰富,而且也更加自信,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生活的眼界在不断开阔,诗歌的题材也有很大的开拓,表现手法不仅不呆板、不陈旧,还注入了一些现代的因素。他如今已是从山沟里冲腾而出的诗人,翅尖上飞洒出来的露珠正在润泽更大范围的土地。
他的诗原创性很强,我所说的“原创性”,通俗一点说就是在自家的炉灶上蒸自己的馍,就连喷出来的气息都是自身的味道。譬如,他写了一首《谁说雪花是冰凉的》,其笔下的雪花是能够“熊熊燃烧”的,能够“烧灼一切污秽阴暗的东西/世界从此洁白无瑕”,雪花并不冰冷,雪花能够燃烧,这样的立意与想象,与一般对雪花的定义没有任何的重合。古往今来,诗歌的创意是很容易碰撞和“刮蹭”的,一朵雪花、梅花或者是梨花,翻来覆去就是那些描写的角度。想要创新,是很难的,但我们要勇于探索。
在诗歌的具体词语的使用上,很重视意象的新意。在《逆光行走》中,新颖的意象可谓举不胜举。比如《日落乌江》中的意象:“后来它纵身一跃/坠入乌江/人们从溅起的浪花中才发现/它生命的价值/如此金黄”。“嚼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嚼自己嚼过的馍也没味道”,我欣赏这样出奇制胜的意象。他在语言文字上运用得比较自如,在诗句上大体整齐,但内部结构不乏变化。如词性的适度变换、通感的运用等等。
如果要说他的诗有哪些不足,我想到一个词:“清浅”。崔荣德的诗无疑是有思想、有追求、有韵味的,但通读之后,还有提升的余地,在厚重、浓郁、冲击力、感染力等方面,作者肯定还要努力。
崔荣德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他还会有长足的发展。我只希望他仍要时刻珍重起步时之基础,那是至为可贵的朴厚中的机智。艺术上的求新求变,一定要和时代精神、生命精髓更好地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