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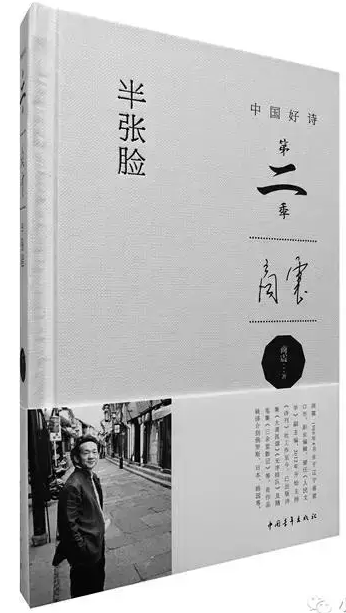
1.这个人,且从这里说起
我想和你谈谈商震的诗歌。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从1960年代,一个诗人的童年总是那么富有诗歌发生学的丰富性,里尔克说:命运总大不过童年密致的内容。但这些交给未来的文学史家似乎更为客观,毕竟,那些密致的内容必须等待时间的酿造。
从1990年代,商震怀揣梦想,在祖国的大地上漫游,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又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合适的居所,在市场、物质和词语的欲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诗歌。对此行为的理解需要整个时代为之作出证词,也许一个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对此更有发言的能力。
而我,似乎只能从2016年开始,从那个就坐在或者站在我的眼前,清瘦,卷发,着中式大褂和黑色布鞋,手持烟斗而双目微张的商震开始,在一片红尘滚滚的喧嚣中,他回过脸去,在人群中将自我挑拣了出来,这个时候——看哪!这个人!
2.这个人端坐在黑暗中,且听到了风
且看商震2016年出版的诗集《半边脸》中开篇第二首诗:
《角力》
月亮飘向远方
乌云与夜媾和
我的全身被涂满黑色
天地间不再有路
也没有方向
黑夜有巨大的胃
我的思绪是一块石头
在夜里只有重量
没有形状
对付黑夜
要用一个清白的我加一个黑色的我
一颗善良的人心和一颗野兽的贪心
当黑风吹灭所有的词语
我心底藏着的阴暗
正在上升
并且比夜还黑
这首诗歌是一种最自我的自白,不是抒情,而是一种冷峻的叙述,读这首诗歌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无边的黑暗和绝望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诗人的回答是“不再有路,也没有方向”。或许我们会想起弗罗斯特著名的《林间路》,因为生命之路的不可选择性,导致了诗人的哲思和悲哀,但在商震这首诗里,却连这二元对立的选择也被彻底取消了,不但被取消,而且黑暗更加浓稠,更加形而上,更加占据世界和人的本原。在这里,世界本原的黑和人心的阴暗形成了对位的关系,他们在互相加深着对方,并在互相的占领着扩大着黑暗的领地,在这里我们隐约读到了海子在其《太阳七部书》里面所描述的黑暗气息,虽然作为一首短诗,它的质量跨度还稍微显得急促了一些。商震在一次访谈里对此有过论述:“这几首诗确实有一种无以言说的‘黑’,不知道其他诗人是如何处理‘黑’的,我基本上是在对一事一物一人用语言无法名状的时候,才动用这个‘黑’字”。无法言说的“黑”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看,也许是诗人主体对于世界一种潜意识的情绪反映,但是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分明又看到了一种类似于的“精神的秩序化”。这一黑暗并没有导致彻底的虚无,而是,他试图在抵抗。“对付黑夜/要用一个清白的我加一个黑色的我/一颗善良的人心和一颗野兽的贪心。”但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在另外一首诗歌《心有雄狮》里面,这种抵抗的复杂性被呈现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形象化。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从陕北以北吹来,这风是狂躁的,四面八方的,制造着强大的噪音,这风由远而近。“一朵瘦小的野菊花/弯下腰躲进草丛里/我也闭上了眼睛”诗人并没有惧怕这可怕的无名的风,恰好相反,与草、野花一样,有一种植物般的生命的韧性在对抗着风以及风带来的黑暗和噪音,而更具有挑战性的是,诗人将内心的“狮吼”藏在了风声中。不,不是藏,而是借助风的声音传达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何等微妙的辩证法。具体的风变成了抽象的风,物质的风变成了命运的风,在科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名作《古舟子咏》中,也是因为一场风引起了命运的转折,而在商震这里,“风”成全了一种古老的智慧,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吼或者啸常常是诗人抒发自我,概叹命运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些诗歌的烈士,一边吟啸吼叫,一边冲向无边的无物之阵。
黑暗是一种对峙,但对峙却不是彻底地对立,对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就像商震诗歌中的一道光,切开了世界黑色的铁幕,里面的底色,原来是如此多姿。
3.这个人喝醉了,且把光阴暗换
商震好饮,圈内闻名。曾经有一次聚餐,我因不饮酒而遭其质疑:不喝酒,怎么做一个批评家?
壶中有乾坤,酒中有玄机。商震对诗与酒的关系有着聪明的认知:“我觉得诗人手中的酒也是诗人本身……酒的歧义性、多元性与诗类似,酒平时穿着水的外衣,浇灌到诗人的心里,就现身火的本性,和诗歌穿着文字的修辞的外衣是一样的。……酒脱掉水的外衣时,诗也脱掉文字修辞的外衣。”
没有在诗与酒中浸淫一番年头,估计说不出这么通透之言。在商震为数众多的“醉酒诗”——这是我对商震以酒事为诗事的一个命名——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夜深独酌》
在我的对面,为你放了一个酒杯
我每喝一口,都要
与你的空杯碰一下
听到“当”的一响
我的心就安稳一瞬
响声里有你的朗笑、躲闪和哀叹
一杯一杯一声一声
我只想痛快地喝醉
不是要把所有的酒喝干
醉了,就敢放心大胆地朗诵:
“东风不与周郎便”
东风不唱蝶恋花——
诗歌的标题是《夜深独酌》,但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似乎又不是一个人。不但不是一个人,简直就是众人。这难道不正是李白式的醉酒美学吗?在“一”与“多”的对饮中,那在诗人心中和眼前浮现的,却是众人的影子。这一人是谁?这众人又是谁?在酒的背后,是造就酒的人与事,在杯的中央,是那些人与事的身影重重。这简直就是一个醉酒的狐步舞,但又暗合着京剧的古典唱腔,在这首诗歌里面,有一种古典性在现代的烛照下熠熠生辉。他让我想起宇文所安论及中国古典诗歌中幽微而绵延的“追忆”传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追忆需要酒,真挚的情谊也需要酒。商震通过酒这一“色媒人”,与古典跳起了圆舞曲。他的步伐踉跄,却又暗含风韵。
醉花阴·荷影;醉花阴·有醉;醉花阴·月牙儿……
如果还嫌不够,那就让他和韩作荣等人来一场大醉,这醉里面,是一种渐渐在消失的可贵的人性。
4.这个人,半张脸就够了
但是商震不是古代人,他是个现代人。现代人,是一种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更是一种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肉体的存在感。
仅仅凭借一种想象中的古代怎么能超脱?
没有关系,商震发明了一种分身术,这种分身术就是——半张脸。
《半张脸》
一个朋友给我照相
只有半张脸
另半张隐在一堵墙的后面
起初我认为他相机的镜头只有一半
或者他只睁开半只眼睛
后来才知道
他只看清了我一半
从此我开始使用这半张脸
在办公室半张脸藏心底下
读历史半张脸挂房梁上
看当下事半张脸塞裤裆里
喝酒说大话半张脸晒干了碾成粉末撒空气中
谈爱论恨半张脸埋坟墓里
半张脸照镜子
半张脸坐马桶上
就用半张脸
已经给足这个世界的面子
对黑暗,商震予以形而上的思考,并以稍微狡黠的方式发出抵抗的狮吼。
对生命,商震且诗且醉,杯中窥月窥人,在追忆和喟叹中发现了光阴的无情和美丽。
而对于现世的生活,商震使用了另外的方式,他以一种肉体的、口语的、当下的姿态和语态来与之纠缠互搏。在这里,诗歌的内容、形式和语言是互相生产的,因为内容是当下的,所以形式必然是戏谑的,而语言必然也就是口语式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在商震的诗歌里面看到了一种非常紧张的撕裂:“半张脸照镜子,半张脸坐马桶上”。他不仅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这种撕裂,而且直接将日常生活内置于诗歌之中:
《屏幕上的我》
几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
我都不敢看
一个化了妆的我
一个笑容和谈吐被编辑过的我
还是不是我
还是鼓足勇气看了屏幕上的我
那个离开了生活琐事的我
那个没有私密情绪的我
每说一个字先在嘴里校正三遍的我
许多朋友都说
屏幕上的我很成功
我突然惊愕起来
难道我体内真的藏着一个
大家都会满意
唯独自己不知道的我?
波德莱尔在论述现代性的起源时说,现代性的一半是永恒,另一半是瞬间即逝。在商震的诗歌写作中,他几乎是直接呈现了这种现代性的悖论,永恒是一种元素和古典性的存在,它只能在黑暗和醉酒的状态下才能抵达;而瞬间即逝的日常生活却以一种重复性构建着它的新的“永恒”和新的“现代”。
这是一枚现代的假牙。他就镶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它时刻提醒我们的,恰好是这样一种真假难辨、犬牙交错的此时此刻:
“和我生命无关的东西
就是长在我身上
也是假的
即使做得再精致
也是没有生命力的配饰。”
“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醉醉醒醒,在努力将自己的精神予以形式化的时刻,我们看到了不止一个商震,不止半张脸,而是更多的商震,更多的脸孔,以及更多的诗、酒和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