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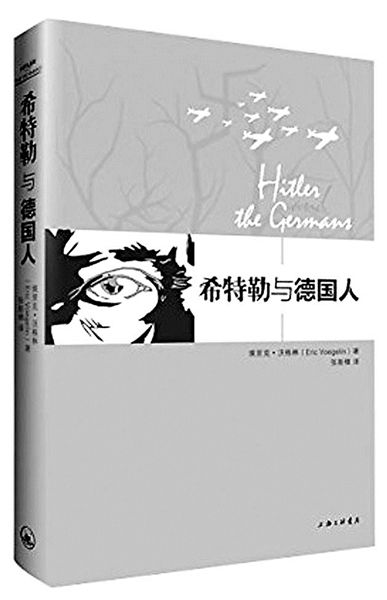
对于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民族经历保持长时期的沉默,是否一种不诚实?将纳粹集中营的罪恶视作一面镜子,照出法西斯魔鬼的狰狞面目,也照出当年屈从于希特勒的邪恶体系,每天得体地工作着的“你和我”,是对德意志民族苛刻的拷问?还是呼唤灵魂进行赎罪的皈依?《希特勒与德国人》自始至终,散发着德国哲学传统那强烈的思辨气息。
德裔美籍哲学教授埃里克·沃格林的这本书,是1964年他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系列讲座的讲稿。这一讲座当时就引发争议,甚至有人为此对他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并不奇怪,直到1946年,大部分德国人还认为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好的理想,只是被执行坏了。甚至在1950年代,“要不是战争的话,希特勒也许会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这种观点还有不少德国人认可。
《希特勒与德国人》勾画了希特勒邪恶的魔鬼形象,同时又去神秘化,解除了希特勒的“魔性”。 作者剖析希特勒的人品——平庸、固执、缺乏教养,一意孤行的小市民品格;他评判希特勒令人无法轻视的实践能力,与令人鄙视的非理性之间的奇怪分裂;他指出希特勒“唯一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为了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政治机会”。 沃格林由此认定:对德国人来说,这个魔鬼并非是个不可解释的引诱者。就这样,作者的凝视对象由希特勒转向那数百万投票支持他的人,以及纳粹时期那些心甘情愿追随他们的元首的“奇怪的边缘人物”。他的笔触开掘的,是希特勒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系。那段历史令德国人最初回顾时,产生了强烈的战栗感。可是,战栗感会转变,用当年的“糊涂”来搪塞、推诿,逐渐演变为事不关己的超脱感。沃格林质问的,就是德国人从战栗到超脱之间的改头换面。
作者将当年德国的上层阶级列为清算对象,他们都跟纳粹政权的罪恶和愚蠢有着牵连和纠葛。可是帝国崩溃后,这些有声望的阶层居然用超脱感掩饰自己,不愿承认,他们知晓当年罪恶的疯狂,一旦承认了,就意味着暴露自己的罪孽。《希特勒与德国人》认定:倘若造成暴行的精神结构不得到清算,那么德国社会就不可能发生令人信服的改变。沃格林教授凝视那段历史,对德国小市民的气质、精英阶层的思想堕落,包括宗教徒的信仰丧失,一一批判。他提醒世人:当年对波兰人民进行大屠杀,旨在灭绝波兰人,为德国扩展生存空间的那支突击队,其成员的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然而德国天主教没有一位代表“告诉那些仍然幸福地待在教会中的党卫队成员说:人,是不允许杀人的。”
《希特勒与德国人》引经据典。书中从政治学视角阐述“统治者”,所调遣的史料是查士丁尼大帝的政权观三因素:权力、理性和精神。统治者作为社会代表:他必须拥有权力,是最高统帅;他必须是一个有宗教性良知的人;他必须是信仰的护卫者。尽管希特勒拥有的权力意味着极高的效率,可他却是个丧失良知和理性的精神的分裂者,居然将这样的人推上统治者之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德国上层的精神结构,无疑是可鄙的。作者还分析了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民主,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即民主要以三个因素为基础——“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以及既不利用前者也不利用后者的审慎。”他认为,即使在1964年,联邦德国已经拥有了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可不利用前者也不利用后者的审慎,则非常不足。“只要这个第三因素还有欠缺,民主制就无法运作。”
沃格林教授的这些观点,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重又在西方印制出版的今天,更有极为可贵的思想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