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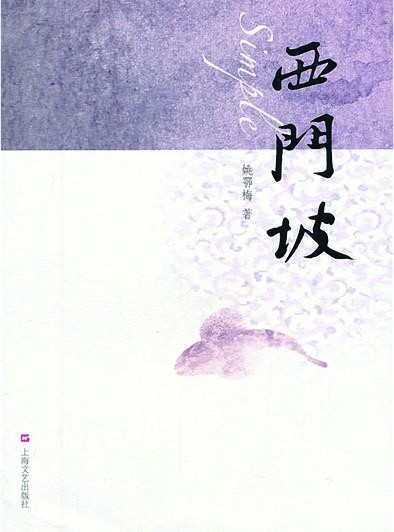

姚鄂梅小说作品
在上海时,姚鄂梅的住所没有电梯。这是快递员最不喜欢的,他们不是唉声叹气往上爬,就是没好气,甚至火冒三丈,只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各种数据线、戴眼镜的小伙子,每次都像豹子般一口气冲上来,双手将快递递给她,再一溜烟冲下楼去。他似乎从不觉得累,也从不觉得烦,相反好像有点享受他的工作。有一天,快递员告诉她,那天是他最后一次送快递,因为他找到了新工作。他还说,自己一直都知道,快递员只是个过渡,说不定现在的工作依然是个过渡。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无数梦想在熄灭,也在绽放。“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伙子,而那几个唉声叹气的快递员,依然满脸不高兴地在陈旧的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喜欢有梦的人,哪怕这个梦很小,就像一只鸡,穷其一生,也只飞到矮树上。”姚鄂梅说。而这些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快递员,最终触动她写下最新长篇《贴地飞行》。这部近期发表在《钟山》长篇小说专号上的小说,用作家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
“姚鄂梅的小说经常关注平凡人的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的。她把一个荒蛮的时代切开一个个口子,深挖下去,直到观察到它的毛细血管,然后撕开伦理的面纱,打破各种笼罩的幻觉,不断用故事碰触情感的极限,把七零八落、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重演一遍给人看。”青年评论家项静曾这样评论姚鄂梅的写作。在《贴地飞行》里,作家继续从细微处窥见一个时代的痛处,在日常里道出最深刻的人心。
记者:《贴地飞行》以几个底层人物为主角展开书写,自然可以归入底层书写的范围。底层书写是近年来的写作热点,但热点也容易造成认知的模式化。然而,在阅读中,这部小说的人物设置还是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比如说主人公杨粒,曾经的乡村教师身份让他有了与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不同的精神底气,也成为他在逆境中不断前行的推动力。但正因如此,主人公会有比旁人更多的骄傲,更深的失落,更痛的感悟。为何会为角色设定这个背景?
姚鄂梅:在《贴地飞行》中,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新的群体。最初进城做流水线的那一代人,可能仅仅满足于挣钱,然后寄回去养家,城市对他们来说,跟山里的煤矿没有太大区别。《贴地飞行》里的主人公们则不同,他们是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几乎是农村的精英,但农村不能为他们提供舞台,农村没法留住他们,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养料,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地跑进城里。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慷慨地接纳他们,一方面又在暗暗地嫌弃他们,但是,正如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们的人生也是没有退路的,家乡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归宿,也不是加油站,仅仅只是出生地而已,除非实在待不下去,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城市的。如果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正因为如此,和城市上班族相比,他们的流动性更强,更加不稳定,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加缺乏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的命名来看,一面是轻盈的飞行,一面是与深厚土地的无限接近,所以才是贴地飞行。书中的人物无一不想逃离自己的原生状态,但又无一不是被自己的曾经所累。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困境么?
姚鄂梅: 这个小说从酝酿到最终形成,耗时一年,对一个长篇来说,不算是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对这样的人群很熟悉,我和他们经历相似,从农村到小城,从小城到大城,不同的是,我比他们早几年到达城市,并且非常幸运地成了一个证件齐全、拥有身份的城漂。这些证件令我在缓慢往前爬行时有个最低保障,有时我觉得我就是杨粒们从老家出来的大姐姐,我猜杨粒们也一定很希望生活中能有我这样一个姐姐,姐姐等于是他们在城市这个庞然大物身上钻下的一个口子,没有这样一个口子,他们对城市的了解可能永远止于皮毛,永远只能在城市的表面行走,即使服务一辈子,也无法真正融进城市,我觉得这才是杨粒们的人生困境,他们可以在城里献出一切,但城市对他们的一切并不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说,《贴地飞行》里的“地”就是城市的生态。城市是高傲的,不单单对杨粒们,对各个阶层都是如此。只不过,杨粒们更加脆弱无力,因而体会到更大的压力。
记者:女作家难免会被冠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在以往的写作中,你也塑造了不少成功的女性角色。在这部小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袁圆这一角色。她在与旧家庭决裂之前的形象,和热播电视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有重合之处。在“重生”后,她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都市或乡村女性的性格。你如何看待这个人物?
姚鄂梅:袁圆这个人物最初并没有这么重的戏份,一开始我只想写一个在城里左冲右突的男人,如何为了生存而不是出于寻找激情的原因,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焦头烂额的故事。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一部传奇,但表面上他们特别简单,他们的人生是分段规划和计算的,缺乏整体性,盲目,不计成本,从这一阶段到下一阶段,很多衔接被他们快刀斩乱麻一般粗暴切断。
当我写到袁圆用极端的手段制造自己的“重生”时,我一下子爱上了她,她从家庭的压榨中觉醒过来,走上了反抗之路,她是有能力设计新生的,可惜她碰上了跟她一样有着强烈欲求的男人,当她想要利用他时,反被他利用,像袁圆这么聪明的女孩,应该去跟一个高段位的男人过过手,接受关照的同时还可以学个一招半式,可惜种种因素制约着她,她没有机会碰上那样的男人,这正是袁圆们的悲剧,她只能碰上杨粒这样跟她同样目的的同类。
记者:这是一个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但无时无刻不弥漫着乡村的气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生活在城市里,却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是小说家无论穷尽多少故事都言说不尽的。在当下热火朝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你会如何认识乡村和城市的关系?
姚鄂梅: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一条血腥之路,多少人多少梦想在这条路上被辗为齑粉,这一点不仅乡村体会强烈,城市也一样经历着烦躁不安辗转难眠的痛苦。乡村被切割,人被大批大批地赶往城市,城市的空间被挤压,被侵占。城市别无选择,只有向更大的空间发展,而拓展更大的空间,势必造成对乡村更大力度的切割,这是一个梯级推进的过程,城市的核心圈里依然只有城市的原住民,外来者游移在圈外,更新的外来者游移在更边缘的圈外,城市化首先是从地理上的城市化开始的,真正做到人文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几个形容词来固定某位作家的公众形象,但是,从《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到《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成长,女性,历史,金融,家族,乌托邦……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出人意料的转折。
姚鄂梅: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只有一个原则,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自己自认为可以去完全了解的事物。
我最初的写作全凭直觉。从这点来说,写作跟数学很相似,它们都是从直觉开始的,比如几何,你就是觉得这个角和那个角是相等的,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找出证明那两个角相等的定理。小说就是那个求证的过程,后来,写得越多,直觉反而越迟钝,这时就需要理性的思考来帮忙,但理性的东西不好直接进入小说,得有一个化的过程,把理性感性化,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是生硬,就是过了头。
我比较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比如《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西门坡》,除此以外,《真相》里那个女孩的特异功能,《一面是金,一面是铜》里那个酷爱滑板的男孩,《1958:陈情书》里的小尼姑慧德,其实也都不能算是特别现实主义手法里的人物,与其说他们身上有何种现实意义,不如说他们身上有一种象征主义。
记者:你似乎一直在游走,生活过的城市有宜昌、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在不同气质的城市生活,对你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方式可有产生什么影响?
姚鄂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气质,这个气质决定了你如何观察事物,什么样的事物能让你有反应,跟地理倒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我是个对细节感兴趣的人,有时,跟人聊天,或者听别人聊天,会突然被几句话打动,我会把它存在心底,等它发酵。
我非常赞同你“不同气质的城市生活,对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方式会有影响”的说法,当我们置身一个城市,在我们熟悉那个城市的语言和路名之前,我们最先了解的其实是这个城市的细节,有了细节就有了可以引路的感觉,有了探索下去的动力。到目前为止 我写过的地域性比较强的小说只有《白话雾落》,当时我认为我是在跟故土告别,现在来看,我真是太浅薄了,人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别,那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难以清除,你可以掩盖,可以假装它不存在,但总有一刻,不经意间,它会冷不丁地冒出来,所以无论你到了哪里,到过多少地方,你的出发地永远不会从你生命史上消除,它会像登记表上的祖籍一样伴你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