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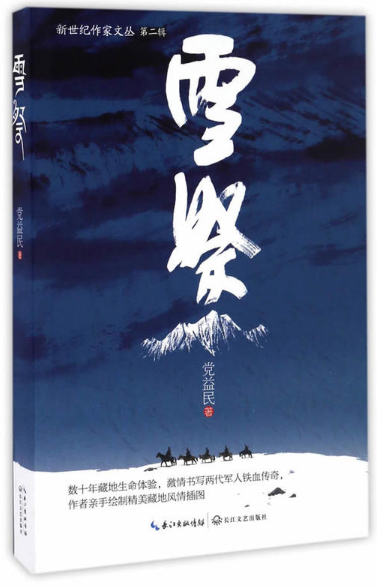
《雪祭》,党益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36.00元
我的许多战友长眠在了高原,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谁来写?我有责任告诉读者高原上发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战友们的英灵。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
“我19岁进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掩埋着我们许多战友。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那里的自然风物和人文环境,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先后进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将西藏紧紧拥抱,又像一条条搏动的血脉,联结着内地与西藏。”
关于西藏,党益民写过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和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还出版过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但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川藏线、新藏线,也包括中尼公路,而西藏的另外两条重要公路——青藏线和那昌线没有涉猎。“不是不想去写,而是一直没敢去触碰这块在我心里最柔软最敏感的地方。”党益民说,西藏是他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每当他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时隔二十年,才写这一段西藏往事?
党益民:我一当兵就在海拔四五千的青藏线唐古拉山修筑公路,我们先后有一百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掩埋在山下的格尔木烈士陵园。部队后来转战到了藏东高原的那昌线,也先后有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的雪拉山上。我亲眼目睹过战友的牺牲,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的场面,一想起来就让我肝肠寸断,浑身战栗。我不忍心去回忆,所以一直没敢动笔。
后来上级将我调离高原,交流到了零海拔的辽沈地区工作。站在海边,呼吸着充足的氧气,想起高海拔地区发生的事情,恍若隔世。我曾对驻扎在海边的部队官兵讲:你们在这么好的地方当兵,要知足,要珍惜。与艰苦的高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你们起码不用住帐篷喝雪水,起码有充足的氧气可以呼吸,起码不会担心因为一场感冒而丢掉性命,起码不会担心雪崩突然从天而降。就是这种零海拔和高海拔强烈的反差,让我突然决定写这部书。我的许多战友长眠在了高原,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谁来写?我有责任告诉读者高原上发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战友们的英灵。
中华读书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一而再地将它混淆为纪实文学。这种真实感,大概缘于无比生动饱满的细节。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多次入藏采访的深入体会,是否《雪祭》的写作相对轻松?
党益民:一点也不轻松。我的叙述语调看似很平静、很节制,但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一直在翻江倒海。平静是高原军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艰苦的环境里,高原官兵已经习惯了忍耐,见惯了牺牲。我用平静的口吻讲述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态与品性。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煽情,不喜欢故弄玄虚,也不想在叙述中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对战友的深情转化为一种尊重、理解和体谅。
我用叙述人称与时态的变化,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用刻意的疏离保证叙事的真实。书中的人物不是现实中的“那一个”,是重新组合过的“这一个”,但故事是真实的,细节是真实的,这就是您为什么有“纪实”之感的缘故。小说本来就是弄假成真的艺术,何况我有高原亲历作为创作基础。小说创作的难度,是站在令人信服的真实之上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制造真实的幻觉,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写《雪祭》的过程,我想可能对您来说在情感处理上是一次挑战。因为您既融入了对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又有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党益民:三年前,我在大连一个海岛部队“蹲点”时,突然产生了创作《雪祭》的冲动。后来上级安排我去“零海拔”三亚疗养,再次勾起我对“高海拔”的怀念,那种浓烈的情感无法抑制,于是便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写起来很顺手,几乎是一气呵成。当时我的感冒还没有好利索,一边咳嗽一边写作。我最怕感冒,一感冒就咳嗽,而且很难痊愈,一般都得折腾一两月。这是高原给我留下的“纪念”。我在高原得过几次重感冒,几乎死掉——高原感冒引起肺水肿而导致死亡并不稀奇,我的肺部受过伤害,留下了后遗症。咳嗽着,回忆着,痛着,写着,这种状态很符合对高原生活的书写。
英雄主义在和平时代已经被冷落了,总得有人回望与坚守。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他们不是不想追求个人享受与家庭幸福,但是职责让他们选择了奉献与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在巨大痛苦里表现出忍耐与平静,在大难临头时表现出从容与淡定,是因为他们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经历过太多的生死劫难。高原现实中的“死亡”比书中写到的还要多,但我实在不忍心让那么多“战友”死去,所以在最后修改时,我又让赵天成“活”了过来。
中华读书报:作品以第一人称破题做引子,随后却转入第三人称讲述——在作品结构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党益民: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是由题材决定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这个题材。第一人称是为了让读者感到“真实”,况且现实中的我就是从高原走来,带着冰雪的气息。后面转入第三人称叙述,包括倒叙、插叙、自述等多种手法,我认为这种多视角叙述,更能体现故事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复杂多义性。
中华读书报:开头第一句话:“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讲述这个故事?
党益民: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亡灵叙事,而是设置了一个悬念,小说最后给出了现实的答案:当众人以为连长赵天成在执行任务中已经牺牲,战友们为他建起了衣冠塚,他却并没有死,只是被雪崩冲下山谷暂时掩埋,在葬礼即将结束时,他在“满天飞雪中,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我在创作每部书时,都在极力寻找属于“这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腔调、句式。只有另辟蹊径,敢于创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别精彩,每个人物都让人过目不忘。炊事班长兰洲为改善连里官兵生活,抓雪鸡被冻死;城市兵牛大伟怕苦装病想通过打小报告和行贿改善处境;赵天成对战友兼同乡刘铁手足般的情谊……还有赵天成的妻子、女医生黄雪丽。这些人物不同性格的碰撞非常精彩,栩栩如生。您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写这些人物的?有没有觉得不好把握的人物心理?
党益民:这些人物是我过去战友的一个或多个的重组,他们想些什么,有哪些喜怒哀乐,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所以没什么不好把握的。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车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这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是有缺点但却令人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都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