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春秋》 新星出版社 201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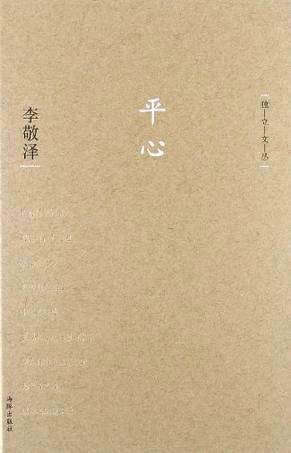
《平心》 海豚出版社 2012年8月

《致理想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青鸟故事集》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李敬泽参加深圳龙岗“文学名家讲坛”。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素来以精准、锐利的文学评论为世人所知,而年初,他自称“新锐作家”,推出了新书《青鸟故事集》。在这本书里,李敬泽如考古学家般穿行于博杂的历史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编织出逝去年代错综复杂的图景。
新书以一种难以定性的文体,将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传统与现代化、虚构与非虚构的复杂关系一一展现。他尝试去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那些曾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传递文明的使者,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们的踪迹,倾听他们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日前,李敬泽来到深圳,做客“文学名家讲坛”和“深圳晚八点”,并接受晶报的专访。在他看来,是小说还是散文,是历史作品还是虚构想象,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将历史中诸多隐蔽的小线索一一串起,在历史的回顾中认清现在和“远方”。
“最初,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一个怎样的作品”
晶报:《青鸟故事集》的宣传语说“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辩,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虚构的内容,也有非虚构的内容,像小说又像散文,似乎很难说清是什么文体。有评论家说这是一种“超文本”或者说“超写作”,您本人怎么看这种评论?
李敬泽:我过去的头衔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以前我评论别人的文章总是能一二三四说出道道来,只见别人频频点头,这让我觉得,“你看,我还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评论家嘛!”现在我自己写出这样一本书,也不得不搞各种活动,听各路评论家来谈我这本书,我一边听,一边也是频频点头,赞其“说得好”。但其实我心里是想,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么多,评论家太厉害了,一开始他们说“超文本”,我还有点愣,还接不上。现在因为搞过几次活动,各种批评家都反复说了,越说我越觉得有道理,越说越是那么回事,他们真的能够把我没想到的全说出来(笑)。
晶报:那您当初写作时候是怎么想的?这些评论家究竟想对了吗?
李敬泽:为什么我愿意承认“超文本”这样的说法?客观地说,对我而言,写这本《青鸟故事集》其实不是特别具有自觉性的写作,或者说,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一个怎样的作品。主要是出于兴趣,觉得好玩。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儿应该虚构一下,还是不应该虚构?应该这样写还是那样写?我真正想的是,我们面对历史那么多隐蔽的小线索,等于面对一片混沌,然后你在这片混沌里面,用一种结构、一个形式,让它清晰起来,把本来没有故事的一件事,渐渐说出一个故事,有了逻辑,还有了意义。
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而且能够感觉到有一种形式感渐渐浮现出来。这就是写作的状态和文学批评状态的差异。写作时不能想太多,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也不能想太多一样,人在进入生命中一个创造状态时是不能分心太多的。
“有时候我们应该回到先秦
回到写作大自由的状态”
晶报:实际上您的写作已发生很多的转变。往小里说是散文,往大里说就是把各种文体的边界和壁垒拆除。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这种拆除的过程中没有造成阅读的障碍。您是如何做到的?
李敬泽:首先一定要有快感。文章也好、表达也好,它本身的写作过程一定是充满表达之快感的。如果一点表达快感都没有,那这个文章就不必写了。界限都是后来的,所以我现在喜欢举一个例子,庄子写什么?一本《庄子》写的是什么?是在写小说吗?在写寓言吗?还是在搞哲学?庄子如果在当今的高校搞研究,一定评不上教授(笑)。
我们看中国文学史,每到走投无路了,文起八代之衰怎么办?路走绝了怎么办?都说我们要回到先秦去。为什么要回先秦?先秦是我们文章初创的伟大时代,混沌初开,没有那么多的区分和界限,这些伟大的写作者,他们心里是没规矩的,他们就是立规矩的人,完全是磅礴自由的表达。
晶报:对,那时候的很多历史写作,很难说没有虚构的成分。
李敬泽:现在我们一写散文就老有人来推敲,文章的某个地方是虚构了还是没虚构。我们回头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左丘明的《左传》,他们根本没想那么多。《左传》里有一个故事,写刺客奉命去刺杀赵盾,看到赵盾一个人正襟危坐,一看就是在思考国家大事和天下苍生。刺客就想,不应该杀这样一个君子,杀了就亏了良心。但又领了命,怎么办?一看身边有棵大树,那就撞死算了。赵盾看到撞死的刺客,不禁颇为惋惜,感慨这是一个义士。
这是多好的一个故事,写的是真好。但是你不能问,“这个刺客撞也撞死了,心里的话是跟谁说的?” 这都是我们满脑子有规矩的人在较劲。在左丘明、司马迁的眼里,人世间的事,理所必至,情所必然,就这么一路写下来了,根本没斟酌这地方我应不应该虚构。千百年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骨子里深信不疑的也常常就是这些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先秦,回到写作大自由的状态。
“世界就在那里
但我们认识世界却需要艰苦的过程”
晶报:所以您在写作的时候,会打通历史和现实,这是否就是您一直向往的、回归传统的“元写作”?
李敬泽:我讲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什么?说明无论是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或者是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现象,其实在它的底部都存在着非常复杂、非常广远的,我们看不到、但实际上存在的种种的联系。这些联系历史不会写,它常常是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联系变得非常重要。而且这些联系也非常好玩儿,值得书写。
晶报:这本《青鸟故事集》里讲的是此地与遥远异域往来的故事。宋朝浮海而来的龙涎香,元大都中进入西方人梦想的银树、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等等,在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就连“青鸟”在典故中也有异域往来之使者的含义。您是希望通过文学来表达对现代社会全球化的一种思考吗?
李敬泽:现代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但是现代文明发展得如此之快,这二百年来人类取得的经济成就、技术成就,包括人类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均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个焦虑的文明。文明要发展,一定要让大家焦虑起来。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焦虑之中。这个焦虑要靠什么来保持?靠时间,靠表。早上闹钟一响,到点儿得上班,这就是一个现代焦虑,古代农民哪需要闹钟上班呀,一觉醒来就扛着锄头下地。所以,整个现代文明机制基本上是建立在焦虑之上。
我们想一想,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庞杂的历史故事,我们都是历史回声的产物。比如我们的焦虑,我们被时间管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写利玛窦的钟这篇时发现,如果说要有什么确切日子的话,1601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就在这一年,利玛窦,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的志向就是要到北京,传教给皇帝,把皇帝变成天主教徒,他不知道自己的志向是多么荒谬,但是他很坚定。从澳门一路走到了北京,用了快十年,他送给皇帝一张世界地图和自鸣钟。从此,中国人开始了现代的地理观念和时间概念。
由此我们知道,远方能够进入我们的头脑,得到一个相应的、确切的位置,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谈起世界的时候要用“发现”这个词,是因为世界摆在那里,但世界要真正进我们的意识、进入我们的头脑,还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如何认识远方
是文明和生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晶报:其实您写到的“远方”,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方”和“异域”,更是文学上的“远方”。
李敬泽:在上世纪80年代搞文学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有个口号,叫做“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当然听上去也有点儿荒诞,咱们就在世界上呀,我们哪用得着走向世界呢?但实际上,说荒诞也不荒诞,因为咱都明白,这个口号意味着在当时我们是落后的,需要努力向世界学习。但是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呢?肯定不意味着柬埔寨、刚果、叙利亚。我们脑子里的世界是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是我们当时认为体现着文明和生产力先进的那些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讲起世界文学时,肯定都是在讲这些大国的文学,我们不会想到尼日利亚的什么作家。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脑子里的世界图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身在大时代,但是自己感觉不到。世界不仅仅再是那个由西方、欧美、日本构成的世界,还有了南亚、中亚、阿拉伯地区以及非洲等等。这是因为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秩序很重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晶报:认识到这些对我们的写作和生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李敬泽:清楚了这些,就知道了几乎所有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规则、基本要素并非天经地义,它是一个历史产物。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人们的选择、创造和各种机缘凑巧的结果。
当我们面对现在的时候,也要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面向着更远的未来,而我们也依然有选择创造的权利、自由和可能性。这其实也是我在写这本《青鸟故事集》时让自己觉得有趣的、有意思的地方。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人不仅一直要面对地理上的远方,也会一直面对文化上的、经验上的、陌生的那些“远方”,也会面对他人、别人、陌生人。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又将如何把这一切化为自己内部的远方?我觉得这始终是文明和生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个人如果心如止水还搞什么创作呢?”
晶报:您写过很多作品,但似乎《青鸟故事集》是您尤为看重的,这是您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吗?您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李敬泽:当我作为评论家的时候,诸如“这是你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吗?”也是经常会向别的作家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每次有人问的时候,你一定说这本书就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这个话可以说永远是敞口的,因为我的下一部肯定是更满意的。至于这本书里最为精彩的部分,我认为是前半部分。
晶报: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现在的文化空间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更复杂更宽阔,有更多利益的诱惑,如何在躁动的社会中保持内心文学创作的安静?
李敬泽:一个人如果心如止水还搞什么创作呢?一定是心里有很多东西在矛盾、在翻腾,你觉得有很多东西要表达,所以才会写出来。不仅是文学,其他任何一行,在这个时代都是这样。当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安静,所谓的安静,还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我们家的书房永远是不需要小时工打扫的,因为我每天进书房之前要把地和桌子都擦一遍,把乱的整理好,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地坐在那里摆开架势。但有时候很可笑,因为我这样折腾一阵,最后摆开架子在那里坐了半小时后,却写不出什么(笑)。
这种安静是物理意义上的安静。我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专注。我想不仅是文学,也不仅是这个时代,大家都得面对种种诱惑,面对着人间烟火,所以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就需要专注。所谓专注,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全部的精力,集中全部的思想,于你眼前要做的这个事情之上。这不仅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来说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晶报:您现在有构思新的作品吗?
李敬泽:现在我计划的,是比《青鸟故事集》更满意的、大概8月份要出的一本新书,书名用的是孔子《论语》里的一句话。孔子问弟子们“你们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其中一个回答,“春天了,我们到雨水边去洗澡”——“风乎舞雩,咏而归”,所以这本书取名《咏而归》,是随笔性的,写得很随便,是阅读种种经典时候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感想,算是本有趣的书。
但我现在真正焦虑、拼命的是另一本题目没定的书,可能叫《春秋传》,我要写春秋时代那些“巨人”,我觉得春秋时代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时代,但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不熟的时代,历史剧一演就是唐宋元明清,让大家耳熟能详,但一说春秋可能都是脑子里一团乱,那个时候光国家就不知道多少个。
晶报:为什么会认为春秋时代是最了不起的时代呢?
李敬泽:首先是春秋时代很重要。德国哲学家讲过人类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各个伟大的民族出现了他们精神上的伟大导师。而伟大精神开创者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五六百年前的这个时段,在中国就是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产生了老子、孔子,他们的著述和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且春秋时代的人也有意思,比现在的人好玩多了,精神上、身体上都非常强健,脾气很大,爱憎分明,性如烈火,按西方人来说就相当于西方的希腊时代、荷马时代。现在写来写去,我发现这书得是一个大规模的东西,现在计划是写三卷,第一卷应该是明年初出版,我坚信,明年初出的这一卷会是我最满意的那一本(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