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vs中国女作家张悦然
缺乏阅读会带来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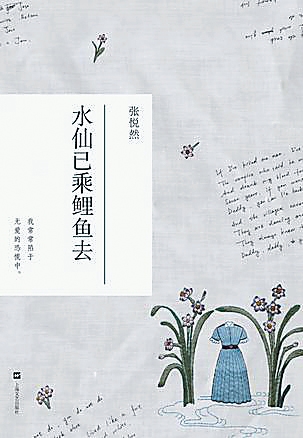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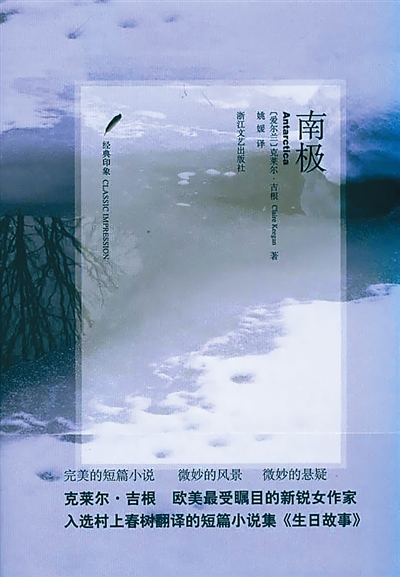



以精致动人的短篇小说见长的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日前出席澳门文学节,与作家张悦然进行了一场有关“小说中的沉默、孤独与爱”的对谈。
嘉宾:
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
爱尔兰当代最受瞩目的新锐女作家,跟博尔赫斯和雷蒙德·卡佛一样,她以精致动人的短篇小说见长。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她的成名作《南极》,获得了爱尔兰隆尼文学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大奖。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田野上》则获得了英国重要的短篇小说文学奖,边山短篇小说奖。2009年,吉根凭借发表在《纽约客》杂志的短篇小说《寄养》,荣获由《爱尔兰时报》颁发的Davy Bynes文学奖。
张悦然
14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小说作品有《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红鞋》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等多国文字。她也是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唯一的华语作家。她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茧》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巨大的关注,被称为80后一代作家直面历史和记忆的转型之作。
问题1:你们为什么开始写小说?
克莱尔·吉根:其实我也不知道小说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讲述给别人,作为一种分享。但事实上,我不知道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何处,灵感是说不明白的。记得还在爱尔兰乡下的时候,吃过晚餐去屋外抽烟,我总会在篱笆周围看到有一只猫,在黑暗中,它缓缓地移动着,它其实就像我写的故事一样。当一些事物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种发生,要去聆听,去关注。当人们说到写作灵感的时候,我还是对这个叫灵感的东西表示怀疑。我并不是一个天赋与灵感的信徒,所以我一直都在一个追寻的过程中,也在文学阅读和创作中成长。任何一部好的小说都是从生活,从阅读,从世界中不断提炼出来的。
张悦然:我是克莱尔非常忠实的读者,这使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有一个特别好的基础。我们交流的时候,都提到一个中国在美国生活的女作家李翊云,李翊云说,她会用小说去和那些她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对话。比如她喜欢威廉·特雷弗,喜欢他的《三人行》,于是写了《金童玉女》。《三人行》是个相当神秘和黑暗的小说,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以及一个爱慕他女儿的年轻男人之间的故事。三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因为种种原因(我认为剧透那个精彩的小说里包藏的秘密是不道德的),老人的存在,成为两个年轻人交往得以维系的前提,如果有一天老人死去,这对男女将无法面对彼此。在《金童玉女》里,李翊云也写了一组三角形的关系:一个老年女人和她的儿子,以及一个闯入他们生活的女孩。但是背景是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的性格和困境也不同,小说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气息和质地。如果不是她自己提及,没有人会在读《金童玉女》的时候想到《三人行》。但是如果知道了再去读,就会觉得《金童玉女》和《三人行》犹如镜像一般存在,很有趣。
吉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姐妹》。写一对出生于爱尔兰乡下的姐妹,妹妹嫁到城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姐姐则留下照顾年迈的父母,耽误了婚事,多年来孑然一身,父母死后,她继承了田地。妹妹每年夏天带着孩子回来,在姐姐这里住一段。但是这一年不一样。她来了就一直赖在这里,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姐姐忍耐着,每天伺候她和她的孩子,直到最后一刻,姐姐爆发了,她揭穿了真相。没有缎子窗帘,没有洗碗机,一切都是捏造的,妹妹已经被丈夫抛弃了,她回来是想侵占姐姐的土地。但是姐姐告诉她,这里的一切是我用三十年的时光换得的,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它夺走。故事的最后,姐姐站在镜子前面为妹妹梳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妹妹有一头姐姐一直羡慕的金色长发,忽然姐姐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掉了妹妹的头发。妹妹惊恐地尖叫起来。小说结束于此。女孩之间,因为妒忌而剪发的情节,并非吉根原创,菲茨杰拉德写过一篇《伯妮斯剪发》,好看女孩的头发也这样被恶狠狠地剪掉了。《姐妹》是不是在与《伯妮斯剪发》对话?不得而知。但这丝毫不妨碍《姐妹》成为一篇出色的小说。我喜欢那个孤独、隐忍和倔强的姐姐,她捍卫着她手里仅有的一点东西,那是她存在于世的凭借。
《姐妹》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南极》里,我大概是在2011年读到的。写《大乔小乔》的时候,我早已把《姐妹》忘得一干二净。我唯一记得是剪发的细节,那是读了菲茨杰拉德之后,产生的重叠印象。《大乔小乔》是我从一个研究计划生育的学者那里听来的故事:一对姐妹,合法出生的姐姐终于不堪家庭压力,在多年后自杀,不合法的妹妹却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健康地活着。后来,我发现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妹妹。按照时间来说,她应该已经大学毕业,步入了社会。我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否走到了阳光底下。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一直活在阴影底下,那只是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里,她有在都市生活里渐渐强壮起来的身体和意志,也有不断妥协和失去的自我。她和城市生活搏斗,失去很多,流了不少血,但是她得活下去,因为她是她,她也是她全家。
如果说吉根的《姐妹》写的是姐姐的心事,那么《大乔小乔》写的是妹妹的心事。但是发生在爱尔兰乡间的故事,和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不会一样。我没有姐妹,我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我们的童年里,有姐姐妹妹是不对的事。就好像马蹄莲茎上开了两朵花,没人会觉得好看,只会觉得畸形。小说中,妹妹的内心有一场善恶的角力。说成是善恶也许有点粗暴,确切地说,是顾念亲情还是保护自己。童年里的资源匮乏,导致她格外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自己赢得的那一点东西。但她最终发现,自己也许并没有真正赢得什么,她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无法把握。
回头去看,《大乔小乔》也和《姐妹》构成了某种镜像的关系。一如《姐妹》里妹妹的回归,扰乱了姐姐的生活,在《大乔小乔》里,姐姐的出现,打破了妹妹维系的平静,构成了某种威胁。而且非常诡异的是,这个小说里的姐姐也有一头美丽而傲慢的长头发,在夏天的夜晚飘啊飘,散出香波的气味。谢天谢地,妹妹最后没有去剪姐姐的头发。因为她不需要这么做了。残酷的现实就会铰去姐姐的长发,根本不用妹妹去做什么。她只要看着就好了。然而看着姐姐消失,就是与隐形的凶手合谋吧?这是中国和爱尔兰的不同,和女性处境的卑微相比,这里有更大的卑微存在。关于阶级,关于律法所决定的被诅咒的生命。
克莱尔·吉根:是的,也许关于姐妹之间的挣扎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在这种相似中又是不同的。她们在一个家庭中面临着自己所处地位的困难,自己所属空间,以及去赢得家人的关注等问题。这种处境就影响了她们的个性,这种处境也让我思考了很久,即使在文学中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问题2:如何理解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怎样选择或者提炼素材?
张悦然:我很赞同爱丽丝·门罗的一句话,使人们产生灵感的不是说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发生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一步步演变成最终结果的方式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偏执,比如对悲剧或者对某一种绝望的处境的热爱,会使小说走向一种结局,但是我依然有兴趣去观看我的主人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这种结局的。有时候小说像是一种装置,我们的主人公走进去,他在里面迎接一些事情或者躲闪一些事情,最后他是否走出来,还是就在这个装置里面被消灭,或者仍旧在作战,这个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勇气或犹豫,这是我关心的事情。而且我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时刻,我愿意把它称为是一个“顿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面他会觉得他眼前的事情全都不一样了,他会觉得他过往的经历碎成了一块一块的小块儿,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他才真正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因为他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克莱尔·吉根:是的,好像写作中有一部分是在等待到来的。如果你想要写出好的小说,你就要等待这一刻的出现。其实你知道你可以强迫它出现,但如果你过于用力,你就得不到你想要写的那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你的故事或许就会沦于庸俗之中。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尝试去找到一种清新的语言去描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意义。一部好的小说,其实是我们感情的一部分,是有关转瞬即逝的情感,是感动人心的。我觉得不好的小说只有单调的陈述,它只是一种死板的描述,而没有一种立体的角度,而一篇好的作品不该受它束缚。在写作中,我觉得总需要有一个明显的声音,甚至它或许是一个男性的,充满权威的声音。
至于怎么平衡小细节与小说的整体结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那样试着去写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品位,我真的很相信它。因为我觉得我生命中大量的时间都在读很多的作品,我可以辨别好的与不好的作品。这也是我可以自信的做一个老师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好的段落与不好的段落的差别,我可以从各个方面把它们展示给你。法国诗人瓦雷里说过,正是艺术形式的限制性才让你激动。我很喜欢这个观点,我尝试去突破形式上的束缚,即使受到阻碍之后,我也愿意再次回归到这种束缚之中。你需要努力找到自己可以停留可以栖息的艺术形式。
问题3: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阅读或者写作经验和习惯吗?
克莱尔·吉根:其实我写作需要重写很多次,写出来再改三十次或者更多。我也不是每天都必须要写作。如果你是作家的话,不写作比写作还叫你难受,即使写作如此之艰辛。我很久不写东西的话,就会感觉不太舒服。我教创意写作课程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对很多来上课的人说,我真是太爱写作了,我每天都不停地在写,一直在写。但要创作的话,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心底,理解和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到底在写些什么,你必须要意识到和感受到你的灵魂,你生存的环境等等。所以我并不会无时无刻一直都在写作。
张悦然:我写长篇小说,所以我很难去改三十遍,三十遍对我来说太残忍了。我常常羡慕一些中国的男作家,他们总会说他们是重写。就是忽然之间,写了十万字,有一天晚上看了一眼,然后说,垃圾,扔掉,明天早上再重写。我做的工作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我最后发现这种修修补补比重写还要累。
问题4:在你们的小说里都提到了宿命,如何理解宿命?
张悦然:我觉得很早的时候在我的小说里,有很重的宿命意味,就是因为我相信事情有一个因果的逻辑,我相信中国的,也相信西方的,试图去从中找到一种规律。后来我发现这种规律给予我的是一种安全感,就像是我掌握了世间的一种秘密一样,这种秘密让我觉得我会知道下一步事情走向哪一步,就像是摸到了命运的轮廓,这会让我觉得很安全。所以在我最早的小说里面,人都是符合各种宿命的规律的,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改变。在最近的小说里面,我好像在对抗着宿命这种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相信宿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知道事物的某种规律,然后按照它去做选择。但是世界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事情是无序的,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是没有办法把握对不对的,而且往往是你越想把握住规律,到最后你越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克莱尔·吉根: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一些宿命的,它是自相矛盾的一种观念。我觉得这也是它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变得更加有趣,一些相同性质的事情或许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我认为它是没有规律的。我相信宿命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词语为它而生,一切有词语可以描绘的东西,我就会相信它是存在的。有人在一次采访中问过我,你相信上帝吗?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你信上帝吗?如果你相信上帝,我是尊重你的,你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我也相信。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无法避免的一切更加感兴趣,对我来说宿命对主人公的塑造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我相信一切的可能性。我喜欢很多有趣的作家的作品都不是非常戏剧化或者极跳跃的,他们非常安静,非常平和,所以我很喜欢契诃夫,他的作品就很平易近人。人物,故事都在一片平静中精彩地进行着。
问题5:如何在作家和教师角色之间转换?
张悦然:我平衡得不大好,我就是很难适应学院规则的那种作家。其实我之所以愿意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就是因为这种紧张的感觉。我在大学里呆着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这种不舒服是一种活力。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就是我生活得太安逸,所以有时候我会给自己找一些麻烦,就想去教书。很多时候我的课是面对本科生,是教他们如何阅读,如何欣赏好的作品,对于这些并不是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将来他们忙碌的生活中也许会放弃阅读小说,他们可能会阅读很多文学之外的东西,我希望我可以让文学和小说在他们的生命中停留得久一些。
克莱尔·吉根: 我非常喜欢教学,但并不是一直都忙于教书。如果是一个好老师的话,你就会很慷慨无私地教育学生,去分享知识给他们。我遇到很多对我影响颇深的优秀的老师,我想我会一直都教书的,我热爱文学,我热爱与其他人分享。我不会在大学做全职教员,因为我能力有限,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我和很多学校有过不同的合作,也举办过很多学习工作坊,我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其他人展示文学以及小说的魅力。我认为现在不幸的一点是,很多在大学任教的人,是那些最无聊的人。他们已经被体制化,他们很懒惰,永远在反反复复教同一门课,却享受着丰厚的佣金。他们是那么无聊和懦弱,真的,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都在大学里。他们不颂扬文学,他们也没有鼓励学生去广泛地阅读各类的文学作品和去在阅读中打开眼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觉得很遗憾,大学里的英文系是所有想象力的核心,是想象力的摇篮。我相信阅读文学的力量,相信缺乏阅读会带来消极后果和灾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