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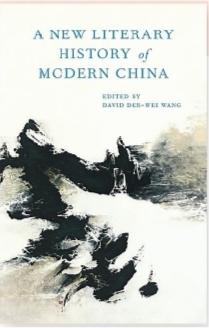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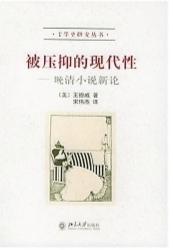


时间:2017年6月8日
地点:人民大学
嘉宾:王德威
参加人员:阎连科、梁鸿、张悦然、蒋方舟、张楚等
6月7日,著名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获颁首届“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该奖项由腾讯文化、京东图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以全球为华语文学写作、研究和推介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学者与翻译家为致敬对象。5位著名作家、批评家和学者担任初审评委,21位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班的青年作家担任终审。8日,王德威教授做客“一勺池文学课”,与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作家们交流。
问:您的很多著作里对民国时期那些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写作手法的作家都特别的关注。比如中国传统手法中的抒情、戏谑、闹剧、世情小说等等,张爱玲、老舍、沈从文等等,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是每一篇作品都那么出色,但是这些继承的地方您都特别关注。我的困惑是,如果我们现在仍旧沿着他们的路线去创作的话,是否还有意义和空间能够向前突破?因为他们继承的地方,总让人感觉到与当下的写作有一定隔阂和矛盾,他们都不是特别在意经营一些欧美范儿的故事。
王德威:那个世代的作家写作就是那个范儿,我们很多人想要做“现代的张爱玲”,现在少了,十年以前有很多。有一年台湾有一个比赛叫“谁最像张爱玲”,这是很可怕的比赛。还有男性作者,希望写出最张爱玲式的小说。何必要重复呢?我认为文学是有无限可能性的文字游戏。老舍的独特性存在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说不定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写作风格,老舍那代想都没想到的。也许不需要太过分焦虑,那个传统在那里,这里面还是有某种传承和对话的可能性,你不可能从石缝里蹦出来。前些年王安忆写《长恨歌》,这个小说太好看了,看了好几天,我要介绍。我用了一个标题,《海派作家又见传人》,我以为是奉承王安忆,没想到王安忆大怒。她就说了,我不了解为什么我是海派作家,她说她跟张爱玲完全不同,张爱玲这个人生走的边边角角,她是开大门走大路的。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即使王安忆有意识地区隔和海外的传统,她毕竟有一个对话的对象。
回到你的问题,你觉得我对传统有这么深的关注吗?以前也有人说我的评论充满了“情伤”,我没有刻意去经营一个所谓的“抒情”或“情伤”,因为我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写作,英语是我后来学出来的,我在抒情之前我得先顾我的文法好不好,我的英文我相信是写得四平八稳的,没有英文世界的同行说王德威你写得好“情伤”。我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在中国语境中很多年前我开始写评论文字或者做文学研究的时候,我想到两个点:第一,我们做现代文学的除了“五四”的传统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扩大影响,扩大我们传承的历史意识;第二,既然是我的母语,我就应该放肆一点,有一点个人风格。“抒情”传统其实是我自觉地和古典的对话。这个东西不只是柔软的、个人的、小资的、王菲式的抒情,这个抒情如果回到古典的传统,屈原是第一个讲抒情传统的人,屈原讲的抒情传统是发奋与抒情,发奋是指有一个很强烈的政治承担和历史抱负,但是抒情又在这个时候激发了我们所谓的中国第一个自觉的诗人或者文人的写作——《楚辞》的屈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个被革命和启蒙所主导的语境里面,来一点抒情未尝不可。
在这个意义上,我再一次回应,是的,我是有意在继承某些传统上的话语。我个人的训练是外文系,我们都在用西方的话语。到了这个点,我应该从我的立场,重新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论述的话语对我的影响。一个世纪的中国文论家,他们产生的丰富的文论的面相,不是我们今天讲巴赫金所能够涵盖的。到2017年,尤其是在我个人的位置,我可以向我在美国的同行和学生来说明,其实这一百年中国的文论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我在比较文学系的同事也能够说鲁迅曾经怎么讲,巴赫金怎么讲,那是比较文学。但目前我们是一边倒,我承认文学传统对我来讲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传统,它应该继续延续。
问:我很关心作家的作品对于社会的参与度,更确切地说是对公众事件参与度的问题。台湾的作家我最喜欢的是朱天心八九十年代的短篇《佛灭》,讲的是台湾公益界,应该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当时看了觉得社会性非常强,取材于现实的勇气也非常敬佩。相对而言,大陆作家对真实的公众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没有那么多。您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
王德威: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在美国的学生们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里,我用最简单的回答,语境跟台湾和香港毕竟是不一样的。大家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自觉和不自觉制约的心态。文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表达意义的有想象力的活动,它永远有公众的层面。为什么?语言本身从来就是一个公众的大家互相传递的符号,没有一个人可以喃喃自语地写作,就算喃喃自语写作的时候,你其实也有一个对象是对自己,那个自己已经变成他者,永远有“他”这样一个面向,才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巴赫金式的,有对话张力的论述和小说。
哪怕是没有真正公众影响力的作品,在他创作的过程中,那个作家自己也必须自觉到他的作品是在某种对话的层次上进行的。这个公共性跟社会性,一旦真正放入到实际生活的场域里面,就有很多有意思的艺术现象产生。台湾的作家,你讲的是作家自觉写作了一个公共的题材,付诸公共的表达,产生公共的效应,这里面就有取舍,跟社会直接的互动和取舍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成功的,有的时候不成功,你看到成功的例子,你可能没有看到作家写了半天,号召了半天,还是不成。作家如果是太想用第三个定义下的公共去写作,我怕失望是比较多的,你做记者算了。回到我第二个定义上,我觉得创作,基本上我知道是为一个目的,我为了我自己,这个公共性不应该和你在现实存在的公共性所期望的效果画等号,否则那个创作一定是有期望和实际的落差。
问:您谈到科幻小说,在晚清时候科幻也有一批作品。您也谈到刘慈欣,您觉得这几年我们中国科幻作品频繁走出国门,这种兴盛对社会有什么意味?在这种类型文学里面,现在的作家能够学习一些什么?
王德威:我在很多年前,在8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对晚清小说有兴趣,我看了无数非常糟糕的小说。科幻是晚清小说文类非常特殊的一个发展,晚清小说大宗是狭邪小说,还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是到了1900之后,十年之间突然冒起来的文类,一下子引起了很大的读者关注和作家写作的热潮。那个科幻小说尽管非常有魅力,但是它的文字基本是不够好的。它的张力,对中国现实处理的张力,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时空,引人入胜。
晚清的科幻十年是异军突起的现象,到21世纪又一个科幻热潮出现,科幻小说很奇怪,在过去是儿童文学,不登大雅之堂。我的学生跟我推荐《三体》,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奇怪,我必须说,它的文字是不够好的,有必要写成三本吗?但是你又觉得它处理的人类文明三体人要来,完全不是王安忆可以处理的,完全不是阎连科可以处理的,在那个意义上,它让我吃了一惊。其实到今天我都觉得,整个十年的科幻作品在文学品质上是有限的,它的创作基本所依赖的是横空出世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非常无羁的,科幻的兴起和新媒介的兴起是有关的。我在不同的场合把20世纪初的十年和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科幻放在一起做类比。
在这个意义上,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推荐刘慈欣,2011年那次我来人大,讲了一个题目《从鲁迅到刘慈欣》,有学生举手说这样合适吗?我觉得刘慈欣当然不是鲁迅,不能相提并论,我要想讲的是,刘慈欣给我的教育是,原来文学有很多种。原来我们在学院里面,正规里面教的文学是这样、那样,但是科幻作为一个文类有就有了,你作为一个文学的专业读者或者观察者,必须正视这个现象。我从那个意义上,觉得刘慈欣所代表的现象还有他内在的爆发力,他对整个历史以外的现象的重新思考,间接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这是他们一群作家共同的贡献,不是刘慈欣一个人的贡献,包括了韩松等等。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恐怕科幻热潮高潮已经过去了,这个高潮一方面当然是作家的爆发力到了一个点,必须要稍微平息一下,社会的反应这么剧烈他们大概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另外一个方面,过于关注大概会起一些反面的作用。《北京折叠》虽然得了雨果奖,你们觉得写得好吗?太奇怪了。科幻小说让我感动的是,在我们熟悉的制式和套路里面,科幻小说家是一群另类,但他们能撑多久是另外一回事,毕竟他们没有一个文学的内在的自觉的机制来支撑它,当然网络现在是一个新的机制,希望它能继续成长。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些作者里面,它的风格也就这样了,他们的语言基本是相当粗糙的。昨天有人问我,幸好我们有一个刘宇昆他喜欢刘慈欣的作品,他翻译了《三体》,不只是翻译,而且进行了编辑,变成一个特别好看的英文版的《三体》,好看到奥巴马总统把它作为圣诞节阅读的十本著作之一。那是美国的刘慈欣了,不是原来的刘慈欣了。这里面有很多这样有趣的曲折。
问:问一个语言的问题,中国的写作者经常谈到中式、欧式,会有很多争论。欧式更多是指翻译体,中式可能指的是语言文学本身比较简练,感性的成分多,欧式相反。在我看来,我觉得语言更多是思维的体现,语言的争论您怎么看?
王德威:欧式和中式我会有保留,你讲的翻译体的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是1920年代的问题,茅盾、鲁迅都牵扯到“翻译体”的问题。欧式不欧式仍然是作家自觉的选择,如果作家在写作里面有不同的风格,应该是容纳最多可能性的语言的场域,不像目前讲话我们得中规中矩,作家在那个意义上真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暴君,他必须要很强势来说明语言风格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真切的问题。
先用台湾的例子讲,王安忆不止一次说,台湾的作家写作是用书面语的方式写作,中国大陆的作家写作好像比较流畅,比较直接。海峡两岸已经有将近70年的隔离历史,语言本身还是回到华语语系的问题,台湾作家朱天文写的东西就很奇怪,文绉绉的,胡兰成加上张爱玲。骆以军就莫名其妙,写的很浓重的诗的东西,你仔细看精彩得不得了,谁有那个体力看40万字的小说是那样的一种东西,很难慢慢消化。
你说那是欧式还是中式?我不觉得是中西之分,作家在各种语言的晦涩和直白之间的一个选择,其实是有各种可能性的。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作品。这里面完全用大字报体,从来没有一个作品会让我想象“文革”这么样的惊心动魄,张口就是大字报式的,这个运用之妙是作家本身的操作。
问:王老师,读了《想象中国的方法》,你这本书的开端用了狭邪小说介绍晚清,包括科幻小说、公案小说、闹剧小说。20年前您对整个中国小说的未来做出了预言。今天您看这20年,这个版图会修订吗?
王德威:我讨论的四个文类狭邪、科幻、公案、闹剧,我当时不只是写小说的四个文类,野心稍微再大一点,是探讨四个文类所投射的四种论述方式,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大的范式。所以我认为,狭邪小说在晚清释放了我们对于情欲的想象性,公案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20世纪我们不断在问的话题。至于官场现形和谴责小说我认为整个对价值体系有一个预设式的写作模式。科幻则对什么是真理、对未来20世纪有一个预设性的呈现。
这四个论述的方向我就问了20世纪最后的几年,我们是不是仍然看到类似的方向的延续?我得自圆其说,当然有。我后来写了很多关于科幻的东西,我觉得让我最心有戚戚焉的反而是谴责小说。我不晓得为什么1990年20世纪最后的10年还有这个世纪前面十几年,作家其实不约而同都在写作这个世道里面各种奇怪的现象,阎老师写的《受活》,余华的《兄弟》,甚至包括莫言的小说,他所要揭露的社会价值颠倒现象等等,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一个世纪以前都已经问了,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但问而且问得更细腻,更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答案。这时候我们对于小说的怀抱是什么,梁启超曾经告诉我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充满了正能量的1902年的宣言。
现在我们看《受活》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看《生死疲劳》不知道有没有正能量,我不是说小说刻意暴露现实阴暗面而已,那个野心太小了,小说这个东西现在变成我们这个世代最重要的话语,在我们这个世代当历史学者、政论学者、思想史界的学者,没有办法能够完整地呈现现实社会的林林总总的怪现象,小说家现在所负担的角色,比在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作者或者是批评家都更来得重要。我在猜想,我最后一个预言,再过30年以后,我们回过来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还有思想史上各种论辩,所有的问题、症结还有可能的答案都出现在小说里,原因大家心里明白,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我们不只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好好讲故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艺,生存法则。我们活过这个世代,有一天我看待现在的小说不会只像美国学者或者美国的批评者把小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是社会论述的一部分,但这个社会论述的公共意义和公共性不见得是在一时一地立刻呈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汇总起来的大的能量,是我对于现在小说家的期许,我也很愿意在今天说,这是我的一个预言。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