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都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这句话却不适合陈河。
二十多年前,生性爱闯荡的陈河在海外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为此,他经历了白手起家、遭遇绑架,还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热爱的写作事业。但写作的美妙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正如陈河在《为何写作》中说道的:“十几年前,当我放弃了写作出国经商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放弃才成全了我日后做职业写作者的梦想。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给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我的生活外延大大扩展。我源源不断地写出了作品,有了自己的粮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
确实,回归写作的陈河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先是短篇小说《夜巡》获得了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10年,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得了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主体最佳作品奖……今年11月,陈河更是携新作《甲骨时光》摘得华侨华人 “中山文学大奖”。步履稳健的陈河,以男性的大手笔凿开历史潜藏的暗道,在东西方的跨界时空下,为读者带来千奇百怪的人物故事。
正如诸多当代海外作家一样,生命的重新嫁接让陈河蓦然焕发出饱满异样的光彩。远离故乡所带来的审美的距离,使他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局外人”的特殊身份更是使他早已超越了惯常的“家国意识”。海外华文文学近30年来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在陈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写作就像求生,是一种本能

(作家陈河 图片源于网络)
搜狐文化:你生于温州,1994年去了阿尔巴尼亚,后来又移民到了加拿大,你曾经说之所以选择出国,是觉得在温州待下去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那经过这几年的辗转和沉淀之后,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陈河:是的,我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了,还是蛮早的,当年也写了蛮多不错的东西,但一方面当时在温州这个小地方是业余写作,写来写去的影响也只是在浙江省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我除了写作以外,总是想改变一些什么,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那时候在温州的单位工作就是平平淡淡的,后来有一个和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生意的机会,就出去了。其实我到海外以后,中断了十几年的写作,2005年的时候才重新开始写,那个时候我在国外已经十多年了,经济条件基本上也能满足自己的生活,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业余爱好的事情了,那时候就想继续写作了,实际上也不是突然想写,写作这件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又被唤醒了,再次开始写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写作的感觉比以前要好很多,一方面是自己这十多年的国外经历,碰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另一方面离开中国以后,跟家乡有在空间上有了一个距离,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经历的那些事情,心里反而更加清楚,写出来的东西和以前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说我认为出国对我的写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搜狐文化:也就是说您虽然停笔十年,但想写作的念头始终都没有放弃过。
陈河:是的,我们温州人出国的很多,我跟我太太在出国以前都是在国有企业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吃穿不愁。但到了国外就不一样了,假如自己不好好做,生意做不成功的话,养家糊口都很难,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我就非常认真的做药品生意,而且做得也蛮好的,后来1998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被一些人绑架了,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上,手脚都捆在一起,关在一个地下的防空洞里就走开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但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能从胶布的缝隙里感觉到有一点点光,也能感觉到有空气进来,然后又听到外面有小鸟的叫声,我就知道自己被关的位置肯定离地面不远,我突然就想,假如我最后没被他们撕票的话,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后来运气也算比较好,关了7天之后被警察救了出来。后来我就想,自己在马上就要死掉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想到文学的事情,我就知道写作在我心里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被解救出来以后我就移民到加拿大了,又是从头开始,辛苦了好多年,直到2005年才正式开始写作,慢慢地把原来做的生意收缩直到停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写作上面。当然我也通过十几年的经商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财务问题都解决和安排好了,我可以不靠写作吃饭,用一种比较专业的职业的方式去从事写作。
搜狐文化:对你来说写作就像求生一样,都是一种本能。
陈河:你说的很对,因为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住,但对写作却特别有耐心,坐在那边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也不会烦,写作永远不会让我感到烦恼。
搜狐文化:那你写作的习惯是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写,还是有灵感的时候一气呵成去写呢?
陈河:我觉得写作就像一场长跑,需要慢慢积累。我现在的状态是,不管有没有灵感,一定会用每天早上的那段时间去写作,然后中午就可以休息一下,下午会看一些书,偶尔也会写一点,但通常是去游泳散步,做一些体育方面的锻炼。晚上通常情就不写作了,一般会看看球,这一天还蛮清闲的。在海外有一个好处,就是应酬比较少,在国内像我们这样比较成熟的作家,大多会有很多的活动,但在国外大家没有这个习惯,生活比较安静,也没有什么大的干扰。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会拿出多一点的时间去写作,但通常都是慢慢进行的,写的太快反而会影响质量,所以我每天也就写那么一两千字,加上修改可能也就几百个字,但一天写一千个字,一年到头就有36万字了,所以不用追求很快的速度,每天写一点,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潜心五年,认真打磨《甲骨时光》
搜狐文化:你的作品经常会涉及到二战,对于普及这段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国内还拍了很多抗日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往往有很多虚假和编造的成分,这些影视剧对于正视二战这段历史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陈河:这个肯定是有的,我至今为止写过两本关于二战时期马来西亚华人抗日故事的书,一本是《沙捞越战事》另一本是《米罗山营地》,虽然第一本是个虚构的小说,但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兵讲述他一九四几年被英国军队招募,空降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里跟日本人作战的事情,那个老人的这一两句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很好奇华人怎么会参加到抗日战争里去,后来通过查资料发现当时在加拿大确实有一批华裔的年轻人被英国军队招募到特种部队,经过训练后被送到马来西亚丛林里去,因为当时在那里有一个华人的游击队,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有抗日战争,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抗日战争的战场,这个战场的主要力量还是我们华人华侨组织起来的,所以我就很想用真实的材料和虚构的方法写成一本小说,这个书出来之后在国内反映还是蛮好的,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一方面有真实的史实,另一方面还有人性的光辉,有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我并没有像那些抗日神剧一样,把战争写成一种单一化的东西,日本人就是坏人中国人就是好人,现在很多影视公司也想把这本《沙捞越战事》改编成电影,而且也已经有人在做这个事情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海外华人,还是有一定责任的,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因为虽然现在中国大陆研究抗日战争的人很多,但海外战场这块确实没人搞,我这两本书至少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原来在中国本土之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人抗日战争的这么一个战场,也算是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搜狐文化: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您最近又新出了一本叫做《甲骨时光》的新书,我有些好奇您在创作这本小说之前对甲骨文有了解吗?
陈河:这个完全没有,我这次到北京参加世界华人大会,除了和大家交流以外,也是因为《甲骨时光》这本书获得了中山文学奖,这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也很特别的奖,可见这本书在国内受到了很大的好评。包括我之前在复旦大学开会,国内很多非常指名的教授对这本书评价也很好,然后一些大的报刊也都对这本书进行了报道。其实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对甲骨文一点了解都没有,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很多东西都会感到好奇。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一次去河南安阳玩,刚好看到了发现甲骨文的殷墟,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又看到一本李季写的书,叫《安阳》,这个人是民国政府时期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哈佛毕业的博士,他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参加了考古,后来又到台湾去,七几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详细地讲述了一九二几年的时候,挖掘殷墟的历史。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田野考古,以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其实是看不起田野考古这种体力劳动的,直到傅斯年和李季他们这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归国以后,才开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但那时的条件很不好,北伐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国知识分子还是在安阳干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考古成就,把甲骨文以及商朝的那段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挖出了很多珍贵的文物,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决定深入研究下去。我回到加拿大以后就买了很多甲骨文方面的专著,还在网上找到很多资料,越看越有意思,就觉得自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小说。但是我要讲的无非就是一个在安阳挖地考古的故事,要把这件事写成一个有意思的长篇小说,真的很不容易,我足足花了五年时间,才深入到甲骨文文化中去,我在书里还用时空穿梭的方式对三千年前商朝的那段历史进行了还原,反响也非常好。十月文艺出版社还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把书稿送到北京故宫做了个评审,故宫专门派了一个台湾级的甲骨文学者来做审读,后来发现我这本书除了个别年份有些问题,大的甲骨文知识方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我里面提到的甲骨文句子,都能找到对应的甲骨文原始古版进行印证,说明我的工作是扎实的,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考古的研究,我要让读者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具有娱乐性,除此之外还能够宣传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因为商朝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起点,前面的夏朝很多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但商朝是真正有甲骨文的,如果能对甲骨文做一个宣传,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宣传,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搜狐文化:但是甲骨文本身是很晦涩的,要把它变成特别有趣的线索,难度应该还是挺大的,那么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瓶颈期呢?如果遇到的话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陈河:写长篇小说,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吸引读者的框架,让各式各样的故事在里面展开,也让读者有兴趣把这本书读下去,所以我会采取很多策略,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采用西方畅销小说的结构,比如密码的形式,搭建一个架子来演绎它的故事。我在书里写到商朝的画,画里会有一些新的图标暗示甲骨宝库的位置,破译了这些密码就能够找到新图的地点,整个故事把破译密码作为推进故事的动力,然后一步步地带起来。除此之外书里还会有一些来中国考古的日本人,以及西方的传教士,还有中国的历史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这几方人马的相互转换也会形成一个故事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有一个民族任务般的行动,这个任务也可以活动起来了。当然这中间的困难还是非常多的,但每天解决一个小问题,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写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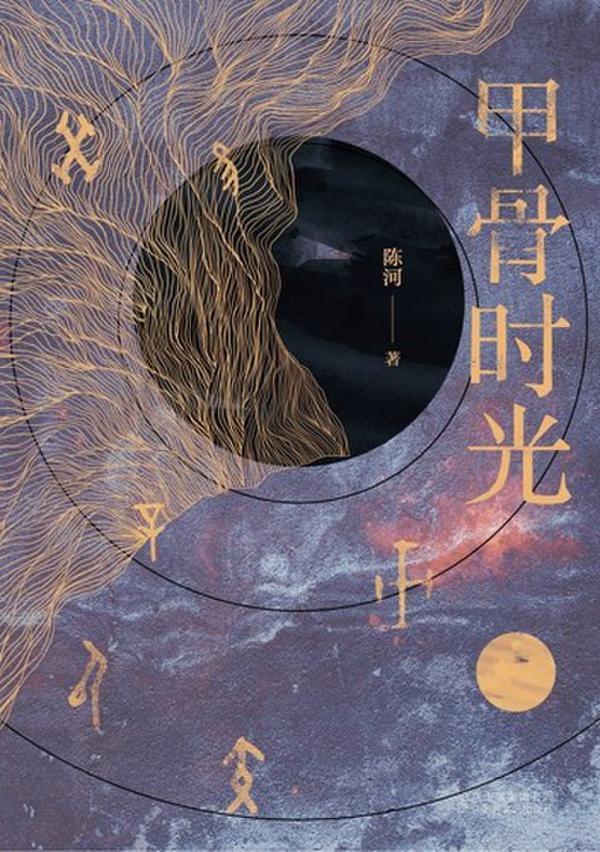
(陈河新作 《甲骨时光》)
纯文学小说与市场并不冲突
搜狐文化:我知道您之前一直是坚持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这次在书中加入“密码”这种有趣的细节,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向通俗文学方向转变的尝试呢?
陈河:我在这个书的后记里也提到,1981年我去长沙,那年才二十出头,有一天站在街头,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突然就有种很神秘的念头,我这辈子要写一本通俗小说,不管文学不文学,大家觉得好看就可以,但是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坚持纯文学的本性,甚至自己心里还有点看不起那种类型的小说,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自己在写作者方面也越来越有经验了以后,就发现通俗小说也有它的好处,西方很多很受欢迎的大师,比如卡尔维诺他们在小说里也会融入一些侦探小说这种通俗小说的技巧。我这本甲骨文的题材的小说,如果不用密码这些技巧,感觉好像很省力,但普通的读者不会感兴趣,另外这种技巧还能帮助你看清整个故事,我觉得它所产生的效果要比写纯文学小说好得多。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当我写到最困难的时候,和我太太去意大利旅游,在佛罗伦萨的一个王宫参观,突然导游对我们说要赶紧走,再过一个小时这个馆就不对外开放了,因为有一个新书发布会,刚好就是《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的那本《地狱》,我正在写一本向《达·芬奇密码》致敬的书,就碰到它的作者朗了,确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觉得很振奋,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所走的路子是对的,后来就摸索着把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解决了,当然第一稿写成以后还是觉得比较枯燥,后来又做了很多修改,补充了很多材料,到最后基本上已经达到我所设想的目标了,很多人看完以后也觉得确实挺好看的。
搜狐文化:所以在您看来,文学和市场之间其实还是可以共存的。
陈河:是这样,虽然我这本书加入了一些通俗的写法,但并不表明我今后会向通俗文学靠近,我从骨子里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一直坚持用非常纯正的方法去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不管写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小说,首先一定要好看,不要搞得很晦涩,让读者看不进去。我们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读者看你的书,不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看,这些都是投入,如果到头来人家发现很不好看,也没有什么愉快的享受,从一个作家的职业道德角度来说,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写作时时刻刻都会提醒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看得下去。当然一本书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很嗨,一个情节过后可以平静一下,但下一个情节还是要有它的精采,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好看的小说不一定就是通俗的小说,好的纯文学小说也应该是好看的。
搜狐文化: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书评人说,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运用两样东西,一种是还原的想象力,另一种是虚构的想象力,您的这本《甲骨时光》就既从细节上很好的把握了历史,又设置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您是如何把握虚实之间的这种尺度的呢?
陈河:这个问题其实和前面说的抗日剧有一点关联,现在中国的这些抗日题材电视剧之所以不好看,是因为他们太不尊重历史,甚至不尊重事物的基本规律,所以随时会产生这种烂的作品。如果要写历史,首先不能改变大的历史,要有一定的史实根据,要不然就变成戏说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做法了。但我目前所写的小说,都是力求把它做得真实,比方我写商朝的甲骨文,在年代、人物和大的历史事件方面,都要通过查阅资料找到历史出处。现在很多人说查什么资料,小说随便怎么写就可以了,但我觉得想出来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东西是不会好看的,就像做衣服,如果这个衣服的料子就不好,再怎么做都不会好看,历史本身就绝有一种美感,只有把历史材料搞得很仔细很准确,好好的钻研它,才能把它的比例展现出来;至于你刚刚说的虚构的想象力,也确实是要有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副画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具有想象力的情节,往往能把读者和观众带到一个非常神美妙的境界,能够让他们觉得非常享受,如果做到这一点,这个作品就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要把握好这两种想象力的尺度,首先是要尊重历史,然后是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
非虚构历史作品同样需要想象力
搜狐文化:你觉得运不运用想象力是不是历史小说和非虚构历史作品的主要区别呢?
陈河:这个倒不是,无论是写实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需要想象力,因为我们所说的非虚构还是一个文学作品,并不是法院的犯罪记录,或者还原调查,那种确实是不能用想象的,但那种东西也不能称为文学作品。同样的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想象力写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非虚构作品来说,想象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我记得卡波特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冷血》,里面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枪手把一个农场里面的人打死以后,放在了棺材里面,等到法医来检查尸体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已经被打烂、裹着丝巾的头时,感觉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在棺材里面发出一种光芒。这样的一个描写,就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种非虚构作品,一定需要想象力来把它变成一部文学作品,所以无论是在非虚构还是虚构里面,想象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搜狐文化:你刚才说用了五年的时间来写作和准备这本书,那么在查阅了这么多资料之后,你认为殷商时期的文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陈河:殷商的文明是非常独特的,虽然我们中国历史悠久,但如果你去过埃及或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话,就会发现中亚的文明更加悠久,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埃及出土的文物,包括木偶、小船之类的殉葬品,那些文物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但颜色还像新的一样,保存得非常好,埃及文明留下了这些非常具体的东西。但我们中国却没有,只有一些传说,直到商朝才留下了青铜器和甲骨文,而且那时候的文明已经非常发达了,我第一次去殷墟的时候看到博物馆里面有两节陶制的排水管,那个水管一头是喇叭状的,而且直径还蛮大的,跟我们现代的地下水管道一模一样,我觉得商朝人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娴熟了,除了玉器、兵器、青铜器,最有意思的还是甲骨文,虽说是一种象形字,但已经非常抽象化了,现在看起来都很漂亮。另外商朝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血腥,我至今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那么血腥,它的血腥程度跟玛雅文化差不多,那些墨西哥的原住民也非常嗜血,在殷商时期大量地使用活人祭祀,那时候的国家一年到头就做两件事,一个在戎,一个在祀,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祭祀,而且他们那时也没有宗教,他们信奉的是天神和祖先,而且他们的祖先祭祀的时候特别严谨,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祭祀方法和方式,包括酒祭,肉祭,舞祭,还有人祭,杀上百个人,非常的血腥。但不能否认的是商朝确实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的发源,中华民族早期的家庭观念和君臣观念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其实从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族群因素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正在减少
搜狐文化:最后我还想跟您探讨一下海外华文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似乎是海外华文文学经常会涉及的问题,在您的《沙捞越战事》当中华裔士兵周天华也经常会面临这种文化归属的问题,他所面临的这种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的问题,在您旅居国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碰到呢?
陈河:说实话我们在国外生活,就像一个南方人在北京工作的情况差不多,一个温州人在北京工作和在纽约工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科技通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那些人背井离乡的人,都要通过写信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那时候话费特别贵,所以打一次电话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我出去的时候已经可以随便打电话了,这种思乡的观念越来越少。而且像加拿大这种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外来的移民是很好的,一进来就能够享受跟自己国民一样的福利待遇,所以这种身份认同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生活,我们也可以在国外生活,族群因素的影响正在慢慢减少。但是不同地方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我前段时间去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化在那里一直面对被消灭的压力,当地华人几百年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传承下去,在那里的有钱人都会拿出来一部分钱办教育,所以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孩子始终能够接受华文教育,很多根本没来过中国的马来西亚华人,中国字写得特别好,说得也很好,甚至他们唱的卡拉OK都是华语歌,而且乐感非常好,唱得特别好听。他们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始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延续着华人族群的血脉,如果没有一代代的坚持,他们很快就会被同化掉,对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有不利的影响。但北美和东南亚不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各种文化都融合到了英语文化体系,但是各个民族会有自己的自由,有自己的意见和权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族群保存下来。像我们的下一代中文水平就要低很多,到了我的孙辈,他们能说中文就已经不错了,根本认不了几个字,通常都会把中文丢掉。总之不同的地理位置不一样,东南亚会很自觉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但北美相对就差一些,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比如最早到北美淘金修铁路的人的子女,都出生在国外,虽然他们现在用英语说话和写作,但是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观念还是有的。
搜狐文化:你刚刚也说,在国外生活多年,对于中国文化在地理和时间上都有一定的疏离,那么这种疏离有没有让你形成一个审视自己文化身份的独特视角呢?
陈河: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在国外生活以后,看待问题会有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比如这次在《甲骨时光》里,我也会写到来中国发掘文物的日本人和欧洲传教士,但我并没有把它们定义为简单的坏人,他们寻找甲骨文,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对考古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他们的国家在效力,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我都可以理解,所以在设置这些人物的时候,我没有脸谱化,而是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去看,会有一个大的胸怀,这样也有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

(作家陈河(右)与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合影 图片源于网络)
搜狐文化:那这种不同的视角,可不可以看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特性?除此之外你认为海外华文文学还有什么特性呢?
陈河:现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真的挺多的,这次来开会的就有三百多位华文作家。但是说实话,作家队伍虽然很庞大,但作家不像工匠,不可以从学校里培养出来,这些喜爱华文写作的海外作家,大多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创作,偶尔会在报纸上发一发文章,也有一部分会印书出版,但总体来说不像大陆有这么多的人口,在国内有体制的支持,作家还可以签约拿工资,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可以专职写作,写得好还可以获奖,而海外跟国内相比,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数,都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国外还是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作家,比如严歌苓,她在影视文学商业化方面非常成功,另外还有刚刚提到的视角方面,在想法方面可能会不太一样。以前海内外的差别可能还比较明显,在中国国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大家对国外的事物会非常好奇,如果一个人用文章把国外的生活写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好看,但现在国门打开了,每个人都可以出国,在巴黎、纽约的街头上全都是中国人,大家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看过了,于是所谓的海外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海外的这种观念,我就是一个写作者,不过是居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不会给自己戴上一个海外作家的帽子,其实写作是一个全球性的事情,我们用华语写作和别人用英语写作,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觉得未来的差别也会越来越小。
作家明星化是商业社会的正常现象
搜狐文化:那你是怎么看待国内文学圈的现状呢?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吗?
陈河:我现在跟国内的作家也比较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中国文学发展的不是特别好,但现在想想也不奇怪,文学作品本来就像沙里淘金,经过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沉淀不出来几部名著,所以中国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只能产生那么几部好小说也很正常,我后来发现国外的小说也没多好,包括那些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很多也是普普通通的,其实中国现在也有一些不错的小说,但读者不一定能读到,这中间需要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目前所走的路还是可以的。而且我在书店的文学区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买书看书,觉得特别感动。另外喜欢写作的人很多,他们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写了之后总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于是每个省也都有文学刊物,在国外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它完全是商业化的社会,卖杂志一定要赚钱,而中国是由政府来做文化的事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现在中国写小说的人日子也越过越好,如果一个人写得好,他在经济方面的待遇也不会差,虽然稿费挣得不多,但他在社会地位方面马上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也是那么多年轻人喜欢文学的原因。尽管现在商业气息越来越重,但中国人对于读书人和作家,在本能上还是会有一种尊重,我自己就有切身的感受。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追求文化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搜狐文化:很多小说家写了一些很受欢迎的小说,不但收入变多,地位提高,还出现了一种作家明星化的现象,导致他们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会有意识地过度迎合市场。
陈河:明星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也是这样,西方作家完全要靠自己养活自己,比如有一个写短篇小说很有名的卡佛,他一开始写小说非常苦,之所以写短篇小说也是因为他付不起房租,总是被人赶出来,所以要赶紧把小说完成换稿费,但出名之后他的收入就非常高了,我还看过一些大作家比如说海明威的故居,都非常豪华,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作家,一定是非常富有的,这是不奇怪的。现在的明星化有两种情况,一种作品本身具有消费性,比如畅销小说,虽然这些小说的文学质量不一定很高,但是没办法,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理性的,但人太理智也不一定是好玩的事情,很多人喜欢一个作家,他肯定有值得喜欢的地方,虽然我写到现在,大家对我作品的评价也比较好,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清的,这个也不奇怪,所以说不写书的人自己还是要有一点钱,但钱也不能太多,钱太多以写作的动力反而不足,我觉得一个作家处于红与不红、富与不富之间,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搜狐文化:通过跟你的聊天,还有之前看过你写的《红白黑》和《甲骨时光》等一系列作品,我发现你塑造的主人公永远是那种为了理想不断远行的人,总是闪烁着非常正能量的光芒,让人看到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这是不是你自身积极的人生观的反映?
陈河:前段时间有一个很喜欢我的小说的朋友,说了一句比较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因为天性上的善良和温柔,导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都没有绝对的坏人,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比如我写过一个加拿大的绑架案件,几个留学生把一个女孩子搞死了,还有两个富家子弟也把人打死了,我写成以后我发现,我对这些凶手都怀着一种宽容的心态,他们都不是坏人,只是因为缺少爱才在特殊的环境下采取一些特殊的举动,我总是会写一些按道理来说很坏的人,但最后都变不成坏人,我自己都搞不明白,后来那个人点出了其中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我所写的那些小人物都怀着昂扬的心态,追求一种比较光明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搜狐文化:最后能不能透露一下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陈河:在写作方面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说实话现在国内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除了贾平凹和王安忆这样特别勤快的人,剩下的基本上已经很少写作了,我刚刚也说了,自己的写作中断了十年,等到重新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是这十年时间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几乎每年一本,应该说是蛮高产的。按道理一个人能有这样的产量已经算不错了,但我现在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我目前在同时筹备好几本书,其中一个比较成熟的是想写红卫兵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这个故事我最早是在凤凰电视台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里看到的,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正好也是美国人发动越南战争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派出了32万中国军队秘密进入越南,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人,其中直接参加战斗的是高炮部队,在实力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还是打下了1400多架美国飞机,那场战争非常的残酷,中国死了1400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十几个革命热情非常高的红卫兵,他们自己偷渡出境来到越南河内,找到中国大使馆,和他们说自己想要到越南去参加战争,打击美帝国主义,中国大使馆在请示了中央政府以后,据说是总理同意他们跟着部队锻炼锻炼,只要在部队调转的时候,早点回来就行。这里面有一个叫赵建军小孩子,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赶上炮弹爆炸了,弹片直接打中他的脑袋,赵建军就死掉了。后来这十几个小孩有的死了,也有的活了下来,回到大陆国内。虽然这个片子是现在拍的,离那个事件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非常感动,我之所以写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美援越的那段历史大家不是很了解,原来都是没有公开的,目前也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把它写出来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另外这几个年轻人的革命理想也让我非常感动,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点目的,也不怕艰苦,就是怀着一种非常纯真的理想去参加革命,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贪图物质的享受。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红卫兵很傻,但我却觉得非常感动。除此之外我写这个类型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如果前期多做一些工作,到越南去走一走找找感觉,我觉得写出来问题也不大。这就是我近期的一些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