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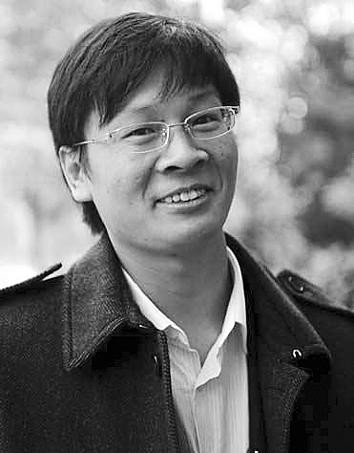
黄惊涛
担任商业杂志副主编的黄惊涛,近年写起小说,在专业文学评论家眼中十足是个“野孩子”:他以怪诞之极的想象书写自己的文学地理,寓言式故事背后是他对探索世界的热情——人类为何不能追求绝对自由,结局会如何?文学给了他勇气和胆略,可以去直面惨淡与失败的存在,文学赋予人类的超越性也正在于此,就像新作《引体向上》里的主人公,进入宇宙另一颗星球时,绝对孤独之下的心愿是获得一本书。黄惊涛的作品告诉读者,当文学回归想象力本源时,其中一切悲欢与生死,都在试图诠释生命本有的深度与厚度。
反寓言让文学生命力更丰沛
记者:我看到的“70后”作家里,仍然有许多是像前辈作家一样,为自己熟悉的故乡书写一个系统的、庞大的、完整的小说架构,你的《花与舌头》《引体向上》其实也是写给家人和土地的,但采取的是一种看似非理性的、寓言式的、幻想的方式。
黄惊涛:你所言的那些作家,是我所羡慕的,他们有自己的根据地,像马蜂筑造蜂窝一般,鳞次栉比、密密麻麻地建设他的“家乡”,他们拥有一种在纸上建设城市乃至帝国的雄心壮志,但我自感是个漂泊者,没有专门要在哪方水土上建立营寨、打下江山的志向。虽然我亦常流连、牵挂于故乡、亲人,但我的写作是抽离的、抽象的,我在《花与舌头》中虽然也建造出一个瓦岗寨般的“光荣镇”,但它不是某一地域的直接映射,更大程度上我希望它是对整个时代和社会人类顽疾的显现,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被批判者,也置身其中,不能自外;而《引体向上》,我干脆写了两个想抛弃地球的人。说到底,任何的写作如果没有灵魂,我们的肉体都将四海为家,跟有没有完整的地域架构无关。
记者:在小说集《花与舌头》里,书名透露了许多内容,佛教故事里有拈花一笑,舌头又是自由自在言说的象征,对现实可能有许多话要说、想说,但怎么去说、怎么选择文体,你是如何考虑的?
黄惊涛:在文学中,我热爱虚构,不爱真实,诚如我热爱荒谬,不爱真理。正是在荒谬和虚构里,真的真实与真的真理才得以新鲜地呈现。很多事物是不可说的,伽达默尔说“语言难以抵达它的及物世界”,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思一经语言的转换,常常不再是它原初的样子,但文学是“说”的艺术,花中有玄机,花不能言我为之言,文学的使命就是说出你所见所思的世界。如果没有了表达,世界像佛偈中的菩萨那样,笑而不语,或者像远藤周作先生在小说《沉默》中所追问的,上帝一直不发一言,任由信仰他的人、做他的使徒的人身陷苦难,那么沉默就是一种罪孽,是上帝之罪、菩提之罪与文学之罪。文学肯定是要把人从牢笼中解救出来,有关我们的,有时是社会,有时是我们的身体。
记者:小说里,42个短章故事引出了许多有趣的人物,他们各自独立又最终连成一片完整的“光荣镇”,而道具和人物姓名是很西方化的,他们卖故事、偷姓名、懂鸟语、贩梦境,以一种温暖有趣的形式在讲述暴力、禁令、失去、死亡等严肃问题,你说“在故事已经搬上流水线生产的年月,愿意做一个织毛衣的男人”,那么这件“毛衣”的款式是“世界性”的。
黄惊涛:“日头底下并无新事”,世界在一再重复它的故事:战争、疾病、饥饿、不道德的情、有道德的性、出生、死亡、喜悦、哭泣……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地狱中,他的祷告、呼喊就需要耳朵,文学就是那只倾听的耳朵,同时也是扩散他的告解、吁请以达天听的咽喉。如果人类真有一天全部进了天堂,那也还需要文学来描述天堂的模样。但文学不能像新世界对旧世界的重复那样来重复它自己,文学的身上可以有机油味,但不能都规格一致、大小统一。我为很少的个体织他们的“毛衣”。至于这些毛衣在风格上是近于西方还是东方,倒是有点“声西击东”、掩饰的意味。不过这也反映了我的一些小说价值观,我并不认为一个中国人就必得按照他的母语的方式、原生的生活来讲话。套用克罗齐的一个句式,他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也可以说“一切过去的文学传统都是我们的传统”,比如,李白的时间距离,并不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我们的时间距离近,像我这样的南方人,孔子的地理距离比川端康成的地理距离还远。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的,但在文学传统上是认同杂糅合一的。
记者:这种阅读感觉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那种打破时空次序的讲述,当然那种西域故事本来就可以有传奇成分和想象空间,在《花与舌头》里,如此密集的绚烂意象让我感到是在进行一种呼应。
黄惊涛:说实话我在写《花与舌头》系列前压根就没有读过或完整读过《看不见的城市》。在早年的阅读上,我是个特别固执且单调的人,我热爱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喜欢他像经历了一切但又保持“太初有道”之际的纯洁的语言、语气和语速。当一些朋友说我的风格像卡尔维诺后,我才去读他,才发现并认可他的精妙、他的轻、他的繁复之美。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很后悔如果不那么偏执并善于学习的话,《花与舌头》可能不会那么杂乱无章、漏洞百出。《看不见的城市》是一本了不起的经典,倘若有人说我戏拟甚至模仿了它,我不视为丢脸,而以为是很荣幸而自豪的。倒是写出《花与舌头》之后,卡尔维诺对我真正的影响才到来,我把他列在心仪的主要作家之列。
记者:《韩非子》里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儒以文犯禁”,评论家李敬泽也在序里说,这是“不服管理的舌头”,寓言性的故事往往有许多可阐释的可能性,你在挖掘言词背后所能达到的更广阔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惊涛: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从诞生之初就为了讽喻世界而存在,同时也因为它具有修辞性而比“直陈此事”显得高妙、有趣一些。读者往往热衷于挖掘寓言背后的寓意,以最后能从寓言中获得“意义”而产生不虚此行的“获得感”。然而我是反对意义的这种简单地正向呈现的,或者说我骨子里就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写的是寓言,那么我的寓言的意义就是要告诉你人生没有意义。传统的寓言往往追求一个有意义的结局,而我更喜欢“不知所终”。寓言因为有了确切的指向而丧失其复杂和多义,只有反寓言,才能使它回到生命力丰沛的丛林时代。
好的文学是为了识别苦难
记者:今年新出版的《引体向上》几乎是以“软科幻”的方式在对当下和未来世界进行描摹,看似认真科幻叙事的同时,却又包含着反科幻、反逻辑的叙事,但不得不承认,假借科幻的意象能让想象落地,也让最终的挫败感更有力量。
黄惊涛: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引体向上》写成一部逻辑精密的科幻小说,那是理性的科学家般的人生引领者的事业。真正的科幻小说拥有机械的推动力、科技的牵引力,那显示出人类是有力量的,但某种程度上不具有悲壮感,而拖着自己的肉体在砂石上磨砺前行,磨出骨血,是另一种力量感,并且试图在力量中显出某种滑稽戏般的荒凉。“引体向上”的意象更像是西西弗斯推巨石,每前进一步,巨石都有可能滚下来碾压推石者。我执着于这个意象,写作的过程中常常想象一个人在宇宙或星辰的边缘攀援,不要脸地说,写到好几处时,我有热泪盈眶、愤怒又被加深的感觉。我首先是把自己催眠了,但正如力量不够、耐力不足会从单杠上掉下来一样,我的写作很可能是无力的,我这个催眠师自己先睡着了,而读者尚还清醒,我能听见他们对我的讥笑和不信任。也罢,我接受这种失败的命运。
记者:你提到的热泪、愤怒或许就是推动自己写这部小说的动力。人类总是受限于自己的能力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人类也一直对地球之外有漫长的想象和向往,但那里一定存在绝对的自由吗?你的小说对此有所质疑。
黄惊涛:假设《引体向上》里面包含了某些寓意的话,那么我想最大的寓意在于表达“自由的失败”。追寻绝对的自由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绝对自由之境,我深知这一点。只要人的灵魂还在自己的身体内,那么身体就是它的监狱,“存在”就是监狱。我们永远是自己的灵魂看守和典狱长,更遑论社会、制度、道德的诸般桎梏。但如果不去求索所谓的自由,不在这条道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弄得头破血流,人是会堕落的。在堕落与失败之间,我选择失败。
记者:许多作家会书写自己的“x托邦”,比如乌托邦、异托邦,《花与舌头》里光荣镇居民好像各有技能,生命长久,却不断在失去美好的东西,《引体向上》里好不容易踏上了外太空星球,却让我和爱人聋了、瞎了、分离了,这是一颗“冉·阿让星”。在你的反乌托邦里,任何地方都会变成一个囚徒之境,但这可能让读者更清醒。
黄惊涛:《花与舌头》与《引体向上》都是反乌托邦的,我建造光荣镇与囚徒星这两个营盘的目的是砸烂这两个营盘,破除它们有关美好的幻象。假定文学还有点无用之用,还能拯救些什么,那么它也是以毒攻毒,从反向来用力的。这是我欣赏的文学。很多正面养育人的文学我以为那是鸡汤,然而人生并不时刻都需要摸着肚皮打饱嗝。我认可的好文学,不是使你变得更强壮、更扩张,而是使你变得更仁慈、更悲悯、更虚弱,更不容易作恶。只有在遭受侵犯时,它才会更柔韧地帮你守住自己内心的城防。好的文学甚至不是为了寻找幸福,而是为了识别生活的苦难之味,不是把苦难遮掩起来,而是把它开掘出来,明白了苦难,你的人生才更具厚度和宽度。
记者:作为“70后”作家,其实对中国文学经验和世界文学经验方面都很熟悉,从你的感受来说,书写中国与书写世界是否已是一件事情?我也能感受到,你对自己、对外部世界讨论的热情和力量都很充沛。
黄惊涛:因为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世界正在趋于“大同”,一切都在交融,文学亦是如此,中文与英文的句式差别并不大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差别。我不认为文学就只能描述一块土地、一种本土经验,从哪里出发又要到哪里去,是由写作者个人决定的,不过我的写作还是从自己的居住地出发的,我最近写的一个《天体广场》系列,就是围绕着一条叫体育西路的路和恒大的主场天河体育场来展开的,另一本待改定的长篇《拉磨转圈》也只是为了回应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疑惑,即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呈周期性的摆动而不能走出新的循环?我对困扰自己的问题一向有足够的热情去琢磨。
记者:我知道你开设了“未来文学”微信公号,介绍许多中外作家名篇,如果文学有未来的话,可能未来还是存在于所谓经典性中,才有生命力去历久弥新。
黄惊涛:我办了一个公司叫树冠文化,公司名正是取自我后来喜欢的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树冠经由根茎而与大地、现实相连,树冠因高于尘土而得以产生朝向天空的想象力。同时我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未来文学工作室”。未来文学的传播形态可能会有极大变化,但好的文学依然会深入人心。好的文学或者说“未来”的文学并不都是新的、拔地而起的,如果能够在创作上回到荷马史诗的年代或诗经楚辞的时代,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天马行空、生机勃勃的气象。我憧憬那种气象:天人未曾分离,人鬼莫相分辨,大地辽阔而苍茫,想象力可自由驰骋,万物皆备于我,我又与万物与邻……如果我们的文学中还有这些镜像,那该是多美的文学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