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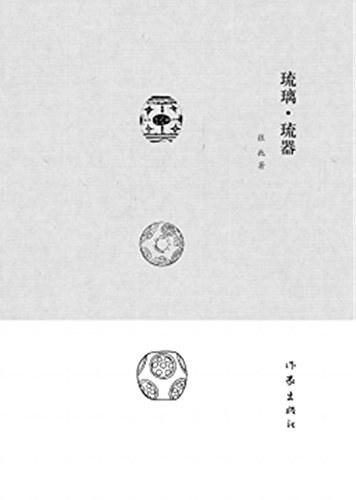
《琉璃·琉器》,张弛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39.80元
在我看来,青年时代的写作是靠荷尔蒙,中年时代的写作靠才华,五十岁之后的写作,比如我现在,应该摆脱个人化的痕迹,多一些常识,多一些质朴。
在中国作家里,张弛是个特别的存在。他大学时学外语,当过导游,开过古玩店,也做过编辑、记者,拍过广告,写过剧本,还演过电影,现在自己也涉猎纪录片和网络电影的拍摄。十几年前,随着嬉笑怒骂、纪实与虚构共冶一炉的两部长篇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的出版,他成为个人风格强烈的畅销书作家,曾同时开几个报刊专栏,有众多忠实读者,保持着连贯的出书节奏。而后,互联网在中国日益普及,人们的表达途径和交流方式都因网络的存在而更加多元,虽不能说这些变化影响到张弛的写作状态和影响力,但也不是全无关联。
三个月前,张弛推出以琉璃这种中国古代器物为线索、以春秋时期历史为背景的跨文体长篇新作《琉璃·琉器》。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琉璃”侧重讲述从范蠡、西施等历史人物切入的春秋时期吴越之争,在历史叙述中不时闪现作者的评说和当下情境;后半部分“琉器”则以作者和几位朋友循着环太湖若干城市的春秋故地行走、探访遗迹、参观博物馆、接触当地人的见闻感悟为主,间有对于某段历史事件或某件文物的延伸阐释。用张弛自己的话说,就是正史未曾写到的那些历史线索,是作家可以据此虚构创作的空间。
《琉璃·琉器》问世后,无当年《北京病人》出版时的热闹。张弛对此倒是释然,时过境迁,他对写作乃至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有新的理解。面对本报记者,张弛偶尔闪现他招牌式的坏笑,和令人停顿一下忍俊不禁的幽默。他的生活和创作充实而丰富,和几位聚饮多年的文学同道常常碰面,除了写作还热衷于影像、前卫艺术领域的创作。他告诉本报记者,由他编剧,施润玖导演的电影新作《空谈》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他手头在编辑的关于一百个中国古代面具收藏的“无字”书,也令其谈兴勃勃。
中华读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古董收藏、古代器物研究感兴趣的?
张弛:1985年我做导游,免不了去一些博物馆和古代名胜,还会带着游客去购物。当时,专门接待外宾购物的北京友谊商店一楼是文物商店,有些文物出售。到了1990年,我在琉璃厂的一个文物商店里租了两个柜台,卖古玩字画。那时真是有很多好东西,傅抱石的人物册页呀,成色上乘的翡翠镯子呀,波斯地毯啊,这些都经过我的手。但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要搞收藏。爱好收藏这么多年,我反思,还是有负面的地方,比如我看到一件古玩,会志在必得,买了也不过放在家里,偶尔拿出来看一看。个别收藏,像琉璃这样最终能形成一本书,但大多数的收藏是形成不了的。之前我确实没见到多少关于琉璃的书,特别是没有《琉璃·琉器》这样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写法。
中华读书报:读了《琉璃·琉器》中那么多关于琉璃和春秋历史的内容,感觉琉璃应该是你的收藏中比较集中的一类。
张弛:为了写这本书,这几年我确实突击收藏了不少琉璃。其实最初我并不喜欢琉璃,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不认为琉璃是本土的东西。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开的皮影店里看到几个琉璃珠子,外头沾着金粉,里面是琥珀色,非常漂亮,放在手里感觉比石头还沉,有金属的分量。
我当时想要修复其中破损的一个珠子,就去查了琉璃的来历和工艺,查到春秋战国那一段,发现琉璃的历史原来和范蠡、西施有关,联想到不久前我看的剧作家邹静之的歌剧《西施》,既然有现成物件,有历史背景,还有成型的文化作品,为什么不把这些串在一起写个东西呢?后来,我多方面搜集资料,读一些历史和琉璃方面的书,去很多国内的博物馆看琉璃文物,到文物市场买一些老琉璃,最初辨不清真假还吃了很多亏。也走访了一些老琉璃工匠,跟他们交谈。基本上对琉璃的来龙去脉了解了一些,争取达到中国人所谓的从器到道的结合吧。我在《琉璃·琉器》这本书中也写到了,中国人一向很重道,不重器。
中华读书报:当年读《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感觉你这个人和你的写作都比较随性,但看了《琉璃·琉器》的序言,知道你为写此书做了很多准备,这在你的写作经历中还是第一次吧?书后面附上那么多参考文献书目也很不像你以往的风格。
张弛:书后附上的参考文献多少带些半开玩笑的成分——给这本书增加一些学术的外壳。本质上,这当然不是学术范畴的书。不过,在一部文学书后附上一些看着很学术的参考书目,有些西方作家早就这么干了。我觉得《琉璃·琉器》是跨文体的写作,游记、读书笔记、小说、历史文献,这些放在一起相互映衬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通过这些年阅读文物考古、历史方面的资料,走访历史遗迹,看博物馆的藏品,让我的文字表述不像过去那样“哗众取宠”,而是更完整更严谨,逻辑关系更明晰。在我看来,青年时代的写作是靠荷尔蒙,中年时代的写作靠才华,五十岁之后的写作,比如我现在,应该摆脱个人化的痕迹,多一些常识,多一些质朴。
中华读书报:我看《琉璃·琉器》的感觉是,前半部分“琉璃”是在历史叙述中夹杂着穿越似的虚构笔法和调侃,而后半部分“琉器”主要是你和几个朋友的行走、考察经历,但穿插着历史叙述,这种前后的结构以及各自的正说和调侃比例如何确定?
张弛:上半部分“琉璃”就是在讲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这部分是我在家里完成的,主要通过大量读书、查资料,外加自己的文学想象。下半部分“琉器”,是我把我们这帮人比喻成“琉器”,通过到环太湖的那些城市去寻访琉璃,包括无锡、扬州、绍兴、诸暨、杭州几个地方,都是春秋故地。这部分给人的感受会更真切。实际上,到诸暨西施故里探访,和当地讲解员交流,去博物馆看器物,在绍兴爬越王山,等等,这些体验如果你不去当地就感受不到。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写作会是你之后写作的一种趋向吗?
张弛:让我再写这么一本书很难很难了,需要多方面的因素结合。再碰到一个这样的题材不是特别容易。
中华读书报:你在“后记”中说,“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陷阱,必须当止则止”,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
张弛:传统文化中,我个人不太喜欢教化的部分。有时候你要看哪部分是传统文化,哪部分不是,中国历史太长了。写这本书之前,我对春秋时期也有一些误解。都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实际上,礼崩乐坏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的青壮年时期,是秀肌肉的时代。那时的礼乐制度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中国文化需要这种青壮年时期。你要是说,礼崩乐坏就一定是坏事,我倒是乐意看到春秋时代那样的礼崩乐坏。笼统地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有害,尤其是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仅仅意味着诗书礼乐的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得不够的表现。
中华读书报:十几年前,你的《北京病人》出版的时候,包括你在内有好几位文风幽默、注重语词提炼、穿插段子调侃的作者,那时得算前网络时代吧,你的作品读者众多,出书也很是连贯。
张弛:是啊,记得那时我和狗子、阿坚一起出了一套“边缘丛书”,都是随笔集,那也是我出的第一本书。那时我对“边缘”这个词没有太多理解,就是觉得自己想特立独行一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果然被边缘了,哈哈。
现在看来,《北京病人》写得太片段化,是把人物的生活细节和一些神话联系在一起。到了《我们都去海拉尔》,写得就比较放得开了。不过这两本书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都借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或者说笔记小说的写法,像《世说新语》那样的。
中华读书报:如今互联网相当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和网络交流方式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渠道,这样的时代对于你的写作甚至表达有怎样的影响?
张弛:一开始,好多人撺掇我开微博用微信,他们以为我写的东西中那些段子会让我迅速成为“网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作品中那些幽默调侃的部分还是很书面的,和网络上的段子有本质区别。网络段子太直接,我这些调侃更多是自我调侃,是对文化的一种认识,有些还有文字上的游戏成分。网络段子是给大多数人看的,但在网上要用文化的方式开玩笑,就容易冷场。
中华读书报:一方面你觉得时代不同,读者对你作品的关注有所减弱,另一方面,这些年你写作的数量和出书节奏也在减缓啊。
张弛:是啊,十多年前我每年基本上都会出一本书,要么会编一本书,同时开好几个专栏写随笔。这两年确实没怎么出书,这次出了这本《琉璃·琉器》,和我以前的写作很不同。我现在倾向于出一些难出的书。
中华读书报:你指的是写作的难度还是出版的难度?
张弛:二者都有。最近我正在编一本无字之书,是我搜集的大概一百个中国古代面具的图片。这些古代面具很神秘,跟它们对视时会感觉有一种交流和沟通。所以,所谓的“穿越”,实际上就是瞬间感应,不像大家说得那么邪乎。完成了这些面具图片编辑,会觉得文字是多余的。看面具的表情,那空洞的眼睛和嘴巴,就够了。
中华读书报:除了编这样的“无字”书,写作还是要继续吧?
张弛:现在我确实对读图比较感兴趣,看到这类书也会买。写作当然还是要写,比如写诗。我上大学的时候,十八九岁就开始写诗,二十多岁疯狂的时候,一天能写20首。写过诗的人都知道这种感受,一日为诗,终生为诗。这些年,我维持着每年写一两首诗的节奏,为的是有一点诗人的感觉,保持这个手艺。诗集也是我想出的书。至于我以后的写作,毕竟我从事古代器物收藏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不可能收藏就只是买了卖了,还会牵涉到考古、联系到历史层面。包括这本《琉璃·琉器》,我个人从事收藏多年,作为一个搞文学者的收藏,不可能收藏只是买了,卖了,必须牵涉到考古,一定也会联系到历史,但归根结底出发点还是个人爱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