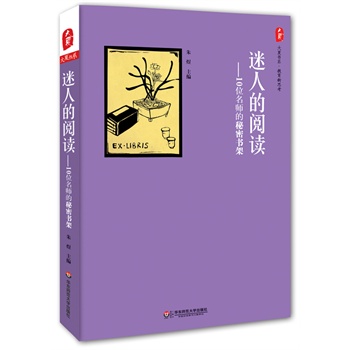 朱煜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教师:在读书中生存 1922年8月6日,梁启超在国立东南大学(即今日南京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作演讲,题目是《学问之趣味》。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当然,趣味有高低之分,梁启超本人以为最高的趣味是“学问之趣味”。而“学问之趣味”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无所为(wèi)”,即不将读书治学视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正如孩子的游戏一般,“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二是“不息”,也就是“上瘾”,把读书治学当作自己的本能。 三是“深入的研究”,他说“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四是“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 梁启超的这番话,至今已逾90年,还是新鲜、活泼、有趣味的,也是我所崇信的。 最近我读了一本好书——《阅读史》,是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的,篇幅不短,有三四十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出版。书中介绍的虽然是西方人几千年来的读书历史,但其中经常穿插着作者自己的阅读经验与感受,所以读来并不枯燥。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也是一种阅读的趣味,作者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趣味来引发读者的趣味。可惜的是他对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阅读历史缺乏了解——这也难怪,但我读了之后,觉得道理是相通的。 曼古埃尔在“学习阅读”一章中说:“在文字社会中,学习阅读算是一道入会仪式,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熟沟通的通关仪式。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记忆,熟稔此一社会的共同过去——每一次阅读,他∕她或多或少都会对此共同过去获得新知。”(见该书第89页)——这个说法很在理,其实我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是通过书本进入知识社会的大门的。只是有的人进大门就停步不前了;有的人入门之后还想深入其堂奥;有的人进入某一房间在角落找个位置就不想动了;有的人到处游览,趣味盎然。我以为,既然进了这一知识的大门,还是到处看看为好,不然的话,枉然来人世一遭,太可惜了。 至于教师,也就是先行进入知识社会大门的人,由于来得早,当然也就有了引导后来者的责任。但是今日绝大多数的教师,犹如各个旅游景点的专职导游,每天接待、引领一批批游客,在自己设定的路线上走动,每到一处就背诵一大段别人为他写下的解说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可是说来说去总是这么几句话,连自己都听厌了,最后把客人送出大门,算是尽了一天的责任。而教师比“专职景点导游”还多了一道苦差事,就是最后要应付学生的考试,也就是“游客”在听完“专职导游”的讲解后,到大门口还要经过一次考试才能“过关”。 这就是说,在入了知识大门之后,学生都要例行公事般地读、抄、默、背、做题目,然后考试合格,被“放出去”各寻生路。他们再也不能饶有趣味地读书、思考、对话、探索、研究、深入到知识的堂奥之中,更难以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大家都成不了“读书人”,更不用说“学者”了,因为兴趣索然了。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我们教师而言,就是要首先进入“读书状态”。还是这位曼古埃尔先生,他在《阅读史》中引用了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的一句名言:“阅读是为了活着。”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行:“活着是为了阅读。”多年前,我到北京去拜访九十多岁高龄的张中行先生。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那就起来读读书、写写文章。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还活着,还是读读书、写写文章。”这种生活态度真令人钦慕,但我们并不是做不到,当然我们的书读得没有张先生那么多、那么透,文章更是写得没有他那么好。 教书的人,要多读书,时刻不停地读书,这才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常识性的真理。可惜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除了教材和教辅材料之外,其他的书基本不读,这是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主张:教师要在读书中生存,要处在真正的“读书状态”之中。这就需要教师们时刻保持读书求知的兴趣。从搜求信息者的角度来看,知识只是别人提供的无穷信息;从谋求利润的商人的立场来看,知识只是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取利润的货色;从传教士的眼光来看,知识或者是使人驯化的法宝,或者是使人“堕落”的“业障”……真正的读书人当然会超越这些片面的认识和误区,走上追求真知的大道。吸引人们的只是知识本身的力量,推动人们的只是求知的趣味,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这才是区别真假“读书人”的唯一标准。(商友敬)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