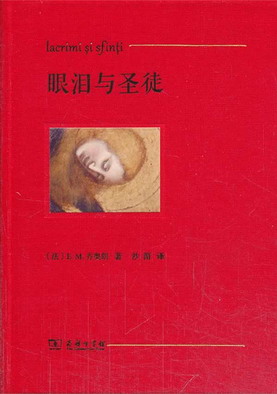 《眼泪与圣徒》(沙湄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一版),是齐奥朗(Emil Cioran)青年时期在罗马尼亚出版的最后一本用罗马尼亚语写的书。1937年,也就是此书问世的时候,27岁的他已奔赴巴黎了。他在巴黎出版的第一本用法语撰写的著作是《解体概论》,那已是1949年的事了。在1937年到194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齐奥朗浸淫于法语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一种“查着字典写情书”的精神进行着。在语言的表象上,存在着从罗马尼亚语到法语的转换,那么,在书写的内容上以及精神上,是否也有实质的变化呢? 我们对《眼泪与圣徒》、《解体概论》以及1952年出版的齐奥朗第二本法语著作《苦涩三段论》(Syllogismes de l’amertume)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在内容上、精神上,甚至文风上、修辞上,几乎没有显著的差异,尽管表面上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跨越。 试着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眼泪与圣徒》里有一则写道:“(要是)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虚无。可上帝正是至高的虚无!”(中译本第133页)我们再看《苦涩三段论》里的这句:Sans Dieu tout est neant; et Dieu? Neant supreme(要是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虚无;那么上帝呢?至高的虚无)。这是齐奥朗的一次自我重复:他把自己以前用罗马尼亚语写过的东西又搬到法语里来了。 在我看来,让《眼泪与圣徒》在齐奥朗一系列格言体著作中显得特异的,是它处理的主题——基督教神秘主义。上帝、死亡、荒谬、失败、孤独……这些关键词贯穿齐奥朗的写作始终,但神秘主义以及天主教圣徒,的确是在《眼泪与圣徒》中才被集中思考的。 在时下的中国,还没有可能就齐奥朗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思考稍作评骘,因为我们连基督教神秘主义是怎么回事也还不甚了然。我稍稍读了一点恩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女士的名著《神秘主义》,才多少能够进入齐奥朗的那个语境。更深的研讨无从谈起,但至少我们可以说,齐奥朗对神秘主义宗教体验的观察是体贴入微的,比如他讲“出神”(ecstasy):“灵魂处于持续的张力中,整个存在随之忘却了对肉身的依附。内在的火焰将肉体的抵抗提炼到如何地步——身体荡然无存,只剩下非物质的出神。出神之恍惚的高强度一旦减缓,向寻常状态的回归就开始了,伴随着那种本已忘却的身体又被重现发现时的惊愕之感。”(中译本第43页,译文稍有改动) 当然,就其写作的本质而言,齐奥朗是一位警句作家。就像乔治·斯坦纳批评齐奥朗时曾讲过的那样,“格言、警句、箴言,是思想的俳句”,说它是俳句,便暗含着一个意思:它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没有论证,没有推演,没有体系,或者更直白一点说,就像一首抒情短诗那样去体味它罢,别去深究了。事实上,我们当然可以为齐奥朗的思想演绎出一个体系出来,但假如那一切不是以他那种警句的方式被言说的,可能也就没有被言说的意义了。 齐奥朗有一种思维的模式,是说某一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这些外在于它的人来说,却又有另一种意义。比如,圣徒是没有意义的,但圣徒是没有信仰的空心人的一面镜子。再比如他讲“最后审判”:“尽管最后审判纯属一派胡言,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可以解释我们的虚无。无论其形式是神圣还是世俗,这种历史终局的表现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都是必不可少的。最为荒谬的理念就这样获得了命运的力量”(中译本第165页)。一种拟构本身是无意义的,但它对我们来说又有用,这就是齐奥朗式的思维。自然,对这种思维,一个英国人很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干脆管铲子就叫铲子呢?” 《眼泪与圣徒》的中译本兼有严谨、灵动两种品质,的确是近年罕见的佳译。像刚刚引用过的“出神”,译者没有随随便便译为“狂喜”;书中提及的圣徒名字,均依天主教习惯的译名书写……这些地方,很能看出译者的态度与修养。虽然《眼泪与圣徒》不能算是一部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正经著作,但《眼泪与圣徒》的中译本却是我们了解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