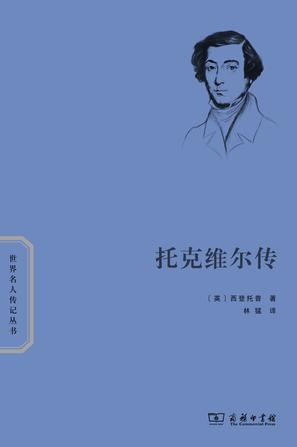 政治和解是可能的吗?托克维尔对法国和美国的思考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里·西登托普撰写的《托克维尔传》,更是将此主题融入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史中。 在作者看来,正是在经验及推理的共同作用下,让托克维尔听到了历史之河的波涛汹涌声,也看到了它的流向。但耳聪目明绝非天赋异常,而是首先得益于两个“教父”: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及当时自由派的扛旗者基佐。 马尔泽尔布同情启蒙哲学家的“生而平等”学说,在路易十六时期不仅要求“恢复对王权的传统限制,还要求人民的自治。”短暂参与革新后,随着杜尔阁的倒台而辞职,但路易十六并没有要他的命。而当他在国民公会上为路易十六辩护后,“由此展开的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他本人、进而几乎全家的死亡。”“马尔泽尔布这种行为表现出来的无私,赢得了他曾孙终生的热爱。‘我是马尔泽尔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对托克维尔而言,马尔泽尔布身上表现出的道德勇气恰是贵族身上为数不多的优点,而这应当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中予以保存。 1822-1823年法国“大辩论”时期,鲁瓦耶·科拉尔所领导的自由派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已明确提出“这是一场旧制度和革命、旧法国和新法国、‘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斗争。”基佐吸收了这场辩论中蕴含的对欧洲制度和信仰演进的思想,尤其将辩论主题总结为原子化和集中化。当然,基佐带给托克维尔的不仅仅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自由派思想,而更是“分析的头脑”。“将近三年里,他每周六都从凡尔赛赶往巴黎,加入古老的索邦学院汹涌、激动的人群中。” 作者毫不避讳托克维尔的自由派本质。在他看来,托克维尔显然已经洞彻了中央集权的实质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遗弃和毁灭。他认为,托克维尔找到了保存个人自由的路径,而这个路径绝不是当时法国自由派念兹在兹的英国式议会政治。实际上,“在基佐内阁时期,法国政治毫无理想可言,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复辟时期的那种重大政治议题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蔬菜牛肉汤,托克维尔为之而惋惜和悲愤。他只能扮演卡桑德拉的角色,这无法让他满足。”对基佐采取的政治措施的不满,让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自由派自身的不足,即原子化的个人式自由无法应对当时的中央集权冲动。 作者认为,托克维尔几乎所有的思考都着力于回答当时困扰法国自由派的这个问题,即“如何在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在托克维尔看来,“无论自由派还是极端保皇派的方案都不够说服力。自由派希望采用英国的议会制度,却忽略英国地方自治的保障不是议会主权,而使一个强大的‘自然贵族’,这个因素在法国并不存在。极端派的方案企图否定法国数个世纪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重建以旧特权为基础的社会,通过贵族制来复兴地方自治,这同样难以让人信服。”事实上,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向曲折往复不过是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无法和解的表现。因为他们不是尝试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推动革新,就是试图用革新的方式来推动中央集权——这些手段非但匮乏经验的支撑,在逻辑推理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但对托克维尔既褒奖贵族如马尔泽尔布式的道德品行又谴责罗伯斯庇尔时期暴民式的恶行如何理解呢?鲁瓦耶·科拉尔所谓的“这是一场旧制度和革命、旧法国和新法国、‘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斗争”这一论断虽然清晰地指明了政治和解的不能,但与此同时无疑也将更多人带进了歧途:这种阶级意识浓厚的修辞,尽管表面上十分有力,但却完全不利于法国政治秩序的重建,因为他们正是以等级的偏见加深彼此的敌视——这充分解释了为何法国贵族不是选择与第三等级合作,而是倒向了君主。“鲁瓦耶·科拉尔创造的意象,一个日益趋向中央集权的原子化社会,正是为此服务的。它让我们注意到,民主社会通过使个人摆脱传统身份与依赖的纽带,一步步地破坏了社会所具有的团体特征。最先被牺牲的,是过去曾为分散权力和权威起过重要作用的中间机构,各特权等级、省三级会议、行会、高等法院、庄园法院,这些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了个人。受益者则是国家,它独自就可以声称代表了全体平等的人民的利益,因为作为民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权利体系,就出自国家之手,护卫者也是国家。所以,社会平等的进程也要求国家的扩张,两者具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托克维尔看到在法国建立起自由的社会制度匮乏与之相应的物质条件。从根本上说,当时的法国缺少足够能塑造出自由的政治秩序的公民。事实上,将托克维尔笔下的贵族与暴民理解为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也并不全面,他更有可能指的是某种新形式的“公民”:既不是君主制下的臣民亦非民主制下平等但庸俗的个人。 因而,当托克维尔足踏美国时,所见所闻让他对此危机的克服有了更为直观的判断:公民应当利用舆论和组织政党的形式介入政治,而对付幽暗王国式“利维坦”的不二法门就是地方自治。“他把美国联邦制看成是美国人的自由民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把权威的范围由乡镇一级经过各州再延伸到国家一级。美国人的道德共识,美国之不存在贵族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冲突,意味着他们的自治习惯不会因残酷的阶级斗争而遭到破坏;相反,自由的民情创造出了新形式的国家。”这几乎将读者从对托克维尔概念化的理解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在作者看来,托克维尔著述中的“旧制度”、“革命”、“陪审团”等等词汇的背后,有着一个更为生动且具体的指向,即公民。因此,托克维尔从美国政治制度中获取的经验——地方自治就转而为公民的自治和共治。 事实上,革命之后的法国已经将英国式的议会政治道路堵绝,面对一盘散沙、原子式的社会现状,“托克维尔借用了美国的乡镇自治,修正了复辟时期自由派的中央集权思想。……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对托克维尔的另一个作用是,证明在政治体系中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实践上的好处,也有道德上的好处。就前者而言,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关于利益的理论。……把各种利益看成一系列同心圆,就像美国的乡镇、县和州那样,一个好处是有助于在民众中形成一种基本的正义观念,从而不受前两种利益理论的蛊惑;同时,它为公民提供了一份公共事务中应该加以考虑的各种重要利益的一览表;最后,他也很好地揭示出,政治体系可以如何培养和教化其成员,让他们注意倾听各种正义的诉求。” 作者的这些论断也将托克维尔身上的共和主义特质揭露殆尽。尽管托克维尔的视野所及几乎全部为制度上的设计、选择和安排,但背后却无疑正形成一个对法国而言崭新的“公民”形象。和他对真正的“贵族”的观念相符,真正的“公民”也绝非等级的偏见,而是动机的纯正。作者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论述的自然环境、民情以及法制因素中,推导出“一个民主社会发展出了自由的民情,形成了地方自治和结社的习惯,普通人就很容易转变成公民。自由制度往往在潜移默化之中,将人们从对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转到托克维尔所称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而这种自由的民情得益于“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结成联盟。不过,“在法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为敌。” 作者同样指出在托克维尔这里贵族制并非一无是处,民主制也不是尽善尽美。尤其是在对抗高度的中央集权上,后者的缺陷更为明显:“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社会要想进行统治,看来不太可能,即使是英国贵族制这一人所皆知的榜样也是如此;它的结局除了无政府状态,或者一种新型的暴政——官僚制国家,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民主社会的真正考验不在于道德自主太多,而是不足;不在于丰富多彩,而是过于单调。从前,贵族社会为一些不同的价值提供了聚合的基础,比如军事贵族的爱国热忱和热衷炫示,资产阶级的精明审慎,农民阶级的坚忍节制,教士阶层的注重来世。这些价值和态度在社会中永久地维持着,内在地构成了一种多主义。然而,民主社会究其本质就无法为这些价值和态度提供一个恒久的制度基础,接受何种价值和态度成为个人的选择,于是这种接受变得极为脆弱而不确定,一如民主社会中个人身份的不确定及结社的不确定。”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做出了“自然”演进的解读,他认为,美国正是通过利用宪法的手段,在政治系统亦即国家中实现法定权利的分散,从而保护地方自治。“美国的殖民者按照他们认为的、一个民主社会的‘自然’方式组织了政府,而没有被阶级意识所阻碍:首先在乡镇一级组成了自我治理的敌方政府,然后在地区一级联合组成州政府;过了很久,才考虑并实际组成了州际政府,也就是全国性政府。”就此而言,“法国的中央集权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尽管这里的“先知”在书中很明确地指向了罗慕路斯、萨伏那罗纳等人,但如何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交战的时代将这些“先知”替换成为“公民”则成为棘手的问题。波考克就此引申出“马基雅维利时刻”——“只有武装公民才是真正的自由人,但并不认为他必然是个好人。罗马史记录了这种公民如何用他们的自由建立起主宰别人的帝国,但是却被这个帝国所腐蚀,即使他们先是失去自由,继而失去帝国。”但是对托克维尔而言,他关注的重点不是这种观念史或者思想史上的延续,而是切实的、能在法国实现的某种宪政结构。在他看来,美国的联邦制恰好就回答了法国自由派的问题。 “让人感动的是,托克维尔仍然努力地想要理解,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在旧制度最后的几十年里陷入的道德孤立的状态:为何一夜之间它就成为了被抛弃和被迫害的对象?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地方自治的毁灭造就了社会阶级的分立,现在人们之间没有了一起合作共事、追求共同利益的习惯,只有在相互的嫉妒和憎恨中才彼此相关。”在法国难寻的政治和解,在美国同样如此。托克维尔意象中的美国并不包括蓄奴的南方,因为,南方通过引入奴隶制不过是重演了欧洲“最接近于贵族制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为了佐证自由制度无法完全抹去“民情的差异”。 以赛亚·伯林在《马基雅维利的源起》中说:“首先,马基雅维利表明了政治生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之间不可能有最终的和解;其次,只要断定它们最终无法调和,政治哲学的解释就必须继续存在;第三,存在着两种自由观:一为积极自由,它导致每个人的自决权,并且他要面对同样行使自决权的其他人;一为消极自由,它仅仅导致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受妨碍,在这些活动中,跟其他个体的相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法律、政府和教化予以管理。” 在伯林看来,政治和解能否实现根本就不重要,纠结这类问题其结果不过是揭露了不能和解的事实,并为此事实创造出大量辞藻华丽的言说,犹如1822-1823年的法国大辩论时期。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武装的先知”实现的。当然,这是托克维尔以后的政治史。托克维尔看到实现政治和解的途径是地方自治,却对“武装的公民”沉默不语这绝非偶然,而是一个贵族的狡黠了。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