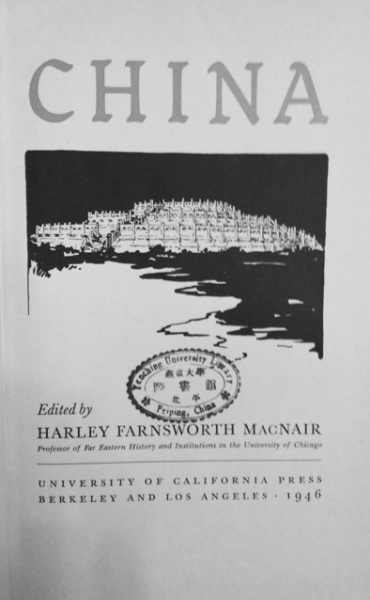
1946年,由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宓亨利(HarleyF.MacNair)主编的《中国》(China)一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被作为第五种列入联合国丛书(TheUnit⁃edNationsSeries)。该丛书的总目标在于“推动二战时期盟国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年代的彼此合作”。前四种——《捷克》《荷兰》《波兰》《比利时》——出版时,二战还没有结束,被编为第一辑,《中国》则作为和平时期的第一本问世。
全书分为6大部分:文化背景、历史与政治发展、哲学与宗教、文学艺术与教育、经济与重建、回顾与前瞻;各部分又分为若干章节,共34章。
第一部分“文化背景”三章:(1)民族塑造(韩玉珊),(2)主导思想(DerkBodde[卜德]),(3)近期的考古发现(WilliamC.White[怀履光])。
第二部分“历史与政治发展”九章:(4)夏商史(LutherC.Go-odrich[富路特]),(5)周史(陈梦家),(6)汉魏六朝隋唐史(邓嗣禹),(7)宋元明清史(FranzH.Michael[梅谷]),(8)中国社会与外族入侵(KarlA.Wittfogel[魏特夫]),(9)民国早期的军阀混战(宓亨利),(10)民国后期的动荡(Paul M. A. Linebarger&RobertE.Hosack),(11)社会革命(AgnesSmedley[史沫特莱]),(12)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EssonM.Gale[盖乐])。
第三部分“哲学与宗教”八个章节:(13)中国思想(胡适),(14)民间宗教(LewisHodous[何乐益]),(15)早期儒家(JohnK.Shryock),(16)宋明理学(陈荣捷),(17)道教(HomerH.Dubs[德效骞]),(18)佛教(ClarenceH.Hamilton),(19)基督教(KennethS.Latourette[赖德烈]),(20)现代哲学的趋势(陈荣捷)。
第四部分“文学艺术与教育”十章:(21)书法、诗歌、绘画(Flor⁃enceW.Ayscough),(22)艺术(蒋彝),(23)建筑(HenryK.Murphy[茂旦]),(24)戏剧(熊式一),(25)古代文学(王际真),(26)当今世界之中国文学(PearlS.Buck[赛珍珠]),(27)战争年代的文学与艺术(DrydenL.Phelps),(28)美国文学中的中国(AliceT.Hobart),(29)现代教育(FrancisL.H.Pott[卜舫济]),(30)科举考试与西方(邓嗣禹)。
第五部分“经济和重建”三章:(31)经济发展(吴景超),(32)农业(裘开明),(33)国际贸易(李卓敏)。
第六部分“回顾与前瞻”一章:(34)世界大家庭中的中国(DavidN.Rowe[饶大卫])。
从以上的列举不难看出,该书涉及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相当于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宓亨利在写于1946年3月9日的“编者序言”中说,他希望这本《中国》除了服务于丛书的总目标之外,还能“体现学界有关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找到了33位作者,其中11位来自中国,22位来自西方,他们都是中国研究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
中国作者方面阵容强大,胡适、陈梦家不用说了,蒋彝是著名画家、诗人,当时任教于伦敦大学;熊式一是著名戏剧家、翻译家,虽然只在国内受过教育,但英文绝佳,曾将《西厢记》全本首次翻译成英文,享誉海内外。吴景超、韩玉珊是学者型官员,分别在国民政府经济部和中央银行任要职,其余几位则在著名大学任教和工作: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邓嗣禹(芝加哥大学)、陈荣捷(达特茅斯学院)、裘开明(哈佛燕京学社)、李卓敏(西南联合大学),他们和吴景超、韩玉珊一样,都是留美博士。
国外学者的阵容同样豪华,既有汉学教授,如卜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富路特(哥伦比亚大学)、梅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也有“中国通”,如怀履光、盖乐,何乐益等。德效骞、赖德烈等重量级学者的加盟更是引人注目。名气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三位:茂旦、卜舫济、赛珍珠。茂旦是美国著名建筑家,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教会大学的校园都是由他一手设计的。卜舫济曾长期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1888—1941),是闻名遐迩的教育家。赛珍珠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因描写中国而获此殊荣的西方作家,她在中国前后生活达三十年之久。
把这么多中外作者召集起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一书虽然在战后出版,但联络组织和分头写作却是在二战中完成的。宓亨利在“编者序言”中特别感谢了陈荣捷、邓嗣禹、陈梦家三位学者,说他们在某些作者答应写稿但最终没有交稿的情况下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cametotheres⁃cue)。翻开《中国》不难发现,在众多作者中,只有陈荣捷、邓嗣禹撰写了两个章节,是“援助”的最好说明。至于陈梦家,早年以写新诗闻名,后来转行研究中国古文字和古史,同样卓然成家,但英文并不擅长。二战后期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和宓亨利有同事之谊,便于被抓来帮忙,《周史》一章是陈梦家一生极为少见的英文作品。
中外这么多专家学者同场献艺,水平的高下立刻显露出来。《中国》出版后,费正清(JohnK.Fair⁃bank)、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孙念礼(NancyLeeSwann)等学者很快发表了书评,他们对中国学者的专业水准给予了一致的肯定,特别表扬了裘开明,裘是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但所写的《农业》一章资料翔实,分析细密,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对于自己的美国同行,几位评论家则评价不一。他们认为《主导思想》(卜德)、《早期儒家》(JohnK.Shryock)、《道教》(德效骞)、现代教育(卜舫济)、《世界大家庭中的中国》(饶大卫)等几章内容充实,堪称精彩;而《战争年代的文学与艺术》(DrydenL.Phelps)、《美国文学中的中国》(AliceT.Hobart)等几章比较单薄,差强人意。他们还认为《书法、诗歌、绘画》一章论题不集中,每个论题都是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这章的作者FlorenceW.Ayscough不是别人,正是编者宓亨利已故的夫人(1942年去世),这一章是她生前的一篇旧作,不同于其他章节都是新作的情况。如果是中国的书评者,很可能会照顾编者的情面,对此存而不论,但几位美国评论者却很较真。这其实是对的,学术就是学术。
几位评论者最为欣赏的是魏特夫撰写的《中国社会与外族入侵》一章。当时西方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中原后迅速被汉化。魏特夫通过重点研究辽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后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只有在征服王朝的权力结构瓦解后,完全的文化融合才有可能”(英文版114页)。魏特夫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熏陶,是最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之一。1937年移民美国后,他把这套理论和方法也带到了英语世界。
多人合作写书,除了水平不一之外,语言表述、行文风格、名词术语的使用等都有差异,这对编者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中国》的篇幅长达573页。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EarlH.Pritchard在读完全书后这样写道:“13个章节是中国人写的,21个章节由西方人执笔,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全书的风格做到了基本一致,清晰、简明的语言一以贯之,有关人物、地点、年代等的信息没有出现前后龃龉的情况,各章之间重复的地方也只有很少几处。”总体来说,普里查德认为该书取得了“编辑上的胜利”(editorialtriumph),宓亨利为此类集体著作的统稿树立了典范。
普里查德的评论是中肯的,但他只注意到了“统一”的方面,没有谈到“不统一”的地方。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对此宓亨利采取了尊重作者、完全保留的态度。比如关于佛教,邓嗣禹认为它“逐渐给予一种刺激,并丰富了中国文化”(81页);蒋彝认为大量中国艺术家“吸收了佛教,从中获取了灵感”(335页);何乐益认为“寺庙给被生活所迫的农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安全”(238页);这些都是正面的评价,但胡适却表示反对,他在自己的章节中说:“中古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从宗教狂热中解放出来,在我看来,中国的理性和人本主义被印度破坏了”(227页)。此外关于孔子的评价,关于科举考试的作用,学者们在不同章节中的表述也有不小的差异。如果这些差异还只是在个别观点的层面上,那么全面的对立则表现在关于民国的两章,著名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亲国民党的两位美国政治学教授Linebarger和Hosack则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看作是对蒋介石政权的威胁。
如果《中国》出自一人之手,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因为是多人合写,这样的矛盾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可能是一种优势——使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不轻易被一种意见所左右。
在《中国》之前,美国出版过多种类似的综合性著作,最有影响的是卫三畏1848年的《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和赖德烈1934年的《中国历史与文化》(TheChinese:TheirHistoryandCul⁃ture),都是个人著作。以一人之力来书写整个中国,虽然勇气可嘉,但难免浮泛。卫三畏在1883年修订版《中国总论》的“前言”中说:“我相信以后的学者不会再尝试写这样一部概论式的作品,而是会像李希霍芬(FerdinandP.W.Rich⁃thofen)、亨利·玉尔(HenryYule)、理雅各(JamesLegge)等那样专注于一、两个相关的领域。”确实,学术的发展必然走向专业化和精密化。卫三畏提到的三位学者都来自欧洲,在19世纪的美国还没有这样的人物。“专注于一、两个相关的领域”的美国汉学家要到1930年代才被培养出来,他们开始取代业余从事研究的传教士成为中国学的主导力量,并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这就为合作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条件。在《中国》之前,第一个成功的范例是出版于1943—1944年的《清代名人传略》(TheEminentChineseoftheCh’ingDynasty,1644—1912),该书收录清代近三百年间约八百位著名人物的传略,由学者们分头撰写,然后汇集成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书的主编是美国人恒慕义(ArthurW.Hum-mel,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不少美国学者也参与了,但大部分内容是由中国学者(特别是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帮助完成的。《中国》一书虽然也邀请中国学者加盟,但至少从章节数量上来看,美国学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是又一次成功的集体合作,也集中展示了美国汉学的新进展。日后成为美国中国学领袖的费正清一方面为取得的成绩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在书评最后一部分指出,《中国》一书体现的主要还是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明显不足,即使是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也基本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因此他呼吁“社会科学家应该更加关注中国”(greaterattentiontoChi⁃na on the part ofsocial scien⁃tists)。费正清写这篇书评时刚回到哈佛大学(二战期间他被借调到美国政府工作),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他以哈佛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和运用,具体到中国研究,就是要将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关于如何开创汉学研究的美国模式,费正清后来曾有一系列论述,早已为学界所知,但他这篇为《中国》所写的短评却从未有人关注,其中已经包含了他日后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的萌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