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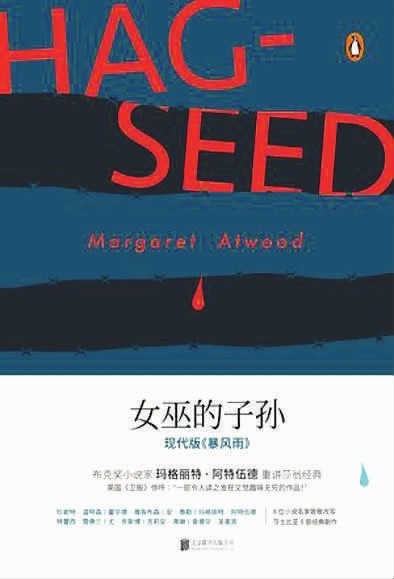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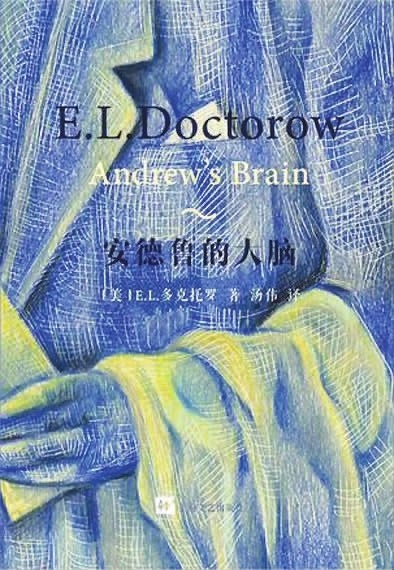
评论界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19世纪以后,杰出作家显得越来越稀少。一些作家聊起让自己手不释卷的书目,也总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梭罗这些经典大家。仿佛,当代文坛热闹归热闹,可堪一读的作品却很少。当代文学作品真的贫乏了吗?
这是个不好仓促下结论的问题。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虽不讳言她的日常读物以狄更斯和笛卡尔为主,但她也指出:现在被公认为杰出作家的梅尔维尔、迪金森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才被真正发现。
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现实总是平庸的大多数包围着杰出的少数派,最好的作品并不是人为选择的,而是岁月从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淘洗所得。所以,当我们在上海书展正面遭遇大量文学类新作时,所面临的真正困惑在于,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也许一时一刻是难以辨识、难以定论的。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把眼光投向一些既不够流行,也不能制造刺激的感官冲击的作品,聆听丰富多元的声音。
这里是今年上海书展上一些文学类翻译新书。在这个时有偏见、盲目和狭隘制造创伤的世界里,文学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是不妥协地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将让人们从自我封闭、不加反思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认识到自 己与他人是相互关联的,认同世界是复杂且充满灰色地带的同时,仍然为有迹可循的真相奋斗和努力。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暴力冲突的新闻,让人想起去年秋天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在 《纽约书评》 发表的散文 《恐惧》,她在文章里写道:“‘恐惧’是当下美国文化中最严重的问题,酿造美国日趋分裂的局面。‘恐惧’使得人们不再按照应当遵循的准则行事,逐渐远离最好的自我。”一如她在小说里反复探索的问题:人如何战胜不确定的恐惧,踏实地活着。
玛丽莲·罗宾逊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尽管她的长篇小说只有四部:《管家》 《基列家书》 《家》 和 《里拉》。《管家》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本人非常珍视的一部作品,奠定了她后来的写作基调和主题。小说以一个偏远、潮湿的湖边小镇为背景,娓娓道出三代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露丝和露西尔是一对孤女,母亲死后,她们由外婆和两位姑婆的照看,直到姨妈西尔维接管她们。她带着她们流浪,居无定所,后来,妹妹露西尔回归日常秩序,姐姐露丝继续四海为家,“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夜中独自跳舞。”在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正面出现过,只有女人和女孩是鲜活生动的,女性的沉静、古怪、内敛、冷淡等等特质,代代相传,一并传递且不断累积的,还有对逝去亲人的回忆。罗宾逊笔下的女性,以各种各样的不圆满打破了人类的常态,她用诗意的韵文写下生命的无常,关注那些在传统之外的人们———选择漂泊未必是寻求解放的女性的理想出路,但只有摆脱了“托付男性”的情结,女人才有可能成为自由完整的人。
《管家》 的结尾,姐姐露丝忍不住想象妹妹露西尔可能的生活场景,暗生向往。一切的自我选择真的可以甘之如饴么? 谁是真正离开的,谁被困在原点? 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 里,一对姐妹花的命运殊途是另一幅浓墨重彩的人生画卷。
经过 《我的天才女友》 和 《新名字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文版出到了第三部 《离开的,留下的》,“费兰特”这个笔名背后作家的真实身份依然是谜,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她对女性情谊极度诚实、尖锐、毫不粉饰的书写。埃莱娜和莉拉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贯穿了意大利战后动荡的岁月,这两个生长于那不勒斯贫民区的女孩,为了冲破逼仄命运的封锁而挣扎,她们数十年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是替对方度过她难以企及的人生。她们一起构成一个神奇的、自给自足的整体,互相补足对方的缺憾,也互为彼此最大的阴影。无论是生活还是小说,一段友谊里,更强大、性格更丰富的那个人会让软弱的那个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但是在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埃莱娜,从自身的从属位置中获得了某种才智,那让莉拉失去了方向。费兰特以史诗格局展开的,就是这个难以描述的过程———一个人不断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她们帮助彼此,也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
对于作家而言,很多时候他们也会不可避免地从另一个作家身上汲取情感、知识和力量,那些经受了时间锤炼的伟大作家,其实注定要被后辈同行“洗劫”。三年前,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受邀参与了一个名为“改写莎士比亚”的文学项目,以小说的形式重构莎士比亚的戏剧。阿特伍德的新作 《女巫的子孙》 就是这次命题作文的作品,她把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作 《暴风雨》 切换到当代加拿大,原著中的米兰公爵化身戏剧导演,落魄后成为监狱教导员,和监狱里的三教九流一起排练莎士比亚,莎剧成为这些人命运的复调。
阿特伍德说,她选择重写 《暴风雨》,因为“这部戏剧包含了许多未解的谜题,复杂的人物,它的魅力一部分就存在于读者试图解答这些谜题,挖掘人物复杂性的这些挑战之中。”开始写作前,她重读了两遍剧本,一度陷入恐慌和思绪混乱:一个魔法师跟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一起在孤岛上被遗弃了12年,这种事在现代哪有什么翻版呀? 她第三次重读剧本时,改从结尾往前读,被普洛斯派罗的最后一句话击中:“还我自由。”于是阿特伍德开始计算这个剧本里出现过的“牢笼”,剧中出现了九个囚笼,其中第九个,也是最大的囚笼就是 《暴风雨》 这部剧本身,囚徒是普洛斯彼罗———这是一部关于禁锢的戏,每一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禁锢的。于是,她决定把小说的背景安排在加拿大的一所监狱里,她笔下的男主角在挫败的生活中,把热情转向排演莎剧,他改编 《暴风雨》,席卷了他身边所有的人们,而那场演出也将成为他生命中所不能幸免的暴风雨。通过 《女巫的子孙》,阿特伍德抓住了莎剧 《暴风雨》 的精髓,也触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唯有创作,是抵抗命运的“魔法”。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写作之于很多作家,是通向内心的长路迢迢,也是释放那些难以释怀的经验。
理查德·弗兰纳根以父辈的经历为蓝本,历时12年完成了小说 《深入北方的小路》。他的父亲二战期间入伍,在太平洋战场被俘,是日军战俘营第355号战俘,扛过饥饿、殴打、热带疾病以及修建泰缅铁路的繁重工作,九死一生。泰缅铁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当年日本军方强迫6万盟军战俘和无数亚洲劳工,用18个月完工。疯狂赶工的后果是西方战俘死了1.2万,亚洲劳工死亡数在10万以上。这些数字背后的血泪磨难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恰是弗兰纳根在小说中做的:他试图想象父亲经受的苦难,也想象昔日作为施暴者的日本军官的心理。这个故事不是人类战胜困苦逆境的陈旧套路,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失败感———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生命的虚无感。战争和爱情这两个主题在小说里都有体现,但作者真正描写的是面对命运无情的本质,人类残酷的、但残忍中有时也具有美感的精神世界。弗兰纳根的人文修养极高,他独辟蹊径地处理了诗与冒险的关系。如果用“诗意”形容与战争有关的故事,似乎有些轻佻,但这本小说确实是诗的叙述,诗的表达,诗的隐喻,就连书名和每个章节名都来自俳句。“今世,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繁花。”书里引用的这句俳句,未尝不是对这部作品恰如其分的评价。
关于“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美国作家多克托罗有过一句颇有意思的抗辩,他说:“我抵制历史小说家这个标签,我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关于‘此刻’的。”两年前辞世的他,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安德鲁的大脑》 是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
多克托罗最负盛名的几部作品涵盖了美国100多年的近现代史:以南北战争时期为背景的 《大进军》,发生在20世纪初的 《拉格泰姆时代》,讲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 《世界博览会》 和 《鱼鹰湖》,关注1960年代的 《但以理书》,还有 《纽约兄弟》 串联起从一战、大萧条时期、二战,直到越战的40年历史。
在《安德鲁的大脑》 里,作家回到了字面意义上的“此刻”,小说以对话体展开,认知心理学家安德鲁和不具名人士在交谈中讨论人的认知、记忆,以及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创伤回忆。但这不是一部心理小说,主角安德鲁纠结于“大脑怎么衍生出意识”,因为他对过去怀有负罪感。
书中大篇幅地谈到“9·11”,源于多克托罗曾为摄影师大卫·芬的图片集 《哀悼911》 配文,借这本小说,他“复活”了那段让他难以释怀的经历。在他生前接受的最后几次采访中,他希望读者不要以“时代寓言”的偏见去看 《安德鲁的大脑》,不要试图寻找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我没有兴趣针对任何一个时政人物。如果足够幸运,50年后还会有人来读这部小说,那时应该没人会在意人物原型是谁,那样就能看得明白,我想讨论的是:人不该杀戮。”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曾经写到:“天堂不是仁慈的,思想的人类也不是。”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向他致敬的 《赫拉巴尔之书》 里,写的就是一群“思想的人类”的独白交响。这部小说有一个特别荒诞的情节框架:安娜怀孕了,但是她厌倦了和作家丈夫在一起的生活。上帝为了防止安娜堕胎,派天使下凡,但天使毫无用处,所以上帝只能亲自出马,去找赫拉巴尔聊天,去学萨克斯……笨拙地做一切能让安娜感受到“上帝之爱”的举动。小说的特别在于,作家放弃了对情节和细节的设计,将巨大的空间留给了倾诉、议论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神思飞扬,每一次倾诉、议论的声音源总是不确定的,倾诉中,情绪泛滥,裹挟了大量碎片般的现实生活的细节,同时敞开了和文学世界内在历史脉络的对话。
《赫拉巴尔之书》 之后,《一个女人》 是一次更大胆的文体实验。本书由97个小节组成,每个小节长短不一,长的数千字,短的只有一句话。97个小节采用了类似音乐中的“赋格”,不同声部交替吟咏同一个主题,每一节的开头都是“有一个女人”,紧接着是“她爱我”“她恨我”,小节之间“爱”“恨”交替。这些描写展现了参差多态的女性和男女关系,有爱的体验,两性的冲突,也有激情的游戏,以及自我意识的碎片。在这部“非典型形态”的小说里,艾斯特哈兹展现了他罕见的语言才能,将粗俗与高雅、直白与隐晦熔于一炉,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节奏。以这场语言狂欢的文本实验,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小说以及文学的真谛在于思考语言———对语言的关切是思考人和世界关系的立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