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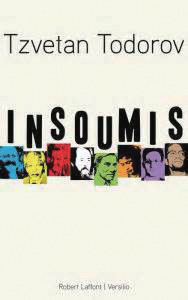
《不顺从的人》法文版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2017年2月7日患脑神经变性逝世,享年77岁。《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影视综艺》等法国媒体按他2016年秋发表的新著《不顺从的人》称他为一个“不顺从的人文主义者”,终生关注人的“独立自主”,不为“善”与“恶”的概念所拘,勇于摆脱窠臼,自由思索,不断探求文学相异性的路途。
茨维坦·托多洛夫曾以法国新文论弄潮儿的身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文坛崭露头角。他跟罗兰·巴特和钱拉·热奈特一道大论是弘,形成“结构主义分析”深层理论的“三位一体”,显赫一时。孰料,罗兰·巴特仙逝后,他突然于2007年发表《文学的危殆》,自相违背,给亲身参与的“新文论”贴上“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三段式标签,为结构主义在法国科研与教育界的专制敲响丧钟。对此,评论界所执各殊,卫道的雅克-彼埃尔·阿迈特斥责他身为符号学“非同小可的人物”、《诗学》丛刊上显赫的辩护士,居然“揭竿起义”,充当起“出殡哭丧妇”的角色,行为荒诞,是“言可非之事以为说”。
如今,托多洛夫已去,报界为斯人唱挽歌,认定他是个融入“自由社会”且有所创见的典范。他本为斯拉夫血统的保加利亚人,投入西方怀抱,成功转型为拉丁秀士,其幻术当属奥维德的稀奇变形神话。与他的同胞或曰先辈伊凡·伐佐夫、波特夫和瓦普察洛夫相映照,托多洛夫显然更倾向于在当代选取“适者生存”的法则,择良木而栖,以酬弘愿。
托多洛夫1939年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少年时代他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后又接触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对法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同时也读了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卡夫卡的作品,拓展视野。1956年,托多洛夫进入索非亚大学,以文学为志向,相信这一途径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世界,丰富生活”。他向往西方的自由,在他眼中,巴黎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天地,无与伦比,充分体现法兰西特征,令人憧憬”。
1963年,托多洛夫如愿抵达巴黎求学,于1967年进入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取得法国国籍,后当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艺术与语言中心主任,跟钱拉·热奈特共同创办《诗学》杂志,跻身六角国的文化精英界。他涉猎历史研究,加入列维·斯特劳斯的哲理与人类学阵营,陆续发表了40余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宣扬个体自治的理念,既反对专制极权的意识形态,又不赞成极端自由主义,尤其警惕革命乌托邦的诱惑。作品主要有引进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历史的伦理》《面对绝境,集中营里的精神生活》《普通生活,人的社会性考量》《恶名善诱》《艺术与生活,伦勃朗状况》和《民主的隐秘之敌》,尤其是《结构主义诗论》《散文诗学》《批评之批评》《象征主义与阐述》《对话本体论》和《奇幻文学》;后一部文论分析了对卡佐特、波托基、雅利耶·德·里拉唐、纳荷华和莫泊桑奇幻的感知,颇有新意,较早在法国文苑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他的学术著作迄今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
托多洛夫曾数度抽闲返回故国“旅游”,1981年发表《保加利亚游记》,对至今“还在受苦受难”的同胞流露怜悯,哀叹:“我在法国受了33年的陶冶,精神面貌全非,令他们对我的人格格外陌生。各自的生活使然, 我只得佯作不见”。这位在西方发迹的贵人还乡,乍陷始料不及的逆境,难免显出一副窘态。抑或,此翁保有些许“斯拉夫情结”,故不完全像一般所称,变成一个在价值观上“归顺西方”的人。他毕竟还“合而不同”,甚至敢抒己见。
更为明显的是,他忤逆当年法国主导潮流,公开抨击1999年北约干涉南斯拉夫,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的侵略行径。对此,托多洛夫跟雷吉斯·德伯雷一样,不怕被气焰嚣张的贝尔纳-亨利·雷维之流孤立,鼓起勇气质疑北约进行的是一场“人道战争”。托多洛夫声称:“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更引起我反感的,是它竟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一位反极权主义猛士之笔。他奢谈‘道德战争’和‘人道炸弹’,岂非奇谈怪论!即使存在正义战争,炸弹总是残忍的。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制止一场种族大屠杀的战争是正当的。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并非科索沃的情况。不应该再相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酿成悲剧。应该干预,但不能自认为有权支配全世界的命运。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权国度’,尽管我们对这个辞令不敢恭维。以行善名义干涉,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19世纪的殖民征服也正是打着维护人权幌子干下的勾当。”
托多洛夫进一步指出:“北约在南斯拉夫发动的战争,向我揭示一种新迹象:民主国家也可能出现近似极权国家的其他偏离举动……我对民主的一些演化更抱怀疑态度。原则上,民主并非一种拯救理论,不能允诺地上天堂的降临。民主制无意引导一国臣民走向完善,也可能傲慢过激,尤其在得势之时”。他具体举例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恶果至今还在影响着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西方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战争几乎自此不断,从南斯拉夫到乌克兰,从阿富汗到叙利亚,从马里到科特迪瓦。法国和联合王国两个老殖民帝国运动其中。在法国,新保守主义主张被左右两翼一同接受。”
十分明显,托多洛夫将矛头直指弗朗索瓦·勒维尔、贝纳尔·库什奈和贝纳尔-亨利·雷维一伙“人权斗士”倡导、在法国舆论界占据上风的“人道干预”论,反对法国冲在美国前面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托多洛夫的同行,意大利符号学大师翁贝托·艾柯生前曾告诫欧洲知识分子,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已无济于事时,最好保持沉默”。然而,托多洛夫并不认可艾柯研究出的语言规范“符号”,不那么甘于寂寞。他不但发表《文学的危殆》,在文论战线“起义”,而且对他自己和妻子南茜·哈斯顿一同自愿融入的法国社会制度不乏微词。菲利普·杜鲁在《解放报》上撰文,称他是“一个总想说‘不’,要对潜在危险发出警示的当代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廉洁》杂志发表专论,述及逝者生前最后10年对“法国民主”论题的深刻思考。托多洛夫说道:“今天在法国,议会服务于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立法与行政之间既无分离,也不平衡。政治干预,法官服从政府决定,威胁到了司法独立(预审法官被取消)。一出影响大的社会事件,就炒作公众情绪,要求修正法律,向强硬方向变动。这类由一种权力蚕食其他一切的现象,终归还算传统,近年来又增加了一切政治权力都屈从于经济势力的危险”。他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提出“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今天影响着广大民众,其信徒建立起强效网络则更为可怕。这一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形成对立,严重妨碍自由企业,如同在向着古拉格迈步。人们将之约简为经济需要,被看成自足个体。公共的、甚至社会的财产都被当作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着极端自由的搏斗。现时极右翼也正是如此这般反对移民和穆斯林。无限制的经济自由要求全面的自由表达,尤其是肆意排外。当然,自由是宝贵的价值,但在掌权人手里就变成了压迫的渊薮。狐狸自由进出鸡舍,意味着母鸡的死亡。多数剥削或歧视少数,绝没有什么光彩”。
他接着联系法国当前社会实际,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人们感到,政治阶级的成员均系在宫廷培养,留在同一些圈子和派别中,不论在哪个党里,皆沆瀣一气,只是不能跟国民对话。黎民百姓听不懂他们晦涩的辞令,全盘唾弃。种族内婚繁衍,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木头语言继续流传下去,民粹偏离必将日益严重”。托多洛夫针砭法国当今社会的弊病,将其根源归咎于制度。他强调:“视极权主义为邪恶帝国,并不意味着民主就是善的王国。民主披上良善外衣,祸患则潜伏其中”。因为,如果视民主为“善”,那么善的诱惑是危险的,托多洛夫从而提出要“抵制善的诱惑”:“诚实地说,民主本身会发生偏离,导致悲剧”。
他坦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柏林墙倒塌后,实施新的进攻型政策。他们所声称的目标是“促进重大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但具体可见的惟一结局,却是这些国家强化了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如此行事,他们危险地接近了耻辱的极权主义功利实践。“反人类的滔天罪恶都是以道德和人道的名义犯下的”。托多洛夫批评美国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5年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重申“不道德的深重罪孽总打着道德的幌子,故而是邪恶的道德。人们跟与吾等有共同世界观者讲道德,而和他人则不然。我赞同德勒兹和拉康给邪恶下的定义,即生活在没有他者境界的人属于反常”。他断言,使用暴力强行施善的意志,乃是极权主义祸患的源泉。正如俄罗斯作家、极权主义受害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二战小说《生存与命运》中所云:“黎明时分,老幼丧生,血流遍地”。由此,他主张关心个人福祉,对把“为了人类”工具化深恶痛绝。
基于这一原则,他觉得法国避而不谈自己昔日的殖民主义历史十分不正常,向报界坦率表示:“我无意给法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描绘一个单色图像。可是,许多文献流露出对当年‘土著’的一种极度蔑视。然而,法国的殖民冒险并不只涉及一代人,而是绵延了150年,在人们的心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之保持沉默,似乎是民族意识上的一个空白,应该将之列进中学的必修课程。”这里,托多洛夫对法国社会的敏感问题直言不讳,表露他性情耿直。
说到性情,托多洛夫是一个为人谦和的君子。2000年,女记者卡特琳那·鲍特万在对他的专访辑录里写道:“托多洛夫是一个思想温和的智者,具有惊人的毅力。清廉自持,非同一般”。他的同僚、现任《书林》杂志主编奥列维·波斯泰尔-维奈回忆:“他乐意到编辑部,每两周来开一次编辑会议,不引人注目地找个位置坐下,参加辩论时从不提高声调,丝毫没有过激情绪”。
托多洛夫一生为人朴实无华,虽受种种非难,但总靠自身的语言才华和勤奋写作,在瓦斧雷鸣的时代,登上了法国学术研究的顶峰,却仿效罗曼·嘉里的谦卑,坚持不懈地寻求人与人的相逢对话,消除偏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留下这般清泠泠的文学潮音,让友人追怀。他的女儿在巴黎向法新社宣布,今年3月1日,弗拉玛里翁书局将要出版故人的遗作《艺术家的成就》(Le Triomphe de l’artiste),《世界报》称之为“文学的尾声”,不免令读者翘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