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的文化自信
http://www.newdu.com 2025/12/18 02:12:18 文学报 袁筱一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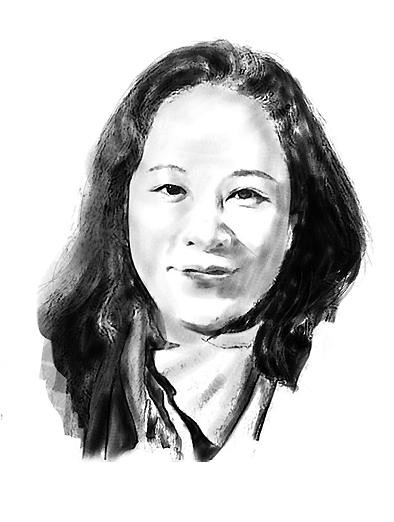 翻译家,译有《生活在别处》《法兰西组曲》《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著有随笔集《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最难的事》等。 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点任何一个合格的传播主体都需要的耐心、理性与勇气。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翻译研究的热点也不可避免地从外国文学的翻译转向了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但仍然讨论的是究竟应该怎样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这也还是一个应该采取直译立场还是意译立场的老问题。而且大致也还是说,直译中国文化会遭到排斥,效果不好,意译中国文化又多少觉得有些牺牲汉语里原本的优势,出去倒是出去了,可出去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只是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多少有些焦虑的心态,倒更容易陷入翻译本身固有的悖论。其实如果追溯中国翻译的历史,均肇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翻译和西方思潮的翻译也都是从改写开始的。用现在的翻译观来看,自然是有很多“错误”,而且均属硬伤:因为理解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审美趣味的缘故。只是十分有趣的是,语言比较的框架始终是翻译的一个梗,但却未必是传播的梗。传播史总是与翻译的纠结背道而驰,而且仿佛越是遭到翻译的责难,越有此后历经抵抗和艰险,成功传播的可能。有时候“异”的因素就这么活生生地闯入了目的语的语言,语言的或是文化的;有时候却又还没能安顿下来,就遭到了目的语的排斥。接受总是有点不顾翻译规律的样子,它要求平顺和简单,看不出曾经抵抗过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接受史一旦被这样改写式的翻译炸开了缺口,就会在其未来的漫长旅途中,开出异域的花朵。这朵花早已不是原来的,是在新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的新生命。 无论是中国文化在国外,还是外国文化在中国,这种翻译溯源与接受面向的悖论其实都存在。而溯源与转向传统的根植也的确是文化两个本质性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文化往往会特别彰显其中的一个特征,而遮蔽了它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我们只是在语言层面的结果——亦即译本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悖论是无解的。 然而我们不难观察到,总是会有少数经典文本以其特殊的接受进程告诉我们,止于文本结果的语言转换远非翻译的使命。由翻译行为所构成的原本与译本的关系也远非互相对立、彼此消解,尤其是译本遭受原本消解的关系。只是大量的翻译实践止步于第一阶段的译本生产,所以遮蔽了人类思想、文明、文化欲求翻译的实质。诚如沃尔特·本雅明写于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译者的任务》所言,可译性是被包含在原文之中,而非取决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远近。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逻辑继续下去说,原本(对于文学来说,往往是文本意义上的原本;对于思想来说,也可以是作为体系的多文本构成的整体)倘若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从整体意义上成为新的生产的起点,是因为它包含了必然得到译介、阐释、传播与建构的因素。 看似孤立的经典文本的翻译、阐释与生成因而早已超越了文本的范畴,因而即便是在翻译史的讨论中,我们往往会使用到生成这样的字眼来定义这个阐释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所谓原本的问题早就已经遭到了消解,也走完了自身作为历史的生命所必需经历的出生、成熟、衰老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译本有时会覆盖真正的“源”文本,成为新的原本。在西方,或许《圣经》的翻译与传播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而反过来,中国亦有相当多的典籍会在进入异域之后,不断得到新的阐释,甚至克服了相应的抵抗,成为异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是作为原本,在新的语境与新的接受环境中,遭遇抵抗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抵抗愈烈,也就意味着欲求愈强,意味着未来在异域开出的花朵有可能愈加艳丽。二是愈是具有经典与再生意义的原本,接受愈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其蕴含的“真”将需要借助一而再、再而三的呈现,滤去其中不可避免的误解,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真”的整体,直至反过来证明了原本的价值。而这,也正是经典文本在传播史意义上的生命里所在。 在此参照之下,我们完全不应该担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不再作为接受主体,而只是作为完全的传播主体而存在。恰恰相反,越自信往往越开放,越开放往往也越自信。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点任何一个合格的传播主体都需要的耐心、理性与勇气。我们理应对早已因为开放而不断融入“异”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传统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翻译很美,普鲁斯特很长
- 下一篇:阐释与补偿:《红楼梦》英译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