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克·费里 资料图
“当我们看到前总理突然为儿子换了住房,因为对巴黎城区公寓房持有权力,我不会向他投掷石块,而只是直接问他:那其他人呢?”
说这句话的是法国前教育部长、哲学家吕克·费里。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那场“五月风暴”深深影响了费里的一生。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在其《1968年:撞击世界之年》中,将“五月风暴”描述为一场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革命而革命的极端事件。法国社会学泰斗雷蒙·阿隆称其为一出无聊的“心理闹剧”: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抗议。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则认为,这场年轻人“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
当今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实实在在源自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现象,并非像“五月风暴”那样属于“无病呻吟”。然而,在费里看来,无论是“五月风暴”还是反对全球化,两者都具有某种共性:都是现代性自身开出的“恶之花”。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一旦推到极端,不受到某些原则的约束,就会释放出各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信念,从而俘获对现状失望的人的心灵,成为他们反抗现实的思想武器。
费里深知现代人道主义(他避免使用“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谱系的两端分别连着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困境,但与后现代主义者和神学家不同,他既不愿意诉诸解构的方法,让现代社会成为虚无主义所主宰的世界,也不愿意退回到宗教信仰,让历史上曾引发过无数暴力流血事件的绝对信念在现代社会引起新的压抑和冲突。
面对现代性困境,费里没有否认个体自由的意义,也没有跳出现代性本身的框架,而是试图在框架内找到能够驾驭“危险的自由”的原则。在《论爱》这本新书中,费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生活意义原则,也是他所谓的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的核心原则——爱。
自由之爱的重要意义
费里的“爱”与基督教的“爱”在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叠,但在根本上两者的旨趣又完全不同。费里想要的是哲学的爱,而不是信仰的爱。自尼采以降,现代哲学越来越专业化,试图获得与科学齐平的学科地位。而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大量探讨的则是生命意义和伦理规范,它们后来都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养料。费里并不完全拒斥哲学研究的专业化,但他认为要解决现代性困境,就必须把焦点重新放在探究人的意义原则的哲学上,而这种“哲学是没有上帝的关于拯救的学说,是对生活意义的探求,这种探求……凭借理性的唯一明晰性,而不求助于永恒不朽。这种追求主张世俗精神。从定义上讲潜入我们的所有机制中的爱,将在协调一致的哲学体系内部,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把我们的每一种活动和某种意义原则联系起来”。
不寻求超越于人的来自至高力量的爱,就把人放在了自由平等的主体位置上,而这正是第一次人道主义革命——也即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积极成果,人类社会由此第一次摆脱了超越性力量的桎梏,开始发现和欣赏自身的可能性。正如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费里的论证正是从“爱”最狭义的内涵开始的。他简要回顾了人类的爱情婚恋史,发现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社会才逐渐从包办婚姻或门第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在此之前,人们很难想象两个异教徒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很难想象贵族和平民可以自由婚娶。基于情欲的婚恋是危险的,蒙田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娶因情欲、色情而爱上的女人,意味着绝对的灾难!但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后,个人被看作自由平等的主体。反映在爱的领域,也就让两情相悦第一次成为了人类爱情和婚姻的基础,纯粹的爱情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个人全面掌管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摆脱了被父母决定、被身份决定、被宗教教义决定的爱情生活。
虽然世俗的爱情和婚姻更加脆弱,但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对婚姻的掌控,人们不需要回到天主教和基督教对婚姻的教义约束,通过将婚姻神圣化来对抗离婚的世俗诱惑,人们可以将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从感性的情欲上升为理性的关爱和家庭的责任,斩断情欲与婚姻生活的狭隘关联。情欲只是婚姻的基础,但不是婚姻生活的全部倚靠,包容、关爱和责任仍是费里所谓的爱的原则的应有之义,是自由个体在自由婚姻中应有的自我修炼,只不过这种修炼并不来自于外在的要求和强迫,而来自于个人对于婚姻生活本质的内在反思。
在费里看来,自由爱情和婚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既肯定了个人的自主性,尊重了个人的选择,又让基于自愿选择的爱情的结晶——子女后代——在父母眼里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今天,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无私的爱,在历史上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在中世纪,孩子往往成为非自愿婚姻的牺牲品——孩子被父母遗弃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现代社会,即便父母离了婚,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将婚姻的怨气发泄到孩子身上。
毫无疑问,在现代人看来,孩子已经成为父母生命意义的延续,父母对孩子的爱超越了父母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某种程度上,这种爱具有永恒的超越性的意义,而这种超越性与超越于人的至高力量无关,与神圣无关,仍属于自由的个体在世俗社会对生命意义的更高追求。
总之,费里通过肯定自由爱情和婚姻,肯定了第一次人道主义革命(启蒙运动)。由此可知,费里并不是现代性的反对者。但费里很清楚,第一次人道主义革命并不彻底,自由被误读、被滥用。如果没有爱的原则作为约束,自由将走向爱的对立面,陷入现代性纷争的泥沼。因此,费里对爱的原则的阐释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私人爱情的范畴,爱的原则还必须能够解决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现代性问题。在费里看来,正是父母对后代的关爱以及由此对后代生活环境的关注,让人们的关注点从狭隘的私人领域转向了宽广的公共领域。而爱的原则既包括对个人和孩子的爱,也包括对他人的爱,这就是他所谓的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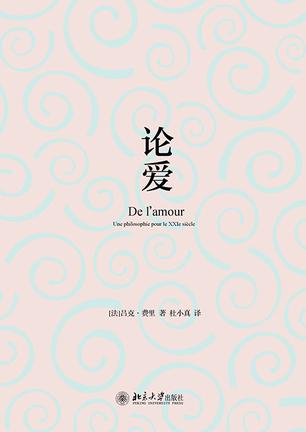
相对主义的幽灵
当父母审视孩子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他们会发现,第一次人道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人性自由,一方面确实为个人潜能的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为人类社会开启了价值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自由一旦没有了“锚”,过多的可能性和多元化也会带来价值的混乱。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极权主义就是自由社会价值混乱的结果。虽然费里承认,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有其积极意义,让个体之间呈现出更明显的相异性,进一步拓宽了个人潜能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费里却并不认为,所谓的后现代真正解构从而替代了现代性。现代性困境仍然摆在那里,解构只不过进一步加剧了已然十分混乱的价值体系。
既然在解构者看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打着国家、自由解放和革命旗号的极端运动当然也就有了正当性。费里对于这些运动深恶痛绝,与后现代主义者或宗教分子的看法不同,虽然他深知现代性的病症,但他决不会将人道主义解构为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决不认同试图退回到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怀旧病”。
明辨文明价值的高低,意味着费里明确肯定了现代社会的先进性及其崇尚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试图用这样的价值观将现代社会从后现代的解构和历史的怀旧中拯救出来。同样基于这种价值观,尽管费里认为不同文明的价值有高有低,但他决不同意为了同化低级文明而对其诉诸武力。费里的爱的原则始终以个体的生命和权利为根基,因此,他所崇尚的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并没有脱离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他反对为了某种极端意识形态、为了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私利而牺牲他人的生命和权利。因此,无论是对虚无主义还是极权主义,费里都极为警惕。
爱他人即是爱自己
爱的原则一旦从私人领域延伸到公共领域,意味着我们应该像爱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那样爱他人,而非仅仅停留于自爱,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或一己之念牺牲他人。费里的爱的原则之所以反复强调父母关爱后代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这种关爱,正是超越一己之私的起点,进而将关爱投射到更为广泛的他者,或者说,投射到公共领域,而这种投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同情心。同情心能够既让人对异质的他者保持宽容,也让人意识到,为他者争取权益就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
当费里说,他不会向前总理扔石块,而是会质问他,那其他人呢?他就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爱的原则何以能够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嫁接起来:爱决不仅仅是宽容,甚至是顺从,为自己和他人伸张公平正义也是爱的原则的应有之义。这就好比,爱孩子决不意味着宠爱和溺爱孩子,而是应该像费里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父母要对孩子的行为施加必要的戒律,老师要向孩子传授正确的知识。
费里认为,博爱和同情是爱的原则派生到了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爱的政治”。父母一旦关爱后代,意味着父母将不得不关心后代所生存的环境,比如,生态环保、医疗教育、财富分配、经济机会、权利保护等等,这就将他们对自身的关切延伸到了对社会和他者的关切。
在费里看来,爱的原则不仅是解决现代性病症的一剂良药,还为个人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原则:爱既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保障了个体的自由,繁荣了文化的多样性,又为个人生活找到了更广阔而深邃的意义,一种超越了自私自利、更有恒长价值的生活意义——为了后代,为了他人。即使每个人都面临死亡的结局,也无法抹掉此世为了爱的价值而奋斗的意义,这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作者也许已作古成灰,但小说的精神价值却能恒久光照后来者的心灵。费里相信,这些意义都不需要超越于人的至高力量来赋予,世俗社会完全可以有爱,或者毋宁说,爱本身就是世俗的。
诚然,基于博爱和同情的爱的原则为世俗的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广阔的视角,它要求人们从长远的、他者的角度来思考公共问题,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费里自己也谦逊地承认,第二次人道主义革命(爱的原则)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这种乌托邦可能是第一次没有被新的灾难充斥、膨胀。因为,(这种)乌托邦意欲实现的理想不是国家的、革命的理想……而是为了我们最爱的人们,即新生代的未来。”
的确,仅凭爱的原则无法根本解决现代性的困境。想想看:费里的绝对命令该如何适用于IS这样的极端信徒?他们根本不珍视自己的生命,甚至也不珍视孩子的生命!我们该如何说服被全球化的进程所伤害的美国底层白人,让他们明白,短视的孤立主义最终会损害他们的长远利益?我们该如何说服政府官员,如果不能让某些既得利益者经受短期的阵痛,长期来看,所有人都会因为改革的迟滞而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些问题远非爱的原则能够提供满意的答案,而突围的希望仍要寄托在现代社会的理性慎思和认知进步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