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江子 《回乡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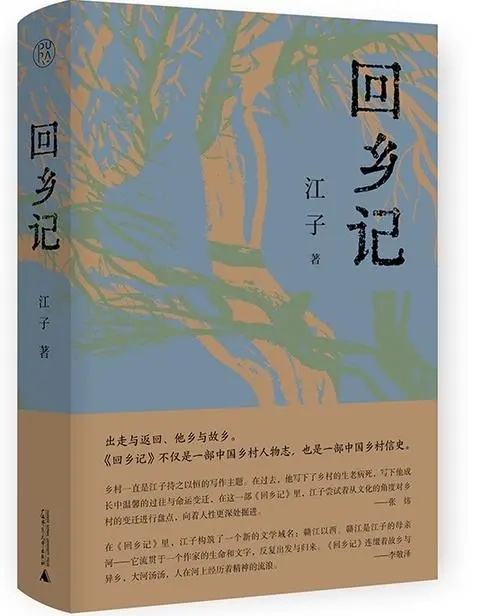 《回乡记》,江子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品,2021年12月 曾几何时,我们的乡村面目是清晰的。 我们说到乡村,就会很清晰地想起田地、民居、祠堂、族谱、祖坟、池塘、草木、动物,想起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在传统文化里,“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南帆语) 这一整套生活经验和审美体系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它宏大又微观,深刻又浅易。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塑造每个人的灵魂。因为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具有超常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过去对乡村的印象,它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是恒定的,几近于静止。相比城市的瞬息万变,它几乎不动。它是安详的,平静的。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再大的灾难都毁坏不了它。只要这套体系还在,即使遭到极大的破坏,它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重建——它有着极强的再生能力。 正因为乡村文化的独立和其强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它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古代的田园诗,当代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白鹿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都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乡村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地、祖坟、民居、祠堂、池塘、草木、动物、族谱都在,可作为主体的人大多不在了。他们都去了城市,务工、居住或就读。 我曾去过一个据说古代非常繁盛、出过很多官员的村庄。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人。接待我们的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个村庄户籍上有一千多人,可是今天全村的人有43人。 只有彻底的贫困人口和残障人员,以及老人,才把乡村当作最后的安息之地。 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田地的耕种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资本租赁。我一初中同学,就做我的村庄的田亩承包商。不过他不组织生产,他将承包到的田地转包给了他人。 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没有人养猪。牛也不视为必需,因为很少有人耕地了。即使耕地,也是用的铁家伙。 那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已经难以为继。比如婚宴已经找不齐一整套乐队了。新居上梁,已经找不到唱词的人了。春节舞狮舞龙的习俗,已经多年不见了。那套过去维系村庄秩序的伦理,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当然也有许多新的增长:比如宗祠,所有村庄的宗祠都重新修建过,并且都建得夸张而奢华,都是清朝宫廷风格;比如许多新房,都是出门打工或在外工作的人盖的,风格是对城市别墅的模仿;比如村口都有红色的砖塔,是过去中秋节时搭建瓦塔的风俗的戏仿…… 村庄面目日渐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不再清晰。过去的对乡村的认知,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这种变化让乡村书写变得无比困难。如此情况下如何书写乡村?在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乡村书写还有多少价值?该如何书写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土地、现代与传统,消逝与生长? 而我以为,当乡村面目日渐模糊,现代乡村写作反而有了新的可能。 这是我创作乡村主题散文集《回乡记》的原因。 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以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及所属的赣江以西区域为经,以从上世纪初到如今的百年时光为维,努力探寻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下人的命运变迁,文化的变迁,文明的遗存、消逝与增长,弱者对精神安放之地的寻找,道德的自我救赎可能,新的时代里异乡与故乡的关系…… 那也是诗人杨万里、《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陈诚、地理学家罗洪先等先贤的故乡,是一个具有霸蛮、血性而诗意的文化性格的乡土。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其实有着中国的典型意义。 我毫不讳言,作为一名纯种的乡村后裔,我怀着一颗为故乡的写史之心——当然也是当下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