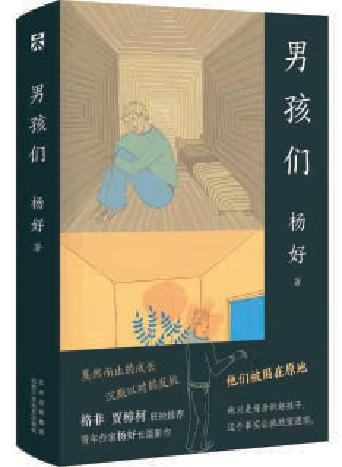 《男孩们》 杨好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其实在完成一个小说之后关于创作的讲述或是记录,来自写作者的说法已经变得没那么可靠了。黏在小说之前或之后的记述更像是一个产品说明书,说明能让一个写作者听起来诚恳坦白,而这似乎是我们现在的读者判断一部作品的前提——从作者开始,而不是从小说开始。 在我写完第一部《黑色小说》之后等待出版的那段时间里,《男孩们》的故事就已经开始冲进来了,最开始是一艘模型船和一个老人。我买了一块一米长的白色黑板,就是英语补习班上常用的那种。我在上面写下很多名字,然后再擦掉它们,就这样,这个故事始终没有进展。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试图处理这两者间存在的“远”和“近”的问题,这其中不断生出层层谜团和烟雾让我继续下去,也不断阻挠着我。时间、人物、杂念、不安与犹豫在不动笔的日子里就像无主的幽灵一样随时出现。更令我心慌的是,一个像我又不像我的声音整日整夜没有间断地在问我:你究竟为什么写作? 第一部作品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总带有自我救赎的意义,那种澎湃巨大的自我拯救足可以让作者暂时逍遥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之外。在这之后,写作者将面临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你是否要躲避它们?你是否要跳入其中?你是否要粉身碎骨或是与之同处——你该怎么做?接近这些漩涡意味着接近无数秘密,而试图揭开秘密的路途一定伴随着巨大的危险,比如巴别塔的轰塌、普罗米修斯周而复始的折磨,以及失去头颅永坠不甘的刑天。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秘密最终没有谜底。 这些危险的行程和勇敢的探险者几乎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懦夫。那段时间里,我处在完全沉默和失语的状态,几乎让自己消失和隐匿。如果答案的寻找一定是无果的,我们依然注定和现实相互依存,在消解中并行,在反抗中咀嚼一切。我们面对现实巨大的无助不仅仅来自我们要在其间生存,还来自未来和记忆造就的回响空间,使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迷失其中。于是不可逃避地,还要回到“自我”上面。让自己后退再后退的时候,“我”可以大到宇宙万物,也可以小到只有“我”。 我不再重复我的故事,也许只有这时才能讲述更多的“我”的故事。所以一切“远”和“近”也好,老人和模型船的意味也好,那些对知识的焦虑和对生命的功利也好,当剥去层层迷雾的时候,我才能开始成为一个写作者,只有赤裸生命。 大概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一下子被冠状病毒困在了家里,那块白色黑板就摆在客厅的正中间,在被困的几个月里一动不动地对着窗外空无一人的大街,那里有一个明朝建立的古观象台。我周围的一切,连同整个世界似乎都开始进入缓慢而滞后的行进中——时间前行,时代往后。 在一瞬之间,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谈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切似乎都比它们许诺应该成为的那样要艰难更多——在最难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还是个孩子就好了,但回过头才发现,孩子们听到的许诺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于是我终于看到速为和李问互相遥望,他们隔着没有边际的玻璃彼此呐喊,然后沉默。后来是陈先生和陈卫国,他们被看不见的隐线牵起,分不清楚哪些是大人,哪些是男孩。他们似乎都想成为大人,又似乎都想停留在孩童时代。再后来是罗老师和李老师,她们极度悲伤,不可避免地在原地等待。他们的故事在向前和往后之间踌躇,仿佛时间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天天向上”的承诺。 于是模型船和老人的故事最终成了整个《男孩们》故事的起源。虽然船和老人最终被置于后半段几处不太起眼的地方,但他们提供了我写下这个小说的动力和疑问。在这之前以及之后,世界抛给我们的信息远多于我们对自己信息的处理。李问和速为在小说里停滞了自己的成长,但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终将持续生长。我几次做梦的时候都好像在和他们说话,每次都是突然醒来,惴惴不安,我找不到道别的方式。我知道,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问和速为这两个男孩的命运已经与我的日常生活隐秘地纠缠在了一起,我知道他们的挣扎已经在我眼前挥之不去,但是他们背后隐藏的那只模型船和老人的身形,让一切回家的可能成为温暖的希望。这使我更加笃定,小说中是有魂魄的,对,故事是一部分,人物是另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这之外小说自我的延展。 我可以和他们道别了。有一句话我没有写出来,我希望李问和速为能回过头说一句“妈,我回来了”,我相信他们在心里一定默念了这句话。 最后他们没有离去,李问和速为,以及罗老师都是不可靠的、迷人的叙述者。他们和我们一样生长在一个年轻的时代,这给讲述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性和困难感——其中的社会信息和道德信息也许会被迅速从整个叙述中分离出来,冠以某种“现实”之名。 几乎不可避免地,写作无法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被传导,抵达的过程其实神秘而不为人知。如此,《男孩们》又是一个不只关于速为和李问的故事。说一个故事能把整个人或时代搞清楚,那是谵妄。但人的命运未曾因时代改变过,即使在虚拟世界里,生存、毁灭、邪恶、怜悯、欲望、抵抗、逃避、软弱,该在的都还在。 我突然想起写到李问在火车站台上重新变回婴儿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五十分。那是北京酷暑的七月,一抬眼,窗外满是紫红色的朝霞,炽烈而博大,仿佛那种不真实的光芒就要穿透所有将人笼罩。然后太阳一下子冲出云层,天亮透了。 某种意义上,文学依旧宽容得一视同仁——对善或恶,对真或假,而今天,它更加宽容了。 感谢看到这个作品的所有人。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