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 一 ◈ 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尤其是在扩展写作视野、建构文化维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的写作状况有必要改变。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自由的、丰富的,单一地沉迷于文化追索,会严重缩减散文本应有的精神空间——尤其是散文作为一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体这一传统,理应再次获得重视。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中,称这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字为“美文”,并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倡议。即便是在今天,“记述”和“艺术性”,依然是散文写作的理论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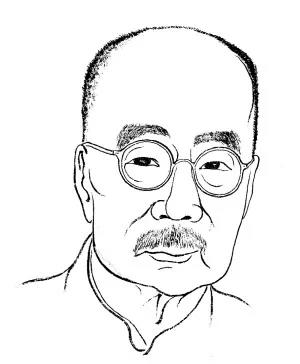 (周作人) 所谓记述,无非事关作家的所见所闻,这本来是一个写作常识,然而,当散文一再地被历史史料和文化感慨所捕获,带着个人发现的“记述”反而成了稀有的品质,因为在许多时候,看见一种眼前的事物,要比想像、沉思一种远方的事物困难得多——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说过类似的话。回想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像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像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写作者普遍戴着文化的面具,关心的多是宏阔、伟大、远方的事物,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呢,不仅进入不了作家的视野,甚至很少有人会对它们感兴趣。 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写作方向,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和盲目升华。但是,在这个背景里,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就是一种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将感官的知觉放大的写作。感官、记忆、在场感,作为写作的母体和源泉,在任何时候都是语言的质感、真实感和存在感的重要依据。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的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丧失了基本的联系。这个时候,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就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基本的写作才能,如今很可能将扮演着复活文学精神的重要使命。熟悉艺术史的人都记得,当古典现实主义绘画面临着因拘泥物质事象的真实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印象派绘画以模糊和虚化事物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世界真实的想像方式,从而复活了业已死寂的绘画精神;然而,当现代绘画越来越走向抽象、怪诞、不知所云,甚至落入了“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这话是菲利浦·拉夫在20世纪中叶对拙劣模仿卡夫卡而产生的假现代主义的批评。转引自[美]MORRIS DICKSTEIN:《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一书)的网罗的时候,或许,惟有求助于旧有的对事物的观察和摹写,才能复活真正的绘画精神。文学也是如此。今天,当丧失活力、抛弃感官的“纸上的文学”一统天下的时候,我尤为看重作家借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些感官以及记忆所发现的真实世界——当苍白的虚构遍地都是,惟有真实才能复活文学的心。否则,举目所见,都是空心的文学,虚假的文学,那将是何等的贫乏和荒凉。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套用在现有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可以说,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世界的分量还重。一个作家,如果相信内心的真实和具体的世界、事物密切相联的话,他必定会进入一种眼睛式、耳朵式的写作,因为在我们这个敌视具体事物的时代,有时惟有借助看、听、闻、嗅,才能反抗遮蔽,澄明真实。 我期待这一种真实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文学中重新复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推崇台湾作家陈冠学的散文《大地的事》。该书以《田园之秋》之名在台湾出版多年,并获得了文学界的崇高赞誉。尽管在此之前,国内散文理论权威、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教授,作为陈冠学散文的知音,曾在多部理论著作中对陈冠学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可对于内地读者而言,直到二〇〇六年才第一次读到,这实在算得上是一种迟到的阅读幸福。 《大地的事》是一部日记体散文,它以一个秋天的年轮,记述了台湾乡野景物的细致变迁,以及土地所蕴藏的美,用台湾知名评论家叶石涛先生的话说,“是一本难得的博物志”:“如同法布尔的十卷《昆虫记》,以锐利的观察力和富有创意的方法研究了昆虫的生态一样,陈冠学的这部作品也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台湾野生鸟类、野生植物、生态景观等的诸面貌的四季变迁,笔锋带有挚爱这块土地的一股热情。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注重风花雪月未见灵魂悸动的散文史中,独树一帜的极本土化的散文佳作。”(引自叶石涛为《大地的事》一书所写的“序”)《大地的事》的核心叙事,正是“田园”和“秋天”。关于田园,中国历代的文人都曾反复吟唱过,从陶渊明以降,田园叙事就成了失意文人最主要的写作路子。然而,在这些文人笔下,“田园”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假想,他们抒怀的重心,主要是为了寄托官场、仕途的落寞和不得意,那份怡然自得中,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做作和不甘心。在这种心境下,田园再美,大地再丰饶,他们也未必真有兴致去观察和享受——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竖起耳朵谛听来自京城的马蹄声,是否能为他传报复职或升迁的佳音。但长年隐居在台湾屏东乡下的陈冠学和他们不同,他回到故土、走向田园的心境,有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平静和自在,同时也带着一种面对人世的通达和智慧,所以,他的文字自然、纯净。“陈冠学返乡的原因称得上是没有被胁迫的出于本性的纯粹,没有丝毫的失意,如此也就决定了他返乡后的生活起居和创作的纯粹,陈冠学是纯粹的返乡实现了返乡后的纯粹,真是凭借这种纯粹,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是空前绝后。”(引自范培松为《大地的事》一书所写的“推荐序”)——“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一说,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但陈冠学作为当代文人中一个独异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少,我读《大地的事》,并不把陈冠学笔下的“田园”当作官场、商海或其他的嘈杂人世的对抗性存在,它就是“田园”,是大地的一部分,是花草树木,鸡鸭牛羊,是虫叫和鸟鸣,是无边无际的夜晚,是路边的一句问候,是田间的一次小憩……这个“田园”,不是象征,也不是隐喻,它就是田园本身,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人,在其中发生的事。因此,陈冠学用日记形式记下的田园和秋天,不乏琐碎,但我们读起来却兴致盎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从中读到一个真正的田园,能随着一个感官全面打开和解放的人,进入一个最为细微、有趣、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陈冠学和大地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秘密通道,正是这种生命的关系。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甚至舌头,都全面向大地敞开。他说,“真正美好的事物,看着,听着,闻着,要比实际的触着、吃着更合宜。”他不是靠知识来认识大地,也不是靠技术来征服大地,而是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谦卑的人,重新用自己的感官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他没有沦陷在世界的喧嚣之中,而是守住了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一份隐秘的欢乐。在他看来,喧嚣之外,世界别有洞天,神奇而平实。他因为接近大地,也就接近生命,接近事物和声音,接近心灵。陈冠学为我们重现了眼睛和耳朵这样一些感官所能洞察到的世界秘密,并告诉我们,人可以幸福、欢乐、简朴地居住其中。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更是观察者,谛听者,反刍记忆者——也是真正在大地上栖居的人。 ◈ 二 ◈ 陈冠学在田园之中,真是找到了一种难得的自在和闲心。而这,正是散文写作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凡是写得好的散文,往往平和随意,自由不拘,既一目了然,又让人回味无穷,《大地的事》就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比如,它写雨声,真是贴着自然写,让人回味无穷:“雨声之美,无如冬雨。冬雨细,打在屋瓦上几乎听不出声音,汇为檐滴,滴在阶石上,时而一声,最饶韵味。”它写秋虫的鸣叫,节奏分明,一咏三叹:“行到庭中,站立了一会儿,正要转身入内,忽听见土蜢的鸣声,像发条极松了一般的弱,可听出擦翅的每一片段单音。心里不由受到一震,全身也受到一震,好久没听到这亲密的声音了。正待要多听一会儿,鸣声竭了,就像发条全松了一般,前后计算起来,似乎还不足十秒钟。又站了一会儿,等待第二声,竟就没有了。这是老友最后的道别,真真是向我说一声珍重再见,不免一阵悲思袭上心头……”在作者笔下,各样的景色和生物,都是活的,有感情的,并和人心相通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面对这样的散文,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不过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心的读者,慢慢体会作者笔下的文字味道,此时而若有人硬要跳将出来,喋喋不休地在那概括、分析、阐释、指手画脚,不仅不能帮助人更好地享受这样的散文,反而容易破坏这类散文的文气和境界。 我读周作人的散文时就常有这种感觉。他当年给《亦报》《大报》写的随笔小品,篇幅都很短小,每篇也就五六百字吧,虽然也有“文思枯窘”、“不是乏味便多生凑”(周作人自语)的时候,但绝大多数篇章,应该说,周作人都写得自然从容,情趣盎然,达到了散文随笔这一文体的极高水准。对于这些文字,周作人自道:“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他还自定了两个写作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特点都准确地说出来了,加上他的文字很多都并不难读,这时,如果批评家硬要用微言大义去阐释周作人的散文,恐怕纯属多此一举。 有一种散文是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的,它并不适合阐释。比如《大地的事》,比如周作人的散文。我们都知道它好,但很难说清楚它好在哪里。不是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是闲适的吗?但周作人自己却说:“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貌似闲适实为苦涩,这可能才是周作人散文的真谛。一九二八年,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作跋时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周作人一再强调闲适里也有反抗这一点,并不是要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情形开脱,而是不愿让自己以及自己的追随者(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文字混同于“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的行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理解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人可谓大有人在。 要在周作人这种“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散文境界里读出涩味和反抗来,仅靠批评家的阐释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读者要有心境去揣摩,回味,响应。没有合适的心境,那是不能读这种散文的;即使读了,也可能会读出另外一个模样。因此,我认为,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这种散文,用王统照的话说,“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使人阅之自生美感”。(王统照:《纯散文》,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6月21日)——“阅之自生美感”,阐释便显得多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专供闲读的闲笔了。这样的散文会被忽视数十年之久,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周作人自身的历史污点这些原因之外,实在是与他的散文气质有关的。——在漫长的狂飙突进的大变革时代,谁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些闲笔文字呢?所以,只有等到精神的弦放松了,生活的自由和趣味慢慢得到尊重了,人们才会重新想起,现代汉语散文中,原来也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这一脉文字的。  (王统照) 相比之下,读者和批评家的目光,在大多数时候是集中在那些可阐释的散文上。比如鲁迅的散文,无论是他的《野草》,还是杂文随笔,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你可以在思想上、存在意义上,作很多的发挥。他的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枣树”(《秋夜》),我们就可从中读出无穷的孤独和意味来;他的一篇《女吊》,篇幅并不长,里面的灰暗和绝望却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像鲁迅这种思想个性鲜明、语言充满隐喻的散文,确实是适合阐释的(包括错误的阐释);或者说,他的许多散文,只有被充分阐释之后,才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以致鲁迅的这种散文传统,在当代已被简化为意义型的写作,许多的散文家,动辄也用起“墙”、“夜”、“死火”之类的象喻,像鲁迅那样“彷徨于无地”,“彷徨于明暗之间”起来;还有的人,以鲁迅为样本,写杂文和短论,也名之为“匕首”和“投枪”,扮演着“战士”的角色,但惟独容不得别人批评鲁迅——他们以为鲁迅是害怕别人批评的,这简直是对鲁迅精神最大的亵渎,它令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的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散文的写作伦理若只有关乎革命、意义一类的文字,就显然过于单调了。散文的魅力和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文体的丰富(叶圣陶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和内容的广阔(林语堂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它的本质应该是最自由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规定它应具有怎样的话语品格。因此,我喜欢鲁迅的尖锐与沉重,但我也重视轻松、有趣的闲笔文字,我觉得从这里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心性。试想,如果《鲁迅全集》没有《朝花夕拾》里那些涉笔成趣的篇章,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岂不是要比现在坚硬许多? 但闲笔式的散文确实是拒绝阐释的,你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恰当地贴近它。所以,多数聪明的批评家都对这类文字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鲁迅、朱自清,或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事关一些大的精神话题(如余秋雨之于文化关怀,王小波之于自由主义,张承志之于精神信仰,韩少功之于怀疑主义,刘亮程之于乡村哲学,等等),这样,批评家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可另外一种散文呢,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废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比如《大地的事》,他们的文字多为大白话,在这样的文字里,你总结不出大的散文话题,但作者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讲究等秘密却蕴含在一字一句里了。汪曾祺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表明,有一类散文所深入的是个人情趣和个人琐事的世界之中,它不像那些革命性散文或思想性散文那样,一眼就能让批评家识别出作者在散文里的话语追求——许多的散文好像是没有多大追求的,它们仅仅是为了呈现个体的状态,个体那微不足道的情趣。汪曾祺自己的散文就是这样。事无论大小,情无论深浅,在他的散文里都慢慢道来,不动声色,文辞朴白,却韵味悠长,那种闲心和风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 面对这样的散文,我常常想,批评家还有什么用?他还能找出怎样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这样的散文?没有。因为一切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面对这样的散文,惟一需要的是阅读,再阅读,并用心来享受它。这种散文在当代显然已经越来越多。 因此,批评家们在研究散文的过程中,不仅要懂得阐释,有时也需要学会放弃——放下阐释的架子,重新做一个散文读者。此刻,你不是批评家,不是作家,甚至你也不是散文家,你就是一个读者。试问,我们多少时候有闲心去做一个纯粹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散文界实在是“批评家”太多,“读者”太少了;“阐释”散文的人太多,“读”散文的人太少了。 许多的时候,散文理论的困境或许不是因为缺乏阐释,而是因为过度阐释,以致使人最终丧失了阅读散文的心境。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散文是适合阐释的(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散文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后一种散文往往为批评家所忽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喜欢。 像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也属于拒绝阐释的这一类文字,若是没有闲心的读者,是很难进入他的文字世界的。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有一个明显的困境,就是作家的写作普遍都太紧张了,叙事没有耐心,文气毫无从容,作者没有了闲心,文中也就没了闲笔,以致很多人将散文也写得像小说一样紧张和急迫。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殊不知,即便是中国的传统小说,作者在紧张的叙事中,也还有闲庭信步的时候,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这么凶险、狠毒的场面,可作者仍然不忘来一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就是写“文章”时才有的闲笔,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从容。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小说尚且如此,何况是散文? 《大地的事》是具有这份闲心和从容的,所以,里面的文字,深得散文的神韵;它的出现,恢复了散文作为一种潇洒自然、散漫真实的文体的话语风度。 ◈ 三 ◈ 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像,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语)。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帐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莫里哀)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泡沫。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一九九二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六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像),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哲学家牟宗三门下,而按照牟宗三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命的现代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总是想返回到生命的基座和底部,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他笔下的田园和大地,都是生命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一个大地上的居住者,要有一颗“纯朴的心”,“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餍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祥的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他还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可见,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一直都是在恢复“田园”和“心”之间的亲密关系。无“心”则无“命”,无“命”哪来“田园”?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  (陈冠学) 《大地的事》正是因为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这是一颗真正的中国之“心”,它消融于大地之中,又遍存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无论陈冠学在《大地的事》一书中,对田园生活写得如何具体、实在,他的文字,依然具有广大的想像场域,因为他一直将自己的“心”藏于万物之中。他的散文,写事、写人、写物都不厌其细,但整篇读下来,你依然能感受到他散文的重量——这其实就是“心”的重量。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文字里没有“心”的维度,自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像;而一种没有想像的散文,必定是贫乏的散文。而陈冠学的散文是有重量的散文,它的重,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想像,对人生和存在的追问。 因此,陈冠学和他的《大地的事》,为散文写作敞开了一种值得珍视的写作伦理,它重新解放了作家的感觉,使当代散文又一次找回了那份闲心、自得,并在一种朴拙的记述中体察和丈量着生命的重量。这种“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写作方式,还强化了人和田园、人和大地之间的“谐顺”关系——这无论对于救治现代文明的痼疾,还是对于推动散文写作从现有的困境中突围,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毕竟,在一个散文写作日益泛滥的时代,只有重申一种散文的写作伦理,重申散文写作中的生命维度,才能离散文的本心越来越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