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迎来初版两百周年。这部小说及其衍生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没有人再怀疑它的经典地位。但是,正如任何经典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弗兰肯斯坦》实际脱胎于一则鬼故事。在它荣登“第一部科幻小说”之前,首先是“恐怖”为其开辟了通往经典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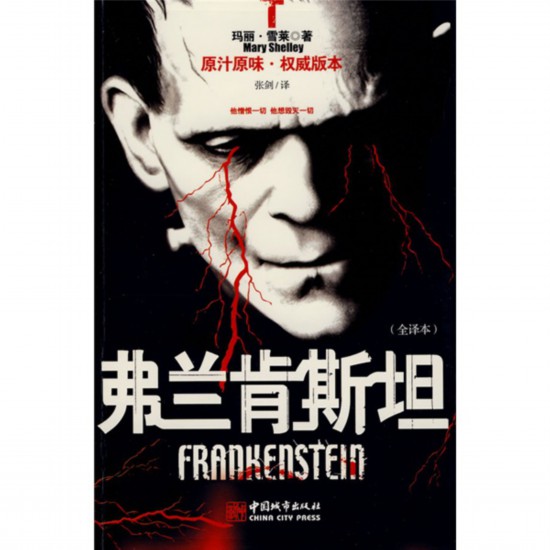 《弗兰肯斯坦》 缘起:日内瓦的无夏之年 《弗兰肯斯坦》诞生的故事足以令后世津津乐道。1816年5月27日,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双子星——拜伦和雪莱在日内瓦湖畔“风云际会”。两人性格迥异,却相见恨晚。拜伦因婚变和债务丑闻出走欧陆,身边是私人医生约翰·波里道利;雪莱则处在第二次私奔途中,他带着19岁的“雪莱夫人”玛丽·葛德文——无政府主义作家威廉·葛德文(雪莱的偶像)和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以及玛丽继母之女克莱尔·克莱尔蒙特。 拜伦本希望每日去湖上泛舟,可惜正如他同年的诗作《黑暗》中所描述的,这是个气候反常的“无夏之年”(后世归因于史载最剧烈的火山活动——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次年北半球平均温度骤降3华氏度)。在阴冷多雨的6月,众人只好躲在拜伦租住的迪奥达蒂别墅(位于今日万国宫对岸半山腰)里谈天说地,包括探讨生命的本原问题,或者朗读鬼故事——自18世纪后期流行英伦、内容灵异惊悚的哥特小说。 根据雪莱夫妇和波里道利的日记记载,一般认为,聚会者在6月16日(或更早)决定进行一场鬼故事写作比赛。而根据玛丽在1831年第三版《弗兰肯斯坦》序言中的描述,她一度为了故事的主题绞尽脑汁,灵感最终来自一场噩梦。在梦里,一个渎神的学生不可思议地将生命赋予了一具拼凑起来的身体。 无论玛丽的梦境是否真实,那场写作比赛都注定载入史册。波里道利181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成了现代吸血鬼作品的肇始,而当玛丽开篇写下“那是一个阴郁的11月之夜……”,竟诞生出一个更伟大、更恐怖的故事。这种恐怖,不仅来自那具可怕之物“显示出生命的迹象”或那双“黄色的、水汪汪的眼睛”,更来自制造生命这一行为本身,“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类试图模仿造物主的伟大机制更加恐怖”。  玛丽·雪莱 从故事到小说 7月21日至27日,玛丽前往霞慕尼旅行。她眺望勃朗峰,俯瞰冰海冰川,那将是故事的核心场景之一。在雪莱8月28日向拜伦辞行之前,玛丽已经完成了最初的故事,并决定将之扩写成小说。 玛丽住在巴斯和马洛期间,阅读了《希腊罗马名人传》、《失乐园》以及航海和化学的科普作品。她将故事设定在日内瓦,模仿《新爱洛伊斯》、《帕米拉》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书信体结构,并给主人公起了一个日耳曼姓氏——弗兰肯斯坦(可能来自莱茵河中游的弗兰肯斯坦城堡,西里西亚小城弗兰肯斯坦——今波兰宗布科维采,马修·路易斯作品中的弗兰克海姆和法尔肯斯坦,或是为了致敬法兰西或富兰克林),配以雪莱曾用笔名维克多。被创造物没有名字,只被唤作造物、怪物或恶魔。 由于首任妻子自杀,雪莱和玛丽在年底完婚。1817年5月14日,小说在几经删改后定稿。经过雪莱奔走推销和两度退稿,《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于1818年1月1日由拉辛顿出版社(Lackington)正式发行,初版500册,作者匿名。最初的评论褒贬参半,有人(包括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称赞作者的大胆想象以及思想和表达上的力与美,也有人批评故事太过荒谬,缺乏敬畏,以及一些处理不够老道。 《弗兰肯斯坦》被顺理成章地归入哥特小说。与强调恐怖意向和气氛的作品相比,“创造生命”的主题具有颠覆性。它的故事情节简单易懂,多重叙事加强了真实度和情感共鸣,两位主角的辩证关系和生死互动更为传播和演绎提供了空间。不久,小说的知名度节节攀升,1821年被译为法文。 不过,小说首版序言写道:“我不认为自己仅仅在编织一系列超自然的恐怖。”在父母和雪莱的影响下,玛丽在小说中穿插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折射出进步的宗教观、政治观、伦理观和教育观。例如,弗兰肯斯坦不仅是挑战上帝权柄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不负责任的父母;怪物则比喻堕落的天使、人类的开化、失去母亲的孤儿(正如作者自己)、被压迫的阶级、报复社会的边缘人群(符合葛德文主张的“后天养成说”)、人性中的善根、爱与被爱的需要……不过,这些思想丰富有余,深刻不足,最终在“恐怖”的主题之下退居次席。 自雪莱1822年海难身故,不为夫家所接受的玛丽便不得不成为职业作家。令其欣慰的是,1823年,首部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推想;或弗兰肯斯坦的命运》在英格兰歌剧院(今伦敦莱塞姆剧院)上演。到场观看的玛丽对这部作品及其惊悚效果表示肯定。同年,公开作者身份的第二版《弗兰肯斯坦》面世。更重要的是1831年的第三版,它奠定了今日版本的基础。为争取更多读者,玛丽在书中强化了主角性格,并在序言中详述了创作的传奇背景。 玛丽·雪莱在1851年2月去世。几个月后,旨在展示人类(大英帝国为首)工业和科技发展成就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拉开序幕。 大众文化的演绎 19世纪后期,工业和科技的蓬勃发展开启了社会和信息领域的变革,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原本属于上流社会的文学和艺术大为普及。经典与通俗的分野变得模糊,流行文化从美国开始夺取话语权。在《弗兰肯斯坦》诞生后的第二个百年,这一趋势帮助它获得了多数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910年,在现代电影诞生15年之后,“发明大王”创办的爱迪生公司第一次将玛丽的故事搬上荧幕。这部12分钟的默片在今天看来并不恐怖,反而有些滑稽。弗兰肯斯坦像是魔术师,怪物则是个憨态可掬的小丑。 1931年,环球影业出品、改编自一部20年代舞台剧的恐怖片《弗兰肯斯坦》一炮走红。波利斯·卡洛夫扮演的缠着绷带、插入电极、目光呆滞、步履笨重的怪物形象虽与原作多有不符,但从此深入人心。19世纪就已出现的将怪物称为“弗兰肯斯坦”的误会开始被广泛接受,标志着怪物占据了故事的中心地位(中文译名“科学怪人”也应证了这一点)。1935年的《弗兰肯斯坦的新娘》、1939年的《弗兰肯斯坦之子》延续了商业成功,使环球影业又拍摄了五部续作。 1957年,汉默公司的彩色影片《弗兰肯斯坦的诅咒》(克里斯托弗·李饰演怪物)再次赢得市场垂青,也同样引出了数部续集。进入60年代后,围绕《弗兰肯斯坦》的演绎进入高潮,除了电影和舞台剧,还出现了电视剧、广播剧、小说(斯蒂芬·金《它》,1986年)、散文、诗歌、音乐、漫画、卡通、电子游戏等多种形式。 这些作品对原作进行模仿、改编、续写(如1974年的喜剧《新科学怪人》),有些将小说情节重新包装,有些嫁接于现实历史(二战或冷战)或虚拟故事(《死亡飞车》系列),有些把小说和创作背景糅合起来,有些仅借用了小说的名称或概念,还有些将怪物与狼人、德古拉、范海辛、超级怪兽或其他恐怖角色拼凑出新的主题。 据不完全统计,以《弗兰肯斯坦》为背景的舞台剧迄今已有近百部,而电影则超过70部。不过,兼具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不多。除了个别作品(例如国内观众较早接触到的1992年版《弗兰肯斯坦》和1994年版《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忠于原著外,许多作品未能摆脱娱乐化和庸俗化,导致许多观众仍对玛丽笔下的情节感到陌生。 就这样,怪物作为流行文化的宠儿,被包装成各种外表和性格,成为一位经久不衰的明星,一个令人惊惧的符号。在英语世界的《最具影响力的101位虚拟人物》一书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高居第6位,紧追哈姆雷特,遥遥领先分别排在第38位和第74位的哥斯拉和金刚。 第一部科幻小说? 作为哥特小说,科学元素是《弗兰肯斯坦》无法忽视的另一个特点。“科学”一词在最初几个章节反复出现,作者还援引了伊拉斯谟·达尔文、伽伐尼和富兰克林的实验。不过,玛丽虽然另有一部《最后的人》可被视为科幻小说,但并不是科幻作家。《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比重不高,也没有对创造生命做出合理解释(至今无人能够解释),只能算作1970年代才提出的“软科幻”。由于时代和视野所限(“科学家”一词直到1834年才出现),玛丽似乎没有意识到《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意义,更未提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 毕竟,科幻是大众文化兴起的一部分,从诞生到成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19世纪末,“科学传奇(Scientific Romance)”已被用来形容凡尔纳、威尔斯和柯南·道尔的作品,但“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一词在1926年才由雨果·根斯巴克在其创办的首本科幻杂志《惊异故事》中提出。 到了20世纪中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开始着手研究自身的历史。人们上溯2世纪琉善的《信史》,下及1895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关于科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 1973年,英国科幻作家、“新浪潮”代表人物布莱恩·奥尔迪斯在科幻史著作《十亿年大狂欢》(1986年扩写为《亿万年大狂欢》)中,首次将《弗兰肯斯坦》视为第一部科幻小说。他表示,随着认识的深入,定义科幻的起源愈发困难。但是,将《弗兰肯斯坦》视为科幻鼻祖仍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弗兰肯斯坦》恰好写于工业革命和进化革命的双重进程之初,对人类的能力提出了全新设想。在宗教和艺术史上,“创造生命”的想象不乏前例,但玛丽让专属上帝的伟力降临凡人,将幻想的“可信的不可能性”转变为科幻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这种被新时代读者所接受的“人定胜天”,构成了科幻的基础——在已知与未知、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桥梁,与神话和奇幻划清了界限。 其次,《弗兰肯斯坦》通过接受科学方法,宣告了科学对超自然的胜利。弗兰肯斯坦一度崇拜炼金术和神秘主义,继而皈依现代科学,他的创造最终以化学这一“自然哲学中已取得和可能取得最伟大进展的分支”以及物理学、解剖学为基础完成。或许,玛丽将弗兰肯斯坦比作普罗米修斯,不只因为他们创造生命的事业,也是为了赞颂后者为人类盗取的真理之火——科学? 最后,《弗兰肯斯坦》表达了对科学发展的早期忧虑,向“技术万能”和“人定胜天”提出了警告,呼吁理性的回归。弗兰肯斯坦代表疯狂科学家,而怪物意味着实验失败的风险。科学既是对未知的探索,其结果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恐怖的——这将在现实中不断得到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科幻产生于哥特文学,便在情理之中。 尽管认定“第一部科幻小说”并无统一标准,奥尔迪斯的主张还是被科幻界广泛接受。随着科幻小说回归主流文学,《弗兰肯斯坦》也进入课本,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后人发现,《弗兰肯斯坦》的内涵异常丰富,涉及遗传学、基因突变、机器人学、社会工程学、精神分析学、伪科学、机械论、反乌托邦等一系列科幻母题,成为史蒂文森《化身博士》(1886年)、威尔斯《莫洛博士岛》(1896年)等许多更加精巧和深刻的作品的先驱。近年来,当电影逐渐成为科幻作品的主力军,人们又不时能在《银翼杀手》、《机械战警》、《异形》、《终结者》、《黑客帝国》、《剪刀手爱德华》、《复仇者联盟》、《机械姬》等影片中看到弗兰肯斯坦和怪物的影子。 经典之问:人造人——科学还是恐怖? 《现代汉语词典》将“经典”解释为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弗兰肯斯坦》的典范性除了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包容性和思想性,也得益于流行文化所赋予的新鲜度和生命力。它的成功表明,市场对塑造经典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证明,经典难免要经受解读和歪曲。甚至,解读和歪曲有时也构成了经典的一部分。 因此,经典是时空与环境塑造的,也不是绝对不朽的。《弗兰肯斯坦》之所以在两百岁时依然受到追捧,首先是因为其主题强烈而矛盾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人造生命”的科学梦想,另一方面是对其内生风险的疑惧。 早在20世纪中叶,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就提出了“弗兰肯斯坦情结(Frankenstein Complex)”,用来描述人类对仿真机器人的担忧和恐惧。这一心理类似“恐怖谷”理论,也是阿西莫夫设定“机器人三定律”的缘由。后来,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还发明了“弗兰肯食品(Frankenfood)”一词,旨在讽刺科学创造的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的危险。 与玛丽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科学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类越来越接近“人造人”幻想的奇点,也陷入越来越大的矛盾和危机。2014年5月17日,当地球上还不存在阿尔法狗或体细胞克隆猴、也没有机器人获得公民身份的时候,人们在日内瓦城南的普兰帕莱广场(Plainpalais)也就是弗兰肯斯坦的幼弟被害的地方立起一座怪物的雕像。只见他高大褴褛,蹒跚独行,仿佛在等待他的同伴——一个真正的人造人,以印证弗兰肯斯坦的临终遗言:“我所失败的,未来可能会由别人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