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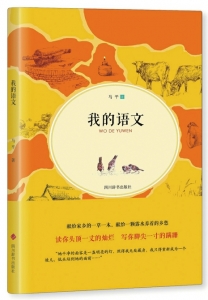  直接瞄准当下社会重大问题,近距离与现实展开对话,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巨大的课题。写出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以文学的形式记录脱贫攻坚工作,用艺术的创造描绘脱贫攻坚事业,写出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写出乡村生活的真实状态,勾勒出了乡村人们的生动样貌,并不容易。而且,仅有技术还不行,更要对乡村有足够的了解,一颗真正关心乡村的心。 对于这些,作家马平恰好都具备。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凭着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和深入思考,他最终以富有个性的书写,拿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他巧妙地把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包裹在日常化的叙述之中,为脱贫攻坚战略工程提供了新的文学表现。 人物简介 马平,1962年生于苍溪,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和散文集《我的语文》,小说《高腔》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高腔》2017年在《人民文学》上首发后,得到很多好评。被改编成话剧,如今又出了单行本。感受如何? 马平:好评越多,我越清醒。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成就了这部小说,读者对重大现实题材的新期待催生了这部小说。由它改编的同名话剧正在省内巡演,我看到它走过了一个不断翻新的历程,感到了它不断焕发的生命力。我也发现,话剧从小说中采撷了那么多花,并没有让剩下的那些花感到寂寞。我的花田沟有无数的好花,谁看上哪一朵就采哪一朵,在这儿我不会做护花使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读《高腔》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也可以写得很生动、细腻,生活细节与人性展现都非常真实,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你是怎么看待主旋律题材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马平: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在优良品质方面打一点折扣,可以粗糙、稀松、平庸。主旋律作品更应该生动、细腻、真实,力求思想性、文学性俱佳。《高腔》动笔之初,我有过掂量,这是重大题材、宏大主题,也是一个难活、细活,需要像脱贫攻坚本身一样花一番绣花功夫。一部主旋律作品如果忽视了文学性、艺术性这些根本的要素,那是无论如何也起不了高腔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我能感觉到,你将《我的语文》中散文的笔法散发到了小说写作当中,文笔非常优美。这是你有意考虑的吗? 马平:一直以来,总有人认定我曾经写过诗,我说没有人家还不相信。一个作家朋友认为我的散文有两种修辞,即小说和诗。现在,你大概是要说我的小说也有两种修辞,即散文和诗。这些,说是我的有意考虑,或者说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都没有意见。我的作品总不会少了诗意,即使写脱贫攻坚这样的题材也不例外,说到底,告别贫困,走向充满诗意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一起奋斗的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高腔》对你个人的文学创作而言,具有怎样的标识性意义? 马平:我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乡土题材居多。创作《高腔》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我一边要排除健康状况不佳带来的麻烦,一边要破除已有的乡村经验带来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经历了一次挑战,完成了一次洗礼。我知道了,自己身上还有爆发力。我不敢说已经写出了自己的标识性作品,但我拼力发出的一腔高唤,或许能让人在众声喧哗中记住一声真切,一声热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成长于乡村,从乡村走来。这个成长背景,对你的文学创作具有怎样的意义? 马平:我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不足我现在年龄的三分之一。我没有读过大学,乡村就是我的大学。离开乡村之后,我好像变成了庸常生活的走读生。依然是我的乡村记忆,常常让我觉得惊风雨泣鬼神。但我的小说创作并没有照抄照搬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散文创作也只是非虚构地呈现了那冰山一角。所以,对我的文学创作而言,那既是一个真实的背景,又是一个虚幻的背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面临不少问题,比如说青壮年劳力都转移到城市里,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凋零,等等。身为乡村之子,又是一名作家,你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吗? 马平:说句大话,我一直思考着乡村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可以给你开一张长长的清单。如今,“乡村振兴”四个字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的主角意识已经被遽然唤醒。这些年,我一直在探寻、琢磨乡村的人气问题。我有一个不一定确切的说法,村姑和小媳妇是乡村的眼睛,如果在一个村子里看不到她们,这个村子的眼睛就是暗淡无光的,甚至可能是瞎的。现在我认为,外出的村姑和小媳妇们纷纷返乡了,那么,这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信号,乡村振兴大有希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高腔》里有很丰富的民俗知识,有很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这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没有这些,小说的文学趣味就会打折扣。你怎么看? 马平:这些,都不是调味品。它们都是内容的一部分,并不为任何趣味而生。城市小说也非常重视这些。比如写《我的名字叫红》的帕慕克,他仅仅是为了拿准一座城市的气味,就在那座城市里闲逛了一两年。我想,那个气味要是一直淡薄,或者没有熟透,他的文字大概会让一股小风就吹散了,或者,被一股来历不明的气味生生憋死、闷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乡土题材小说曾经在文坛上有很高的位置,代表性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等。他们的小说风格带有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如今时代发生了变化。您怎么看当下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 马平:时代变了,气息当然也要变了。我现在很少看乡土题材小说,我不想再看到乡长给镇长汇报工作那样的笑话。我看过一些乡村出来的人写的乡土小说,非常诧异他那乡村是从哪儿盘弄来的。这或许是我短视,或许是我又让老家做了识别码一叶障目的缘故。我的意见是,要写乡村,最好先寻一条小路进去,然后挖地三尺。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