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柯文选》 作者:米歇尔·福柯 版本信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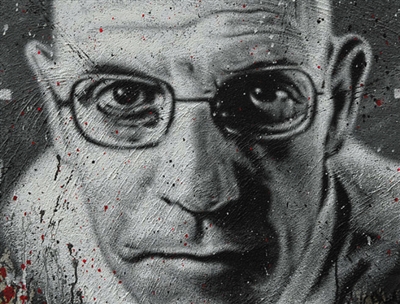 “书写旨在指定、展示、显露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没有书写就会保持隐匿,至少也是不可见的……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远,是度量距离。书写是将一个人自己置于那把我们和死亡,和已死的东西分开的距离。同时,这是死亡在其真理中展露的位置,不是在隐匿的、秘密的真理中,不是在其曾经所是者的真理中,而是在把我们和它分开的真理中……” “作为自我训练的一个要素,书写,用普鲁塔克的一个表达来说,具有一种型塑性格(ethopoietic)的功能:它是将真理转变为气质的一个动因……因此,书写是“展现自己”,把自己投射到目光中,使自己的脸出现在别人面前。就此,我们会明白,书信是一种凝视,它将目光对准收信者。” 上面两段关于“书写”的论述,如果不加说明,相信很容易被读者当做来自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事实却是,它们都出自20世纪思想家福柯的笔下;区别在于,前者选自1968年福柯的一段访谈,后者则摘录自福柯1983年发表的文章。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关注福柯思想的人而言,恐怕很难不去追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上面两段文字对比所呈现出的从语言风格到论述重点的双重转变? 回归生命自治 上世纪90年代,福柯在国内学界便已声名大噪;像《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这样的论著也正是在那个年代被陆续翻译出版。令人沮丧的是,抛开翻译的因素不谈,福柯著作的难懂程度亦是同等的“臭名昭著”。个中原因,福柯自己亦曾坦言:自己早期的写作是“修辞化”的,是巴洛克式——这样的写作并不试图直击或揭示所谓的“真理”,而更倾向于在近乎于层叠的书写中去“试着包围、吸引、指出我们说话和观看所透过的那个盲点……把捉那不可见性,把捉那太过可见的不可见者,那太过亲近的疏远,那未知的熟知……”。这样的写作在下笔的刹那便同步地设置了阅读的门槛:它要求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凭借自己此前的积累去做一个“打开”的动作,去打开那巴洛克式的皱褶——与此同时,作者却从未提及所谓“正确的打开方式”。 若重读福柯在他去世前一年留下的文字(开头第二段引文),正如汪民安教授所言:平实、流畅、漂亮。或许,这正可看做福柯对自己所讲授的“直言”这一概念的身体力行。福柯基于“直言”(parrhesiazesthai)的词源,指出:直言者,是一个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一切的人。他不隐藏什么,而是通过自己的话语向他人完全敞开心扉——也即,“展现自己”——在这里,福柯既是在用“直言”的方式书写(讲授),也通过这种书写(讲授)重新定义了书写本身,呈现出一种完美的自反性。在更为实际的层面,这也意味着,如果选择直接阅读福柯晚期的写作,在文字层面所遇到的阻碍会小上许多;同时,福柯晚期的研究与我们当下的境况又有着诸多对应,两相叠加之下竟使得《主体解释学》这样的晚期述作变成了进入福柯思想脉络的上佳入口。只是,由于福柯在太多时候与“性”、“权力”、“规训”这样的语词并行出现,给人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好奇者终究难免追问:福柯是如何/为何从“权力的规训”转向“直言的主体”的? 提及福柯的转向,便不能不提法兰西学院讲座(除了福柯之外,罗兰巴特,布尔迪厄都曾担任该讲座的教授)的设立。这个创设于1969年的讲座要求所有任课的教授必须讲授/展示一种原创性的研究,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任课教授于讲台之上重复自己发表过的著作,哪怕听课的人只是无需注册的普通民众。而福柯自1971年起便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直到他去世为止。显然,没有任何文献能比这13年的授课材料更有资格成为展示福柯思想轨迹的路线图。 即便只是简单翻阅这11册(根据福柯这13年的讲座录音按年月顺序整理出来的法兰西讲座系列)丛书,亦足以从每一年度的主题变化上瞥见福柯研究铺展的轨迹:1974年-1975年尚且在谈论“不正常的人”,1975年-1976年便指出“必须保卫社会”,1978年-1979年是“生命政治”的正式提出,1981年-1982年则展开论述“主体解释学”。在此,1974年-1975年的讲座可被看做是福柯早期对疯癫与规训的研究之延续,1975年-1976年开始便已彻底转向规训背后的社会权力网络,进而引出对“生命政治”的思考,其关注的重点实为由诸多治理/支配技术(technique)所承载和实现的治理(governmentality);在此(充分理解福柯所谓“治理术”的)基础上,福柯的关注点从治理术转向被治理的主体,亦算得上是某种必然。由此,我们也才继续读到了主体阐释学的提出,读到福柯继海德格尔之后对古希腊的另一种回归。 转向弱者的武器 对于此一转向,福柯自己在1982年的一次讲座中有过更为清晰的表达:“我更关注的是支配的技术与自我技术。我尝试建构的历史,就是关于支配权及自我的知识所编成的历史……我想弄清楚的是,‘疯狂’这种奇怪的话语如何使在疯人院内部及外部进行的对个体的管理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他人的技术与支配自我的技术之间的接触,我称之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我大概已经给予支配性的技术与权力的技术过多的强调了。现在我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对个体进行支配的技术问题,以及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技术问题。” 福柯的这段自白除了道出关注点转换的因由之外,同样清晰地点明了此种转向的内在逻辑:之所以转向自我技术,最终仍旧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治理术——某种意义上,治理术本身恰好是支配技术与自我技术碰撞互动的结果,是二者在相互遭遇之后形成的“界面”——因此,为了全面揭示治理术的样貌,福柯必须在对于支配技术的大量研究之外补上对于自我技术的大量考掘。 然而,不论福柯原本的意图如何,他对于古希腊的回归,对过往不同时代自我技术的考掘,实则为每一个个体在面对支配技术时提供了所可用以对抗的武器库。换句话说,面对基于社会权力网络而强大如斯的种种支配技术,个体依然能够选择拾起一些“弱者的武器”来减轻甚至躲避支配。这种对抗,其实也就是试图在支配技术之下,争夺成为主体的权力,将自己形塑为真正的主体。令人惋惜的是,福柯尚未来得及完成其对于自我技术的考掘便已去世;而在他去世前所展开的考掘中,“关注自我”,“(自我)书写”,以及“直言”,或可算得上是他在最后三年的讲座中着重讨论的核心主题。 在这里,我之所以没有将前述三个核心主题词称为三种自我技术,是考虑到在福柯那里,“关注自我”、“书写”与“直言”乃是密切相关的行为/行动,且指向同一个内核:书写,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直接记录而非分析,以此区别于为更多人熟知的“认识自我”(认识你自己)。只因“关注自我”的落点,是在一个人的灵魂,而非其他。而灵魂,往往经由书写(书信/笔记)来袒露——不论是对自己,对别人,还是对导师,对上帝。与此同时,书写也是滋养和修补灵魂的途径,是能将外部养分内化的过程/技术,也因此能将真理注入个体的灵魂。至于“直言”,则更像是对书写和言说的约束,同样指向了对于自身的袒露。 遗憾的是,福柯对于自我技术的考掘本身并不能保证他所讨论的自我技术能成为所有人的武器;就好像在当下的时代,博客性质的书写亦不足以帮人抵御自媒体书写的狂欢。更何况,转向自我技术的隐含前提,是意识到支配技术的存在与作用——显然,这并不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或许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是:如果不能真正理解福柯的转向,便无法捡拾起福柯为我们准备的潜在武器——最终,“理解福柯”成为了问题(问题化了)。 一方面“理解福柯”可以变得如此关键与迫切,一方面却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法兰西讲座系列依旧看上去遥遥无期;于是,北大社于今年年初推出的《福柯文选》竟成为了当下唯一触手可及的替代乃至救赎——该文选对福柯文献的遴选与分卷完全足以构成对法兰西讲座系列的优质替代,再加上上乘的译文质量,俨然已完成国内目前译著中对福柯思想轨迹最为清晰的勾勒与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