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关雎鸠》的故事发生在海南瑞溪镇上,这个偏远小镇是林森的故乡,满载着他的青春记忆。“初中的那三年里,我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非要躺在四处通风的楼顶才能睡着。现在想起,其实那些夏天也并不太热。春秋两季,我也仍要睡在楼顶上,一抬头就看到满天的繁星或者乌云。”《关关雎鸠》里的少年张小峰身体深处,就蛰伏着这个只能在满天繁星和热带海风中睡去的男孩。
因为被琼州海峡隔离在大陆之外,海岛上依旧保留着许多已在现代都市失落的传统习俗,然而身处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小镇的日常生活亦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打破和浸染的命运。林森写下瑞溪小镇三十年里发生过的故事,或者说,是历史。这是中国社会飞速变化的三十年,是海岛小镇避无可避的三十年,同样是他从出生到成长的三十年,“正是因为经历了小说中的很多事,才让我有了写下这部小说的冲动”。
“在充满躁动的、灵性十足的、幽默机智的、快刀斩乱麻的语言强势介入下,瑞溪镇犹如一列被独特民俗和生活裹挟的‘高铁’,飞速驰过这个海岛的历史,让我们进入一些个体生命荡漾和挣扎的心灵。神奇的故事和潇洒不羁的叙述风度令人沉醉。也同时获得了小说最应具有的飞扬大气和万千仪态。在生命流逝的笑声和哀鸣中,某种民俗的回归与重现,也许是作家对往昔敌意、混乱和亲切交织的生活,最具人道情怀的叹息与悲唤。”在阅读了《关关雎鸠》后,作家陈应松如是写道。
藏在喜欢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韩少功和古龙的海岛少年林森内心最深处的,永远是那个故乡岛屿:“生活那么丰富,可我只能选择一种。回到岛屿——文学总要回到包含生命热度的状态中去,不会永远都和话题、时尚、娱乐有关……没有办法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空的时候,我们只有往回走,找到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故乡。有一天从海岛传出去的声音,肯定会带着海风的味道,带着碧蓝的颜色,也带着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
“历史的废墟”到“现实的纠缠”
记者:《关关雎鸠》最初发表于2012年《中国作家》,至今年出版已经有4年的时间。与最初的版本相比,你作了哪些修订?为什么要为小说取名《关关雎鸠》?
林森:这部作品由发表到出版,修订并不多,大多是字句细节方面,大框架并没变动。如果今天的我重新去写这个小说,或许会完全不一样,或许在形式感上的探索更加大胆一些;或许,也不想像当初一样,要把小说写得这么“重”。
书名《关关雎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的象征——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在流水边的镇子,镇上的每个人就是“雎鸠”,而他们都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关关”的悲鸣与欢叫。声音在这个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叙述核心,整个小说就是以仪仗队的小号声开始。如果再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整个小说五个章节,每个章节的结尾都是一样的,以“呜”的鸣叫结束;而每章的小标题如《闹军坡》《南风云》等等,都是海南民间音乐的曲牌名,也是声音。
记者:你曾表示,与2015年出版的《暖若春风》相比,更喜欢《关关雎鸠》。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关关雎鸠》更“海南”,但它也比《暖若春风》更难进入。
林森:这两部小说相比较,《关关雎鸠》更难进入几乎是注定的,在我写的时候就意识到了。把这两部小说摆在一起,我也更愿意去翻一翻《暖若春风》。这不仅是文字造成的,更多地源自主题的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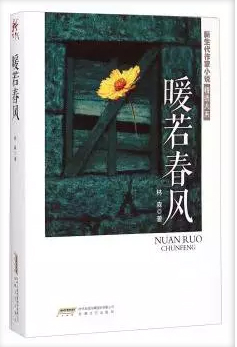
《暖若春风》
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左右,是我生长的近三十年,也是小说里跨越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无所不在,连一个海岛上的偏远小镇也不能避免。我本无意表现所谓“地域”,只不过是当要讲述这样的故事时,这些人所有的言行便和那些“民间之礼”捆绑在一起。小说里流传几百年的“装军”仪式的消逝与试图恢复,不正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遭遇吗?民间之礼的消失,赌博、毒品、诈骗等的疯狂涌入,不仅仅是小说里的瑞溪镇所独有的,也是整个中国的现实。
我想写的,不外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的遭遇与变异。这并非是地域性的故事,它具有普适性的思考。《暖若春风》于我,是有些旁观的,历史的后遗症还在,但作用力在削减;《关关雎鸠》则与我本人更纠缠不清的,也就偏爱一些——这种偏爱,包含着我对难以抽离的生活的某种敌意。
记者:这两部前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对你的写作分别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暖若春风》讲述了大时代之后破碎的“小日子”,那么,《关关雎鸠》描写了什么?
林森:《暖若春风》遥望了历史的废墟,《关关雎鸠》则直面了现实的纠缠——这样的写作,当然不会让读者很轻松进入。
这两个小说的完成,对我个人来讲,是建立了某种“写作的自信”,完成它们之后,我再进行别的写作,我不会畏惧,再漫长,也能完成。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在国内“80后”的长篇创作里,是独异的,那么多年轻写作者都太关注自我的那点小情绪了,对阔大的天地视而不见。我不愿那样。
记者:这两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叙述手法和布局结构错综复杂。作家莫言曾说,你的小说就像一座庞杂的原始森林。注重结构,注重技巧,这对写作者有很高的要求。对当下流行“故事性”的小说写作现场来说,这也不是最受欢迎的写法,甚至可以说是最累的。
林森:莫言老师的话,是在海南参加一个活动时看过我的作品后说的。我更愿意把这当成批评的声音——或许他的原意,是说我没把故事讲得清澈、单纯呢?要知道,单纯的小说,并不容易写。
“轻”和“重”永远是小说里要平衡的因素,太轻,难免虚浮;太重,便觉凝滞。《关关雎鸠》的“重”,是题材决定的;写在《关关雎鸠》之前的《暖若春风》,虽然主题也沉重,但在处理上要轻盈得多。《暖若春风》以正文和附录交叉为结构,并把整个小说的源头,放在小说的最后,都是形式上的追求。《关关雎鸠》则用不同的鸣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合奏,我把结构隐藏了,是不让结构跳出来抢戏。
记者: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一员,你认为你们的写作在当下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呈现出的是怎样的面貌?
林森:说到“80后”的写作者,其实我们有一个局限,好像“80后”里只有小说家,但其实很多“80后”诗人、散文作者,写得真好。我也写诗,出过两本诗集,也参加过青春诗会,但我很清楚,自己没法当一个很好的诗人。但我愿意在诗歌里锤炼语言,保持对叙述的敏感。“80后”小说家里,我喜欢双雪涛和颜歌,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写作意识,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力;写散文随笔的,我喜欢胡竹峰,在那么浮躁的当前,他竟然有着某种民国风韵,学养丰厚,文字好玩;诗人里,写得好的就很多了。
“衰败的诗意”和“习俗的枷锁”
记者:你大学的专业是水产养殖,后来是怎么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除了《暖若春风》和《关关雎鸠》,你以前还练习写过四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林森:被调配的专业,换不了。这专业读得比较狼狈,读书和写作反倒成了逃避的手段。之前写的几个小说,两个是大学时候在网吧敲下的写大学生活的,一旦写作意识上去了,这东西就不能见人了。还有一个写苏东坡晚年在海南的生活的,我写时太年轻,理解是浅薄的,光有故事,没意义,2011年出版前,撤掉了,不想以后见到后悔。还有一个,我不愿说,反正三十多万字全废了,或许多年后会重新写出来,或许永远废掉了,谁知道呢。
记者:许多年轻作者在最初的小说创作中,会经常以投射自己生平的角色为主角。但在《关关雎鸠》中,年轻人却是相对退后的角色,你没有选择自己的同龄人张小峰或者潘宏亿作为你的主角,而是让老潘和黑手义两位老人来主持大局,为什么?
林森:我挺喜欢读武侠小说,有时我也想,若是以武侠的方式,写一个当代的小说,会是怎样?《关关雎鸠》里,我就尝试了一下,让类似武侠小说中掌门人的两个老人,来面对所有的“江湖危机”。——这个理由有点游戏心理,但这方面的因素是有的。
更多的理由在于,当我试图表现一个小镇三十年的变化时,以少年人来当主角,是压不住阵脚的,只有那些饱经生命沧桑的老人,以“老骨头”来与之硬碰硬的时候,才能产生某种张力。老潘身上那种老派的硬气,是这个小说的基础,没有这一点,所有的讲述都不成立。他们这代人身上的饱经沧桑,面对当下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就有了某种“衰败的诗意”?
说实话,我挺瞧不起那些过于情绪化的“青春写作”的,所以在《暖若春风》里,即使主角是年轻一辈,但他们也得去承担那种“历史的后遗症”。——青春写作为什么之所以只是“青春写作”,是由于人物的生活背景被抽空了、根断了,这就造成,即使写的是老人,也是青春写作。

《关关雎鸠》
记者:老潘和黑手义是传统家庭中的“父亲”的角色,他们是旧时代的慧者,是家庭的精神支撑,但又无力阻挡新事物的到来,身上有一种悲剧性。
林森:“雎鸠”的“关关”鸣叫,有两个“关”,为什么?因为得有应和,有问有答。若只有一个老潘,想想也挺孤独、挺无助的,总得有个人说说话才行,于是有了黑手义。这两个人定了之后,才开始往下,构建所有的故事。
在我们心里,对家里这样的老人,总是从嘲笑到认同,最后追随。老潘的原型之一,当然是我那吸毒堂兄的爷爷,我的伯公。他最后死的时候,家里已经溃败得不像样了,但他竟然在死前,把自己死亡都安排好了。他知道家里烂成这样,或许连他死后的安葬都会成为问题,于是他在死前,掏出一笔一直暗藏多年的钱,交给我伯父——他的葬礼刚好把那笔钱花完,不多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骨头里的气,是我想去写的。
记者:你的小说中有大量海南乡土意识和生活场景的记忆。故乡对一个写作者意味着什么?
林森:故乡,就像是血肉,是没法选择的,喜欢或者讨厌都只能承认。既然不能选择,也没法逃避,那就直接面对。其实挺羡慕很多人,可以到大城市甚至到国外去,也能如鱼得水,那种自在和轻松挺好的,没必要这么“苦大仇深”——事实上,我的弟弟妹妹,都比我要洒脱得多。
记者:你小说中的“家”,是“家庭”的家,“家族”的家。一个人不仅是作为个人活着,他或她更多地生活在一个家族的延续和传统之中。这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现代都市中已经很少见。这一点,在《暖若春风》的写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林森:宗族观念在当前的中国,处于溃败的过程中。但据我所知,广东潮汕以及海南大部分地方,对于家族之重视,是超过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的想象的。在海南的乡间,最气派的是村庙和祠堂,每个传统节日,都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这样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对于维系乡村伦理极其重要,无论走得多远,在该回来祭祖的时候,就得回来,死后更得魂归故里。
你前面谈及的小说难以进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很难感受得到小说中捆绑人物的那种“习俗的枷锁”,因此觉得有地域性。但其实,这种“枷锁”并非地域性的,而恰恰是我们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抛弃的“礼”的部分。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海南这种偏远之地,由于隔绝着一道琼州海峡,使得很多礼仪得以保存。在《关关雎鸠》里,第一章写“军坡节”停办,是“礼之失”;最后一章,写“军坡节”试图恢复,是想写“求礼”,在失去到求的过程里,发生了什么?
《暖若春风》中,远去台湾的“曾祖父”死之前都要回来故乡,死在1997年的春节之间,那是我一个朋友家的事。这当然是中国人内心中的故土之念在起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