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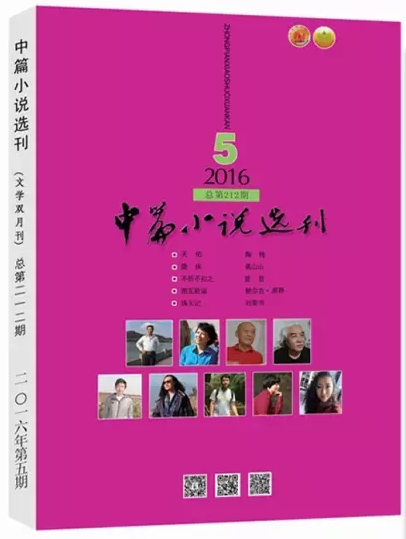
阅读《中篇小说选刊》第五期篇目时,正值里约奥运赛场如火如荼。网络时代的奥运会,如同网络时代的春晚,场下的万众狂欢更胜于场上的激烈与热闹,不爆几个网红都不能算成功。傅园慧的妙语连珠令人喜闻乐见,赛场外运动员恋爱花边也格外为人津津乐道。当然,在耽美文爱好者眼中,这些都还称不上是CP(官配),国民CP的称号无疑属于国球队伍里的一对好基友——马龙和张继科。边看奥运,边读小说,我也获得灵感,决定把本期的中篇小说们来个CP配对。
第一对CP:《阵亡》与《隐疾》,关键词:记忆。
尹学芸的《阵亡》以略带感伤的悠远语调开始讲述那些“褪了颜色的记忆”。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远离文化中心的外省小城,其时,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渐行渐远,唯余背影;而在埙城,一个十来人的文学爱好者小团体,仍然在定期的聚会中咂摸着文学盛宴之后的残羹冷炙,不肯散场。“我”——女诗人王云丫无疑是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因为整个埙城只有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诗歌。然而,她的地位却受到了一位外来者的挑战——舒宇带着文化首都的种种传说,连同他浪漫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及他那首并未写出的诗歌《阵亡了一只小倭瓜》,成为大家的话题中心。“我”渐渐被大家冷落了,甚至包括“我”要好的女朋友民子。而舒宇还卑劣地骗取了民子的爱情。“我”在一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当着众人的面揭穿了文化骗子舒宇的真面目。文学小团体也瞬间瓦解,作鸟兽散。一个文化偶像“阵亡”了,伴随着一个时代轰然倒地,只留下一片荒芜——这个城市再也没有人写诗了,这令我颇感遗憾。然而,故事在结尾处被反转,因舒宇的欺骗而改变了命运的民子,却由于没有目睹文化偶像被揭穿的那一幕,反倒免于在这场文学溃败中“阵亡”。此前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她,活跃在网络上,化名发表诗歌,而“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她的热心读者。尹学芸哀矜、细腻的女性叙事腔调令人回味,而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在现实世界的洪荒中,能幸存下来的,是一对关系亲密的文学女性。裘山山的《隐疾》也是女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总是文学发生的策源地。四十年没见的青枫和丽闽在幺妹的安排下见了面,却勾起了青枫内心潜伏多年的隐疾——四十年前,三人就读同一所子弟学校,也生活在同一个家属院内。因被人造谣与乡下来的男同学冷锁江谈恋爱,仗势欺人的丽闽一定要揪出造谣者,在听信了他人的“诬告”后,将造谣者锁定为青枫,并与冷锁江一起先后欺侮了青枫,令其时隔多年仍难以释怀。再见面时,当年骄纵的丽闽垂垂老矣,甚至信了佛,她请求青枫原谅自己当年的鲁莽行为,并偷偷告诉青枫,当年的告密者,正是青枫的好姐妹幺妹,令此刻的青枫陷入纠结——她该原谅吗?原谅丽闽,原谅幺妹?按照一般的写作套路,我们的主人公该选择原谅吧,让往事都随风,退一步海阔天空,人生境界的升华啊!然而,作者却让她的主人公选择了“不原谅”——“她不原谅,但这个‘不原谅’不是仇恨。她不恨他们。她不原谅只是为了把自己和过去捆绑在一起,不让自己与过去脱钩。如此,她不原谅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个年代。”尽管不原谅那个年代的说法有些语焉不详——是那个年代家长之间的等级关系,造成了孩子之间的“政治”;还是那个不开明的年代,蜚短流长所带给人的精神压力?然而,选择不原谅毕竟是一种勇敢,正如鲁迅临终前所说“一个都不宽恕”,不原谅是一种执着,它所执着的是生命本身的尊严。
第二对CP:《越狱》与《发明家赵奇源》,关键词:突围。
从哪里突围?我说的当然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平庸乏味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围城,人生处处是围城。李铁《越狱》中的机关中层干部牛晓春在丧失了激情的婚姻之外寻觅激情,通过网络勾搭女孩,签下了“不平等”的“包养”协议——一个寻欢猎艳者却不得不扮演“柳下惠”,“沦为”文化教员和启蒙者,而他竟然还有点儿乐在其中——这看似荒诞的情节,作者似乎是想探索,一个深陷婚姻和事业“围城”的出轨者的心理动因。而王卉子《发明家赵奇源》则更多文人的浪漫。赵奇源的人生似乎是被精明的母亲设计好的,夸张一点地说,这是成功人士的乏味人生,包括一个功利而庸俗老婆的“标准配置”,这使不过三十岁的他,仿佛拥有了六十岁的人生。而对他怀有崇拜之情的姑娘马小宝是他反思人生的契机,是他重燃热情的发明“一扭”。《越狱》的结尾,试图“突围”的牛晓春被捉了奸,与他一同落网的是真正的越狱者,法网恢恢,人生如狱,《越狱》在荒诞感中给人以下坠感;而《发明家赵奇源》的结尾却以一种诗意美学化的“私奔”,带来了心灵的飞扬,小说的主人公至少在文学想象的意义上,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突围”。
第三对CP:《图瓦歌谣》与《不折不扣之》,关键词:他者。
叙事者流浪异乡,进入一个异乡文化的他者世界,两篇小说的题材类似,在写法上也有可比性,都是通过段落化的叙事,来呈现他者文化的不同方面。我重点关注的是两篇小说中叙事者“我”——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鲍尔吉·原野的《图瓦歌谣》以一种诗趣盎然、悠游喜悦的笔调来写图瓦国人的信仰,写他们的生死观、生命观、金钱观、物质观,可谓笔意相合。在对他者——图瓦国人的观察与交往中,叙事主体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鹿屁股酒馆”中,图瓦人对物质的单纯享用态度,是一种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关系熏染的朴素生活观,以一种“文化说服”的方式改变了叙事主体。而曾哲的《不折不扣之》则以一种粗粝的文风迎合笔下粗粝的西部生存。事实上,原来陌生化的“西部”在作家们的反复书写中,已经渐渐地被“去陌生化”,比如藏人的“天葬”仪式,让我们立即想起马原的小说;在贺兰山被虏至采石场黑作坊,那种边缘群体中的人性迸发,也使我们想起艾芜的《南行记》。而曾哲小说的叙事主体面对他者文化却是如此“不折不扣”,当然,他也不曾改变他者。不折不扣的主体与他者之间,或许也为文化的多元与人性的复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四对CP:《天佑》与《珠玉记》,关键词:传统。
这两篇作品看似毫不搭界,陶纯的《天佑》讲述一名“老红军”的革命生涯,刘荣书的《珠玉记》写水产公司“神算子”的职业传奇,但两者都有各自的写作传统:《天佑》是革命历史题材,《珠玉记》是“奇人异事”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红色经典”发展至今,中间也经历过一些探索和尝试,尤其是“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讲述的规定性所做的解构,可谓冲击甚大,但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又重回常规,只能在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传奇性上做文章。《天佑》讲述阴差阳错被劫至红军队伍中的乡绅幼子天佑,如何在红军战士的一路照顾下走完长征险途,为此,庇护他的“猴叔”“虎叔”等红军战士先后付出了生命。多年后,老年天佑带着子孙后代重走长征路。今年适逢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小说以此方式纪念革命者,纪念长征,虽然题材与主题腾挪的空间不大,但胜在故事感人。《珠玉记》某种程度上是向阿城的《棋王》致敬的作品,少年朱瞳身怀神算异禀,并忘我地沉迷于“技艺”,与《棋王》中的棋呆子王一生的人生境界可堪比拟,《珠玉记》最后那场双雄争霸与《棋王》的那场车轮大战庶几近之,同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珠玉记》在此显示了作者突出的文学才华,虽然整篇叙事能力并不均衡,对人物生命哲学的开掘也力有不逮,但足以窥其文学抱负与文学气象。
最后,还剩一篇作品落了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小词的《一把薄刀》最符合人们对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期待——正如有一位论者在近期的文章中写的:“作者希望在作品中全景展示某一社会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同时体现出自己的批判立场和情感温度,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文学样式,显然非中篇小说莫属。”(邱振刚:《为什么是中篇小说》)《一把薄刀》在这个意义上,是典型的“中篇小说”,一把薄刀既是主人公拼死抗争,抵抗土地开发、房屋拆迁的个人武器,也是作者展开农村现实批判的文学利器。
不过反过来说,中篇小说是否要义无反顾地继续这种文体“担当”?在网络流行语中,“担当”一词主要是指人物所主要承担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在过往的奥运会中,运动员们或许只有一种担当——“爱国担当”,但在本届奥运会中,我们看到,担当趋于多元化——既有精神象征中国女排所一以贯之的爱国担当,习惯了大包大揽的国乒的“大魔王担当”,也有傅园慧的“段子担当”、宁泽涛的“颜值担当”……各种“担当”改变了奥运会单一的意义结构,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由此想到,我们的中篇小说除了使尽“洪荒之力”来履行其惯有的文体担当,是否还有其他的担当可能?读罢本期作品,相信你已有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