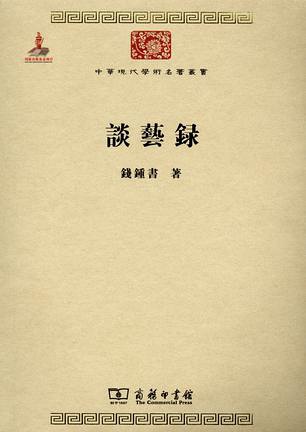 记得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神仙在分娩的时候,山摇地动,天崩地裂,仿佛要生产一座大山,最后生下来的却是一只小老鼠。做编辑工作常常有这样的感叹。悲催的是,与这则寓言故事不同,我们明知道生产的是一只小老鼠,却要抱着生产一座大山的努力来怀孕和分娩。 我在阅读《谈艺录》时发现一个标点符号和一个词有问题,编辑的职业病,让我欲罢不能地去查找原文的出处。其中所查找的书有十数种,其过程,恰如上则寓言所言。现在把查找的结果汇报如下,分享同行,请教方家。 (一)一个标点符号 《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1版)第236页最后一行到第237页开头6行有这样的一段话: 海德格尔至谓古训“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参观《管锥编》论《老子王弼注》第二“道理之道与道白之道”一段)。且曰:“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Schweigen heisst aber nicht stumm sein. Nur in echten Reden ist eigentliches Schweigen moeglich. Um schweigen zu koennen, muss das Dasein etwas zu sagen haben )见Heidegger,op,cit.,164,165。 查钱先生让参阅的内容在《管锥编》第二册第408页(见《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版),这段内容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近世且有谓相传“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注7:Heidegger,Sein und Zeit, Ist Haelfte, 3 Aufl., 165(der Mensch als Seiendes,das redet). )。 单看所引《谈艺录》中的第一句话颇为费解,但是如果回头看了《管锥编》中的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尤其是钱先生所加的外文。原来海德格尔在这里是拿希腊文的logos这个词来做文章,一词二义。而恰巧中文的“道”也暗合海德格尔的解释,不仅在中西哲学上做了彼此打通,而且两相比照,更有说服力。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编辑工作。 《谈艺录》第一版是1948年出版的,出版之后,钱先生很不满意。1983年,应广大读者要求,将原书补订,辑为下编。此时《管锥编》已经出版,下编内容多有采撷引用。此后,钱先生又有补正。2001年,三联书店编辑《钱钟书集》,将补订和补正纳入正文排版,方便读者。钱先生不是编辑,他的增补,会周全地考虑内容,不会周全地考虑编辑的体例和出版的具体规范。这就出现了这一段话的问题:第一,编辑体例不统一,该加外文的地方没有加;第二,前后引文不一致,出现了互见的乌龙注引;第三,没有核对原文,将摘引错为全引。 第一,编辑体例不一致 钱先生所引海德格尔的 “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按照《谈艺录》的体例,尤其是按照钱先生的学术规范,是要括加外文的,这里没有加上。没有加的原因是,在《管锥编》中,外文是以脚注的形式加的,见上文的注7。想来钱先生只是采撷了正文,而忘记了添加注释。因此编辑应该将这个注释补上才是。如果说有的地方不加外文尚可,那么这句话恰恰是要加外文的,因为钱先生在翻译这句话时依照他惯有的俏皮文字,做了意译。海德格尔的这句德文:der Mensch als Seiendes,das redet直译是:人是言谈的存在者。若能明了《存在与时间》中Sein(存在)与Seiendes(存在者)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在《存在与时间》的上下文中,Seiendes是不宜翻译为“动物”的。因此,没有补上这个注释,不仅导致了编辑体例的不一致,而且易于导致学术上的不规范。 第二,互见的乌龙引注 如果说前述所言,过于严格,那么由于没有这个引注而导致的下面的一个引注的乌龙事件,就不是吹毛求疵了。上文摘抄的《谈艺录》那段话,最后有一个引注:“见Heidegger,op,cit.,164,165”,其中op,cit.的意思是“上引书”,翻译成中文就是:“见海德格尔,上引书,第164、165页”。查《谈艺录》中的上文,并未引用海德格尔的著作。这就出现了一个引注上的乌龙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乌龙,就是因为《管锥编》中的注释没有引过来。没有引过来的原因是,编辑没有去核对《管锥编》的相关部分。此外,这个脚注的“164,165”中的这个逗号,也没有引起编辑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摘引导致的。 第三,没有核对原文,摘引变全引 我们知道,钱先生是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规范训练的,他的引注非常规范。翻遍《谈艺录》,如果是涉及到两页连引,钱先生所用的两页之间的标点符号一定是连字号“—”,反之,如果是分开的摘引,中间一定是逗号。因此当我们看到“164,165”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脑海中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个引注不是“164-5”?到底这个逗号是疏忽,还是前面的引文是分页的摘引。如果是摘引,那么其中肯定漏掉了一个省略号。此时,我们就一定要找到所引版本的原书,加以查证。 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果然,钱先生在这里是分引,而不是全引。“默不言非喑不言”在德文版第164页, “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在德文版第165页。查《存在与时间》中文版,这段话是这样的:“沉默却不叫黯哑。哑巴反倒有一种‘说’的倾向。哑巴不仅不曾证明他能够沉默,他甚至全无证明这种事情的的可能性。像哑巴一样,天生寡言的人也不标明他在沉默或他能沉默。从不发话的人也就不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沉默。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言谈中。为了能沉默,此在必须有东西可说,也就是说,此在必须具有它本身的真正而丰富的能展开状态可供使用。”(见《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第200—201页)既然是分引,第一句话后面必须加一个省略号,改为如下的样式:“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同理,其中所引德文中也要加省略号。 如果说原文和脚注是规范问题,那么这个省略号就是一个错误。为了这么一个省略号,费了如此工夫,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不值得,太较真,然后悲催的编辑却总是在这种较真中生活。 (二)一个词儿 《谈艺录》第44节谈江西诗派(上引书第395—399页),其中引用了元好问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 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里人” 钱钟书先生多次将此诗最后一句写作为:“未作西江社里人”,在文中亦多次将“江西派”写作“西江派”。 “江西诗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原作已经佚失,但是其观点流传极广,其后好事者辑录《江西诗派》总集踵事增华,刘克庄作《江西诗派总序》为之张目, “江西诗派”名传后世。因吕本中书名,“江西诗派”亦作“江西诗社”、“江西宗派”。 钱先生将江西派写作西江派,首先一个问题是,西江派与江西派是不是一回事。在网上百度到一篇“说‘西江’”的文章,文中说到: 西江:明清之际,文人墨客对江西的雅称。其说有:自古以来人们将由西至东流向的江河分之为:上游称“西江”,而下游为“东江”。其二,长江自西往东流,但是在中下游段内,至武汉,长江突然由北向南拐了一个大弯。途径黄冈,黄石、武穴到九江,再到湖口,这一由北向南所拐的大弯,将原为一个总督管辖的安徽江西,分为东西两处(安徽江苏在康熙六年以前为一省,称为江南省它与江西同属一个总督管辖,所谓两江,即江南与江西的简称)。因此,江东面的安徽称“东江”,江西面的江西称为“西江”。 按照上述材料,既然江西可以成为西江,那么“江西诗派”亦可以称为“西江诗派”了。该文正是这样说的: “江西诗派”,又称为“江西宗派”、“江西派”、“西江派”,是北宋后期形成的一个诗派。以黄庭坚(号山谷)为祖师,并列陈师道等人为宗派的成员。崇尚苦吟,以学问为诗,风格奇涩险怪。 但是文中并没有指出出处,到底是谁,在哪里首先使用“西江诗派”这个词的。当然,我们也或可同意钱先生的“西江派”应该是有所本,不为错。 第二个问题是,钱先生将元好问的诗写成“未作西江社里人”,那么元好问的原诗到底是“未作江西社里人”呢,还是“未作西江社里人”? (1)先查今人编的书。《万首论诗绝句》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一卷,第337页,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 (2)再查古书。载《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之《遗山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刻治刊本,卷十一,第123页,此诗为 “未作江西社里人”。《四部备要》第81册,第174页,《遗山诗笺注》卷十一,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 (3)那么是不是钱先生所用的版本不同,有版本认为以上两古版本皆为错,钱先生径改?再看旁证。《谈艺录》第396页,钱先生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钱大昕引此诗为 “未作西江社里人”,再查《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第386页,钱大昕所引为“未作江西社里人”。《谈艺录》第396页引《夕塘永日绪论》,王船山谓:“西昆、西江皆獭祭手段”。查王夫之《夕塘永日绪论》,并无所引原文,内中有言:“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 ,“江西宗派……皆一时和哄汉耳”,并无“西江”字样。 (4)查《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1983年9月第四次印刷,第138页,钱先生引此诗为:“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将“未作”改为“不作”,“江西”改为“西江”。 由此导致了第三个问题,钱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改“江西”作“西江”,是记忆错误,还是故意改的?首先钱先生很少记忆错误,其次此诗不应该记忆错误。此诗如此常见,钱先生对该诗又是如此心领神会,怎会出现错误,而且从四十年代的《谈艺录》错到五十年代《宋诗选注》一直到八十年代《谈艺录》的反复增订补正没有改正?如果是钱先生所见版本不同,并认为“西江”为正,“江西”为误,那么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或有方家解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