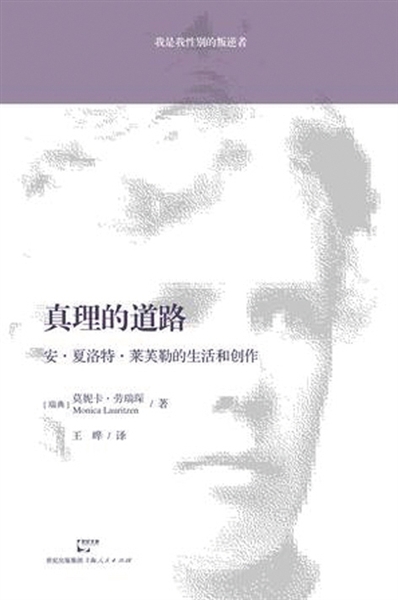
《真理的道路:安·夏洛特·莱芙勒的生活和创作》 作者: (瑞典)莫妮卡·劳瑞琛 译者:王晔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作为卡伊阿内洛公爵夫人的安·夏洛特
有多少女性没有期待过更自由的生活呢?但太多人还是不假思索地活在被规定了的日常轨道上。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女性性别压抑和生理禁锢,并没有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而消失。
如果你知道大约150年前,有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像一头文学母狮子那样怒吼,毕生追寻以一个“作为艺术家、思想者和性爱个体的独立身份”的女人而存在,也许你会慨叹——如果早一点阅读她的作品就好了。
“蓝袜子”之惑
用自己的名字写作
“如果早一点阅读她的作品”——这句话意味着,她有点籍籍无名,至少在中文世界是如此。她是瑞典现代文学先驱、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
这个名字很陌生。1909年,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获该奖的第一位女性。然而,她的同时代人安·夏洛特·莱芙勒却早已陨落。莱芙勒在世时,拉格洛夫写长信给她,表示同代的瑞典作家需要莱芙勒的指点,才能找到自己的风格。
莱芙勒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上“现代的突破”,戏剧是表达她女性先锋理念的最有力方式,而她本人短暂的生命也颇具戏剧性,从温柔的闺秀到恪尽职守的官员太太,继而成长为快乐的意大利公爵夫人、以激进观点获得国际知名度的女作家,这个长得一点也不美的瑞典女人,呈现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愈勇敢愈自由,莱芙勒开启了一种可能性——19世纪后半叶的瑞典,在男性权威几乎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欧洲社会中,莱芙勒是如何摆脱性别的限制,首先成为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真理的道路:安·夏洛特·莱芙勒的生活和创作》是一本让人读到战栗的人物传记,2012年在瑞典出版后,获得了瑞典最著名的文学奖奥古斯特奖年度最佳非虚构类作品提名。作者莫妮卡·劳瑞琛,一名女性学者,在此书前言中写:“我期待了解她(莱芙勒),因为她是为我及其他瑞典妇女奠定了基础的女性中的一个。今天,我、我的女儿和外孙女能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瑞典,要感谢她和许多她那个时代的人的天才、意志和勇气。”
这本薄薄的传记分十一章勾勒出一位女性主义作家的一生。安·夏洛特·莱芙勒1849年10月1日生于斯德哥尔摩。10月1日是很多瑞典家庭搬迁新居的日子,莱芙勒认为生在这一天使她成了一只迁徙鸟,不为任何障碍所阻。
父亲是校长,母亲有贵族血统,作为他们的女儿,莱芙勒处于中产阶级上层。她利用受教育的机会贪婪吮吸着文学、戏剧、艺术、科学、社会政策、妇女参政、道德辩论等各领域的知识。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瑞典,女性的文学才华依然被视作花边,最多是给孩子讲故事的能力。社会是家长制的,妻子、孩子和佣人从属于家庭男主人,妇女的解放问题已经成为升温的社会热点,到1872年她23岁结婚时,作为已婚妇女,她依然是个“未成年者”。而瑞典1874年才颁布法律使已婚妇女获得对自己个人劳动所得的支配权。
公共生活依然是男人的领域,社会规范把女性圈在家庭,是“感性和道德的源泉”,对于莱芙勒这样才华灼人的年轻女子来说,社会规范是她必须冲破的枷锁——“她的女性性别是并且持续是她最大的残障,但也是最首要的挑战”,劳瑞琛这样写道。
父亲饱受抑郁症之苦,母亲古斯塔娃虽然智识出众却控制欲极强,她和莱芙勒毕生都在一种紧密联系却又充满禁锢的母女纽带中,彼此爱护与折磨。从莱芙勒和她的女性知己塞克拉·霍德贝里的通信中,我们知道了莱芙勒19岁时(1868年),就声称她坚信写作是她的使命:“假如我放弃写作,等于放弃我的生命。”
莱芙勒与古斯塔夫·埃德格伦结婚,他属于保守的瑞典中产官僚阶级,低估她的文学才能,认为主妇和妻子的使命远比写小说神圣——他以为自己能控制她,可十六年的失败婚姻证明,在这场痛苦的心理拉锯战中,他的能量远不能和她匹敌。
“一个想写小说的女人,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段著名的话,也是莱芙勒的目标。1873年,她匿名写成的剧作《女演员》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首演成功,此后她开始寻找“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是狭窄的,也是她需要的,她将借助艺术活动和私人生活去接近她感知的真实。她当然可以选择隐匿入更宽广的“客厅”,这和她的传统布尔乔亚生活环境完全匹配,但莱芙勒摒弃了这个选择。
此后,她创作出《助理牧师》和《拖鞋底下》两部“小”戏剧却遇冷。古斯塔夫·埃德格伦太太的角色和作家自我认知间的挤压让她日益窒息,她到底是谁?
这种被困在妇女牢笼里的感觉,也是她新小说《露娜》的主题——受挫于戏剧,她开始考虑往短篇小说创作上探索。和她“灵魂接近”大哥尤斯塔,是莱芙勒写作道路上的导师,却也带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打击着她的自信。带着天真的好意,他要求妹妹用匿名写作,这可以保护妹夫古斯塔夫的官员声誉和他自己的事业体面——在那个年代,公开的女性作家被认为是一件家族的羞耻事。
更让莱芙勒受伤的,是彼时瑞典社会对杰出女性施以“蓝袜子”的污名——这个流行于当时男子的黑话,是说一个胆敢进入男人的文学、哲学、科学领域,却不符合男性设立的价值标准的女子。男人们用它,是为了捍卫男性的领地。
“蓝袜子”对安·夏洛特·莱芙勒的自我形象是个阴影,她曾经想挣脱它,但这个字眼对她来说在不断改变,在精进的写作路上,她意识到做“蓝袜子”不是羞耻之事,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我认定。
莱芙勒的天性是向往真实,诚如她在剧作和小说中表达的意愿——真实,是让人愉悦的,也必须是负责任的。1882年,莱芙勒用真名出版短篇小说集《来自生活》。
成为“文学母狮”
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
《来自生活》(多部)之后,作者劳瑞琛指出,莱芙勒开始成为“我们时代的作家”。创作伊始,她就对哥哥宣称,“妇女解放的理念离她的心很近”,但她并不激进,在她看来,“妇女问题的内涵就是做自己”,妇女解放问题比女权运动复杂得多。
关于妇女在爱情与婚姻、经济独立与职业选择、宗教信仰与私人生活等问题上,莱芙勒用精悍的短篇小说表达了她的思考——《孩子》描述了一个勤奋医生的父权思想是如何一点点戕害了妻子的独立人格;《奥洛尔·邦赫》极为出彩,探讨了性道德的单向度问题,主题颇像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奥洛尔这个被传统捆绑的贵族女子,最终在灯塔管理人的激情之爱面前退缩,莱芙勒在这个故事里受到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女主人公最后对情人说的话出自易卜生戏剧《群鬼》:“没有勇气忠实和真诚是悲惨的。”《在与社会的战争中》探讨的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如果一个母亲由于婚姻不幸而离开家庭之后,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对现代读者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是个幽灵。
1885年后,莱芙勒已经是瑞典文学圈的“文学母狮”,婚姻生活却是一潭死水,莱芙勒的激情投射在了亚当·豪赫这个学校校长、八个孩子的父亲身上,与他展开了一段柏拉图之恋,并以和他的爱情为原型,写成长篇小说《一个夏天的童话》。莱芙勒在此大胆想象了一种平等的爱的可能——一个有独立个性和事业的女性也能有婚姻。这无疑是一幅颇具前瞻性的未来场景——莱芙勒一直是现代的。
1889年,莱芙勒和古斯塔夫离婚,第二年,她和意大利情人帕斯夸列·德尔·派左结婚,派左称她为“我的灵魂的灵魂”。
北欧阴郁多雨环境下那只不断迁徙的鸟,终于飞到了温暖的南方——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更自由的地平线上,莱芙勒创作出短篇集《女性的气质和性欲的诱发》和六幕童话剧《真理的道路》,直至1892年因病去世。
《真理的道路》成为辨识莱芙勒最典型的作品,女主人公维拉拒绝接受“信仰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这样的宗教教义,所以不能进入天堂。维拉就是莱芙勒的化身——这样的女性,永不会相信惯例或别人对现实的解释,即使寻求真理的代价巨大,她们也要自己承受。
生命接近尾声前,莱芙勒说:“假如现在我死去,不得不说,我已在各方面登上人生的高度。”她曾对生而为女性有过抱怨,却用毕生的创作自证明心:“我是自己性别的叛逆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