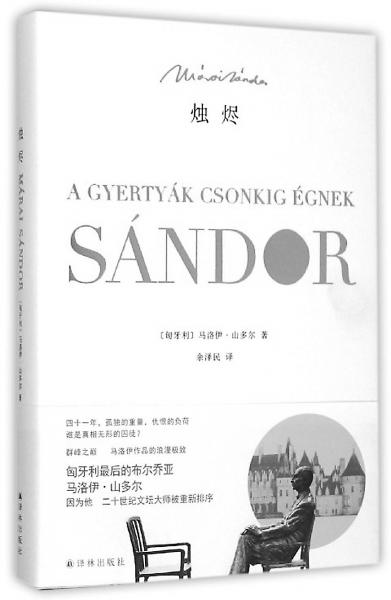
尽管活到20世纪80年代,马洛伊·山多尔骨子里却是一个19世纪的老派欧洲知识分子。1939年二战爆发不久,他就写下“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要熄灭”。稍迟,与他一道浸淫于传统欧洲精神的本雅明和茨威格先后自杀。马洛伊没有自杀,而是开始写作小说《烛烬》(1942),将他多年身经目击的那个传统欧洲的分崩离析,尽数囊括于这部作品中。或许,这本书也是他的告别宣言。1948年,马洛伊离开早已物是人非的祖国,流亡海外,就像《烛尽》中的两个主人公那样,流亡于昨日的世界。
流亡,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说来简单,其实也复杂。《烛烬》中两位73岁的老友,在暌违41年后重逢,于夏夜烛光的微暗之火下,娓娓诉说各自的经历。本来么,好友重逢,总要热情寒暄、殷勤备至、无话不谈吧?但分明,推杯换盏中又有各种机心、各种策略和各种刀光剑影,在暗暗蠢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流亡,完全不一样,以至针尖对麦芒,若非等到万事皆休、尘埃落定,就看不太分明。
我们且看主人亨利克将军的经历吧。他是奥匈帝国军人,帝国在一战战败解体后,他仍将1914年以前的世界,也就是贵族的秩序、荣誉与尊严,视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客人康拉德的观点则大不相同:“我的家园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康拉德是平民,热爱艺术和自由,所谓贵族的纪律和尊严在他并无多少意义。
反讽的是,康拉德的艺术品位和自由主义激情与亨利克的母亲和妻子遥相呼应,尤其是与后者的暗通款曲更是毁灭了亨利克的世界;更反讽的是,这两个明争暗斗的世界——贵族的秩序与平民的自由——在一战后一同灰飞烟灭,到二战时则其残留的那点影子都荡然无存了。
这就是所有流亡者共通的命运:他们都丧失了家园,但其各自的家园并不彼此共通,没有一条神秘的小径可以在两者之间相连,倒有万千额外的因素从中作梗:文明、阶级、财富、性别……这些冲突构成马洛伊大多数小说(如《一个市民的自白》《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等)的主题,也使其文字别具一种独白式的挽歌气质。其独白让人们那交织了爱情、友谊、背叛和阴谋的内心,反射出一种莎士比亚悲剧的奇特光谱。他们复杂的灵魂,在马洛伊手术刀一样的笔尖下,如剥洋葱般一瓣一瓣展现出异常丰富的质地。
而马洛伊挽歌一般的气质,又使其作品在横跨时空的背景下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宕开和扩大了小说原本的物理界限。《烛烬》中那墙上常年蒙尘、只为待客而擦拭一新的肖像画,那重新摆放用以还原帝国时代场景的陈设和氛围,那在冰凉的门把手上透出幽幽情丝的诡异低语……马洛伊以传统哥特手法呈现的,恰恰是一幕20世纪下半叶绽放的魔幻现实主义画卷。就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用以堆砌《百年孤独》的盛大废墟,马洛伊也建造了一座贮藏19世纪传统精神的乌托邦、伊甸园。或者我们不妨说得更精确一些——一座欧洲文明壮美的坟茔。
某种意义上,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存在这样的两极。以其代表人物论,一极是纳博科夫,另一极是马洛伊。纳博科夫代表的那类作家,视流亡为创作陷阱。因为对纳博科夫们来说,流亡不外就是各种纪实、感伤和“政治正确”之类的“刻奇”题目,“小我”意识浓烈而距艺术甚远。当然,它们或许尚有一些见证时代的史料价值。纳博科夫们所做的,是避开流亡,做更有意义的工作,或革新小说创作,或颠覆“刻奇”式的思维方法,等等。
而马洛伊所代表的那类作家,则以流亡为其写作灵魂,但他们同样反对廉价的“刻奇”,而汲汲从如烟往事中挖掘种种冲突与暧昧,驱散敷衍其上的粉色魅惑,重建湮没于战争和时代涤荡中的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是的,马洛伊内心怀揣的世界不止容纳所有“小我”的奔突竞逐,还有高屋建瓴的宏阔视角和深入肺腑的内心关照。读他的小说,不仅能读到时代,更能读到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