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斯蒂芬•金。我喜欢读他叙述的故事和许多人物(从《闪灵》《肖申克的救赎》《绿里奇迹》到《11 / 22 / 63》),但是,我绝不会将任何他的作品放入Western Cannon(西方正典)、World's Classics(世界经典)或者“死前必读之百种”中。 作为一个半辈子都呆在学校的人文学生,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著名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种种唾星。在2003年,布鲁姆是这样炮轰斯蒂芬•金获奖一事的:“这是在愚化(dumb down)我们文化生活的惊人过程中的又一新低”;“不论是一句一句来看,还是一段一段来看,还是一篇一篇来看,斯蒂芬•金都是一个极其不胜任的作家”;“他的书虽然售量以百万计,但是除了让出版业维持运转外,它们对人性(humanity)毫无贡献”。对布鲁姆来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吉卜林(Kipling)的《吉姆》,为什么要读“令人无法容忍的(insufferable)”《哈利•波特》?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爱伦•坡,为什么要读“粗俗至极”的斯蒂芬•金?(斯蒂芬•金赞誉J. K.罗琳说:“小时候喜欢读《哈利•波特》的人,长大也会喜欢读斯蒂芬•金。”这话让布鲁姆毛骨悚然。)其实,我也一直是如此认为的,直到我时隔多年又重新拿起斯蒂芬•金的《论写作》。

写于他遭受一次几乎致命的车祸之后,《论写作》是斯蒂芬•金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总结陈词。漫长的手术恢复过程带来的“脑闭塞”(writer's block),使得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创作小说。就像所有濒于失败的小说家那样,他开始着手于最合适的一个工种——教别人如何写小说。《论写作》既是自传,也是一个小说教程;书中作者交叉使用了两种语调,一种是自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想要了解他对写作的面面观,读者必须听完他叙述自己的大半生,从他的贫穷的童年一直到他如何与毒品纠缠。同时,它读起来也像是一篇对布鲁姆之类的批评家的长篇回应。对我而言,这本书解释了斯蒂芬•金为什么没有读过简•奥斯汀,为什么不是简•奥斯汀,更解释了为什么斯蒂芬•金会成为斯蒂芬•金。
生于1947年,斯蒂芬•金成长于美国底层的一个单亲家庭,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四年洗衣工、中学保洁员以及英语老师。相比于绝大多数的作家,二十七岁就拿到了一笔二十万稿酬的他(《魔女嘉丽》),算是极其幸运的。但是他的喜好以及创作动机,就此带着永恒的底层烙印。他强调,好的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语言、主题、风格、形式、寓意等等,都是次要的装饰品,或者说,这些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受过教育的底层(the educated underclass),不需要普鲁斯特的自悲自怜,需要的是带有“嘭”(金和他的哥哥在儿童时所追寻的pow!)一声的故事。所以,好的故事要不就要有恐怖,要不就要有惊奇,实在不行,起码要有恶心至极(gross-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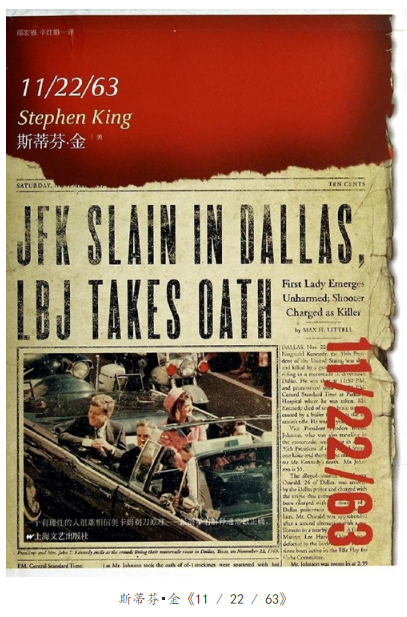
正如他借《11 / 22 / 63》主人公之口说出的:“香烟不过是烟,故事不过是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另有深意!”哪怕,这所谓的“另有深意”,才是批评家所真正关心的。批评家总是询问,斯蒂芬•金是不是一个“严肃的(serious)”作家?“严肃”就是一个指代“关心作品中的深意”的暗语。巧妙的是, 通过实实在在地“解构”一个作家如何创造出“深意”,《论写作》给出了答案:他的小说是有深意的,而且他会在写完初稿后寻找“深意”;同时,“深意”永远是第二位的,来源于故事,并且要绝对地服务于故事。甚至,小说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都应该服务于故事,“删掉所有可有可无的副词”直到最好只剩下动词!用他的话说,如果在地下遇见乔治•奥威尔,他一定要追问奥威尔:“《动物庄园》到底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寓意?”
当然,“故事性”不等于“文学性”(举一近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乏故事性,却几乎毫无文学性)。斯蒂芬•金的可爱在于,他不会为了批评家而矫揉造作出超出服务于故事之上的“文学性”,哪怕只是一句多余的修饰,或者一个多余的副词。然而,斯蒂芬•金又强调说,他的“故事性”,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喜悦,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治疗性质的涤荡(catharsis)。读读他是如何摆脱经年的酒醉和可卡因的,我猜这并非虚言。也许,这个世界上很少还有作家比他更“严肃地”忠于故事本身了吧?
虽然他的作品常常有关妖精鬼怪,他从来不提“灵感”。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灵感”是一种和造物主有关的神圣的存在;这和中国人常说的“述而不作”类似,“作”是来自于“神”或者“圣”。但是,作为最富灵感的作家之一,斯蒂芬•金却一丝一毫没有要把“灵感”拉离真实平面的意思。他以《魔女嘉丽》为例,把自己如何找到这个故事的过程放到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块,然后,所有有关灵感的“神圣性”就在此中被解构无遗。
正像借自基督教的canon(原意为“宗教圣典”)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正典统治下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宗教。我自创一个词,“文教”。“文学性”,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闻不着的超越性的存在,只有礼拜它的信众才能号称体验到它的存在。就像宗教自由是值得肯定的一样,“文教”作为一个以高中教师为信众主体、以大学教授为祭司、并且获得国家支持的宗教,本身并没有大错(也许我自己就一辈子都难以脱离组织)。布鲁姆的错误在于,他假设文学必须接受“文教”的教规,并且所有的美国人都应成为“文教”的教徒,不然,美国文化就是在走向愚化。《论写作》朴实地辩解道,文学完全可以有“文教”之外的“严肃性”,而社会偏底层的大众,不会、也不需要全部成为“文教”的教徒。正如马克•吐温所讽刺的那样,“经典,就是人人想读、却又没人真的读过的东西”。并不是斯蒂芬•金愚化了美国文化,而是布鲁姆忽视了一个事实:在高中教育普及之前,所有能读小说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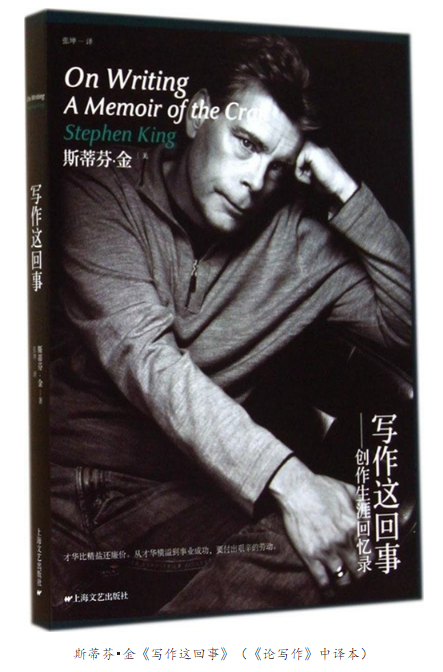
一个常常被斯蒂芬•金爱好者提及的相似案例,是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曾经被当做多产的畅销小说家而颇不受批评家待见,George Meredith这样评价道:“没有多少狄更斯的著作会长驻,因为它们脱离了生活。……如果在未来人们真的读到他的书,他们会奇怪他们到底在读些什么。”但是狄更斯的文学地位却在死后稳升不降。或许一个更贴近的例子是美国作家雷蒙•钱德勒,也许他们俩都永远不会被划入文学正典(我的耳边仿佛回响着金的声音:Who cares about the fucking canon!),《论写作》应该会和《简单的谋杀艺术》一样,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两座一直可见的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